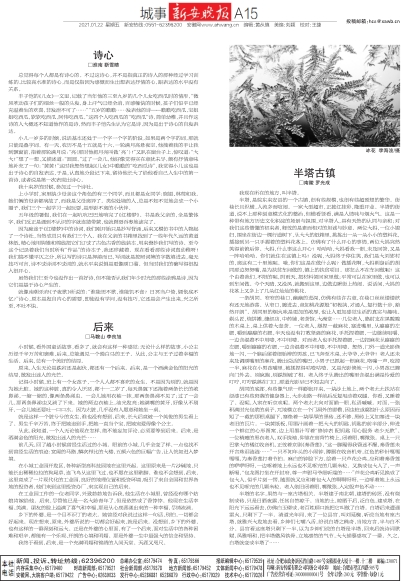发布日期:
诗心
□淮南靳雪晴
总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诗心的。不过这诗心,并不是指真正的诗人的那种经过学习训练的、比较高水准的诗心,而是仅指因为感慨而生出想表达抒情的心,跟表达的水平没有关系。
丰子恺的《儿女》一文里,记载了当年他的三至九岁的几个儿女吃西瓜时的情形,“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五岁的瞻瞻……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四个人吃西瓜的“吃西瓜”诗,简单幼稚,并且作这诗的人大概还不知道他作的是诗,然而丰子恺先生认为它是诗,因为是出于诗心的自发表达。
小儿一岁多的时候,说话基本还处于一个字一个字的阶段,如果是两个字的词,那就只能是叠字词。有一天,农历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一轮满月高悬夜空,他拽着我的手让我到飘窗前,指着那轮满月说:“亮(那时他把月亮叫做‘亮’)!”又趴在窗台子上,惊叹道:“大大!”想了一想,又描述道:“圆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觉得实在意犹未尽,颇有抒情意味地补充了一句:“黄黄!”这时我忽然想起《儿女》中瞻瞻的“吃西瓜诗”,我觉得小儿这也是出于诗心的自发表达,于是,认真地分段记下来,留待他长大了给他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或者说是第一次表现出诗心。
我十来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诗社。
上小学时,家里缺少母亲这个角色的有三个同学,而且都是女同学:晓娟、林莺和我。她们俩的母亲都病故了,而我是父母离异了。类似处境的人,总是不知不觉地会成一个小圈子,我们三个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是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在一起吭吭巴巴地啃完了《红楼梦》。书是我父亲的,全是繁体字,我们反正是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连猜带蒙,也就囫囵吞枣地读完了。
因为痴迷于《红楼梦》中的诗词,我们刚开始只是抄写背诵,后来又模仿书中的人物起了一个诗社,当然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在父亲的书箱里找到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黄道林纸,精心地用钩锥和棉线把它们订成了古色古香的线装本,用来誊抄我们写的诗。至今这个记录着我们当时所有“作品”的诗本子,我还珍藏着。现在看看那些诗词真幼稚呀!我们搞不懂平仄之分,所以写的诗只是押韵而已,写词就是按照词牌的字数填进去,毫无技巧可言,诗不成诗词不成词的,就水平来说倒是更像顺口溜。但当时我们的确写得很投入很开心。
虽然我们仨至今也没作出一首好诗,但不能否认我们年少时光的那些涂鸦是诗,因为它们是基于诗心产生的。
就像南朝乐府《子夜歌》所说的:“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诗心,原本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即使没有学问,没有技巧,它还是会产生出来,兴之所至,不吐不快。
总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诗心的。不过这诗心,并不是指真正的诗人的那种经过学习训练的、比较高水准的诗心,而是仅指因为感慨而生出想表达抒情的心,跟表达的水平没有关系。
丰子恺的《儿女》一文里,记载了当年他的三至九岁的几个儿女吃西瓜时的情形,“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五岁的瞻瞻……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四个人吃西瓜的“吃西瓜”诗,简单幼稚,并且作这诗的人大概还不知道他作的是诗,然而丰子恺先生认为它是诗,因为是出于诗心的自发表达。
小儿一岁多的时候,说话基本还处于一个字一个字的阶段,如果是两个字的词,那就只能是叠字词。有一天,农历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一轮满月高悬夜空,他拽着我的手让我到飘窗前,指着那轮满月说:“亮(那时他把月亮叫做‘亮’)!”又趴在窗台子上,惊叹道:“大大!”想了一想,又描述道:“圆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觉得实在意犹未尽,颇有抒情意味地补充了一句:“黄黄!”这时我忽然想起《儿女》中瞻瞻的“吃西瓜诗”,我觉得小儿这也是出于诗心的自发表达,于是,认真地分段记下来,留待他长大了给他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或者说是第一次表现出诗心。
我十来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诗社。
上小学时,家里缺少母亲这个角色的有三个同学,而且都是女同学:晓娟、林莺和我。她们俩的母亲都病故了,而我是父母离异了。类似处境的人,总是不知不觉地会成一个小圈子,我们三个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是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五年级的暑假,我们在一起吭吭巴巴地啃完了《红楼梦》。书是我父亲的,全是繁体字,我们反正是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连猜带蒙,也就囫囵吞枣地读完了。
因为痴迷于《红楼梦》中的诗词,我们刚开始只是抄写背诵,后来又模仿书中的人物起了一个诗社,当然成员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在父亲的书箱里找到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黄道林纸,精心地用钩锥和棉线把它们订成了古色古香的线装本,用来誊抄我们写的诗。至今这个记录着我们当时所有“作品”的诗本子,我还珍藏着。现在看看那些诗词真幼稚呀!我们搞不懂平仄之分,所以写的诗只是押韵而已,写词就是按照词牌的字数填进去,毫无技巧可言,诗不成诗词不成词的,就水平来说倒是更像顺口溜。但当时我们的确写得很投入很开心。
虽然我们仨至今也没作出一首好诗,但不能否认我们年少时光的那些涂鸦是诗,因为它们是基于诗心产生的。
就像南朝乐府《子夜歌》所说的:“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诗心,原本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即使没有学问,没有技巧,它还是会产生出来,兴之所至,不吐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