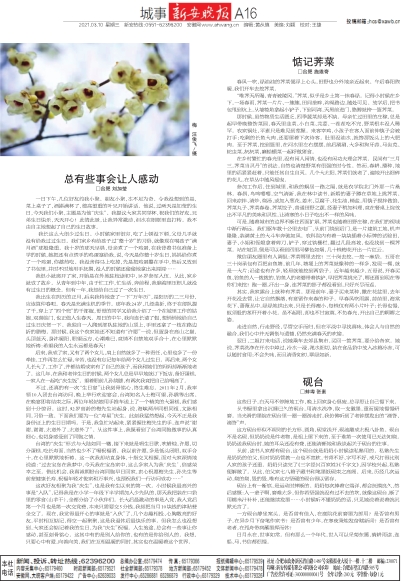发布日期:
砚台
□蚌埠张素
这些日子,白天马不停蹄地工作,晚上回家身心俱疲,总寻思让自己慢下来。
从书橱里拿出沉睡已久的砚台,用清水洗净,取一支徽墨,重而缓地慢慢研磨。当光滑的墨锭在砚台里一圈一圈游走时,我仿佛听到了老钟摆发出的“滴答、滴答”声。
这方砚台形似不规则的长方形,圆角,砚堂浅开,砚池雕成太极八卦鱼。砚台不是名砚,但奶奶说是件老物,是祖上留下来的,至于谁第一次使用已无法知晓。奶奶送我砚台时,她的耳朵还没有聋,还能清晰地和我谈起关于砚台的往事。
从前,读书人家都有砚台,这个砚台就是奶奶小时候读私塾用的。私塾先生是奶奶的伯父,但对奶奶管教一点也不宽软,书背不好、字写不好,戒尺打得比别人家的孩子还重。奶奶只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因学校兴起,私塾便解散了。从此,伯父家七八箱子藏书和笔墨纸砚束之高阁。后来,历经几次运动,烧的烧,毁的毁,唯有这方坚硬的砚台得以留存。
砚台上有一断痕,是运动时摔断的。奶奶每次捧着它端详,都会抚摸良久,然后感慨:人一辈子啊,磨难太多,但你若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就像这砚台,断了用糯米汁补补,还能继续发墨……小时候听不懂奶奶的话,只见她说着说着就沉默无言了。
一方砚台静坐案头。是否曾有佳人,在庭院花前磨墨为郎用?是否曾有男子,在异乡月下奋笔作家书?是否曾有少年,在寒夜秉烛发奋赋新词?是否曾有老者,在孤舟带病蘸墨挥而休?
日月永在,世事如常。但有那么一个年代,世人可以采菊东篱,晴耕雨读,连船、马、书信都很慢。
这些日子,白天马不停蹄地工作,晚上回家身心俱疲,总寻思让自己慢下来。
从书橱里拿出沉睡已久的砚台,用清水洗净,取一支徽墨,重而缓地慢慢研磨。当光滑的墨锭在砚台里一圈一圈游走时,我仿佛听到了老钟摆发出的“滴答、滴答”声。
这方砚台形似不规则的长方形,圆角,砚堂浅开,砚池雕成太极八卦鱼。砚台不是名砚,但奶奶说是件老物,是祖上留下来的,至于谁第一次使用已无法知晓。奶奶送我砚台时,她的耳朵还没有聋,还能清晰地和我谈起关于砚台的往事。
从前,读书人家都有砚台,这个砚台就是奶奶小时候读私塾用的。私塾先生是奶奶的伯父,但对奶奶管教一点也不宽软,书背不好、字写不好,戒尺打得比别人家的孩子还重。奶奶只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因学校兴起,私塾便解散了。从此,伯父家七八箱子藏书和笔墨纸砚束之高阁。后来,历经几次运动,烧的烧,毁的毁,唯有这方坚硬的砚台得以留存。
砚台上有一断痕,是运动时摔断的。奶奶每次捧着它端详,都会抚摸良久,然后感慨:人一辈子啊,磨难太多,但你若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就像这砚台,断了用糯米汁补补,还能继续发墨……小时候听不懂奶奶的话,只见她说着说着就沉默无言了。
一方砚台静坐案头。是否曾有佳人,在庭院花前磨墨为郎用?是否曾有男子,在异乡月下奋笔作家书?是否曾有少年,在寒夜秉烛发奋赋新词?是否曾有老者,在孤舟带病蘸墨挥而休?
日月永在,世事如常。但有那么一个年代,世人可以采菊东篱,晴耕雨读,连船、马、书信都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