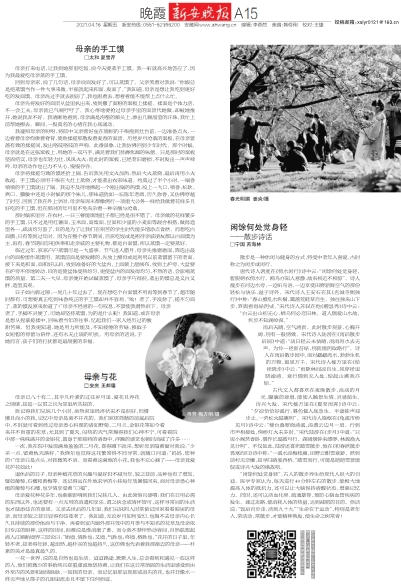发布日期:
母亲的手工馍
□太和夏雪芹
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到她那里吃饭,说今天要蒸手工馍。我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最爱吃母亲蒸的手工馍。
回到母亲家,说了几句话,母亲说面发好了,可以蒸馍了。父亲笑着对我说:“你娘总是把蒸馍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半夜就起来和面、发面了。”我知道,母亲是想让我吃到更好吃的发面馍。母亲洗过手就去厨房了,我也跟着去,想看看能不能帮上点什么忙。
母亲先将发好的面团从盆里扒出来,放到撒了面粉的案板上揉搓。揉面是个体力活,不一会工夫,母亲就已气喘吁吁了。我心疼地要抢过母亲手里的面团代她做,却被她推开,她说我弄不好。我清晰地看到,母亲满是沟壑的额头上,渗出几颗晶莹的汗珠,我忙上前帮她擦去。瞬间,一股莫名的心绪在我心底涌动。
我遵照母亲的吩咐,将院中父亲劈好垒在墙根的干柴抱到灶台前,一边准备点火,一边看着母亲佝偻着脊背,使劲揉搓那散发着麦香的面团。历经岁月沧桑的案板,在母亲紧落有致的揉搓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此番景象,让我仿佛回到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母亲就是在这张案板上,用她的一双巧手,满足着我们贫瘠焦渴的味蕾。只是那时的案板坚固结实,母亲也年轻力壮,风风火火;而此时的案板,已经老旧磨损,不时发出一声声呻吟,母亲的动作也已力不从心,慢慢吞吞。
母亲将揉搓匀致的馍坯拾上锅,告诉我先用文火加热,然后大火蒸烧,最后再用小火收尾。手工馍必须用干柴在大灶上蒸烧,才能蒸出农家味道。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锅香喷喷的手工馍就出了锅。我迫不及待地捧起一个刚出锅的热馍,咬上一大口,喷香、松软、爽口。朦胧中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那味道犹如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又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我在外上学时,母亲每周末都像例行一项重大公务一样给我做着花样多且好吃的手工馍,但在那时的年月里不免夹杂着一种辛酸与沧桑。
那时候家里穷,在农村,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都已经是很不错了。母亲做的花样繁多的手工馍,只不过是用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少量的小麦面等混合相搭,做得造型各一,咸淡均匀罢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艰苦的学生时代能多增添点食欲。而想吃白面膜,只有等到过年时。因为在整个春节期间,自家吃饭或是招待亲戚朋友都以白面馍为主,再有,春节期间祭祀供奉和走亲戚的主要礼物,都是白面馍,所以蒸馍一定要蒸好。
临近过年,家家户户蒸馍可是一大盛事。节气进入腊月,母亲先推磨磨面,筛选出最白的面粉留作蒸馍用。蒸馍前面是要发酵的,先放上酵母或是利用以前蒸馍留下的老面,接下来是和面,面和好以后,放到准备好的大盆内,上面蒙上湿绒布,放到土炉旁,大盆要在炉旁不停地转动,目的是使盆体受热均匀,更使盆内的面发得均匀,不然的话,会影响蒸馍的质量。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开始试碱蒸馍了,母亲手巧得很,蒸出的馍总是又白又胖,造型美观。
日子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吃个白面馍不用再等到春节了,超市随时都有,可想要真正吃到味香纯正的手工馍却并不容易。“唉!老了,手没劲了,搓不匀面了,蒸的馍没原来劲道了!”母亲不经意的一句叹息,不禁使我潸然泪下。母亲老了,手脚不灵便了,可她却坚持蒸馍,为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或许母亲是想从捏拿搓揉中,回味着当年的往事,忆起我们一家人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但我更知道,她是用力所能及、不知疲倦的劳碌,换取子女短暂的停留与陪伴,还有永无止境的叨扰。用母亲的话说,于她而言,孩子们的打扰都是最甜蜜的幸福。
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到她那里吃饭,说今天要蒸手工馍。我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最爱吃母亲蒸的手工馍。
回到母亲家,说了几句话,母亲说面发好了,可以蒸馍了。父亲笑着对我说:“你娘总是把蒸馍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半夜就起来和面、发面了。”我知道,母亲是想让我吃到更好吃的发面馍。母亲洗过手就去厨房了,我也跟着去,想看看能不能帮上点什么忙。
母亲先将发好的面团从盆里扒出来,放到撒了面粉的案板上揉搓。揉面是个体力活,不一会工夫,母亲就已气喘吁吁了。我心疼地要抢过母亲手里的面团代她做,却被她推开,她说我弄不好。我清晰地看到,母亲满是沟壑的额头上,渗出几颗晶莹的汗珠,我忙上前帮她擦去。瞬间,一股莫名的心绪在我心底涌动。
我遵照母亲的吩咐,将院中父亲劈好垒在墙根的干柴抱到灶台前,一边准备点火,一边看着母亲佝偻着脊背,使劲揉搓那散发着麦香的面团。历经岁月沧桑的案板,在母亲紧落有致的揉搓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此番景象,让我仿佛回到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母亲就是在这张案板上,用她的一双巧手,满足着我们贫瘠焦渴的味蕾。只是那时的案板坚固结实,母亲也年轻力壮,风风火火;而此时的案板,已经老旧磨损,不时发出一声声呻吟,母亲的动作也已力不从心,慢慢吞吞。
母亲将揉搓匀致的馍坯拾上锅,告诉我先用文火加热,然后大火蒸烧,最后再用小火收尾。手工馍必须用干柴在大灶上蒸烧,才能蒸出农家味道。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锅香喷喷的手工馍就出了锅。我迫不及待地捧起一个刚出锅的热馍,咬上一大口,喷香、松软、爽口。朦胧中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那味道犹如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又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我在外上学时,母亲每周末都像例行一项重大公务一样给我做着花样多且好吃的手工馍,但在那时的年月里不免夹杂着一种辛酸与沧桑。
那时候家里穷,在农村,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都已经是很不错了。母亲做的花样繁多的手工馍,只不过是用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少量的小麦面等混合相搭,做得造型各一,咸淡均匀罢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艰苦的学生时代能多增添点食欲。而想吃白面膜,只有等到过年时。因为在整个春节期间,自家吃饭或是招待亲戚朋友都以白面馍为主,再有,春节期间祭祀供奉和走亲戚的主要礼物,都是白面馍,所以蒸馍一定要蒸好。
临近过年,家家户户蒸馍可是一大盛事。节气进入腊月,母亲先推磨磨面,筛选出最白的面粉留作蒸馍用。蒸馍前面是要发酵的,先放上酵母或是利用以前蒸馍留下的老面,接下来是和面,面和好以后,放到准备好的大盆内,上面蒙上湿绒布,放到土炉旁,大盆要在炉旁不停地转动,目的是使盆体受热均匀,更使盆内的面发得均匀,不然的话,会影响蒸馍的质量。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开始试碱蒸馍了,母亲手巧得很,蒸出的馍总是又白又胖,造型美观。
日子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吃个白面馍不用再等到春节了,超市随时都有,可想要真正吃到味香纯正的手工馍却并不容易。“唉!老了,手没劲了,搓不匀面了,蒸的馍没原来劲道了!”母亲不经意的一句叹息,不禁使我潸然泪下。母亲老了,手脚不灵便了,可她却坚持蒸馍,为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或许母亲是想从捏拿搓揉中,回味着当年的往事,忆起我们一家人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但我更知道,她是用力所能及、不知疲倦的劳碌,换取子女短暂的停留与陪伴,还有永无止境的叨扰。用母亲的话说,于她而言,孩子们的打扰都是最甜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