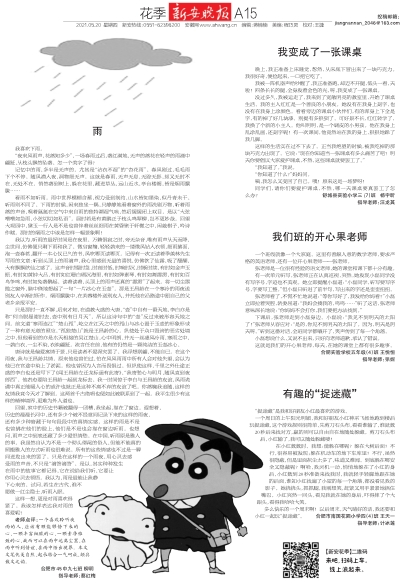发布日期:
雨
我喜欢下雨。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场春雨过后,落红满地,无声的落花在轻声的雨滴中翩跹,从枝头飘然坠落。怎一个美字了得?
记忆中的雨,多半是无声的。尤其是“沾衣不湿”的“杏花雨”。春风刚过,毛毛雨下个不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就是春雨,无声无息,无踪无影,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悄然落到树上,躲在花里,藏进草丛,远山近水,亭台楼阁,皆是烟雨朦胧……
看雨不如听雨。雨中世界模糊含蓄,视力受到制约,山水皆如墨染,似丹青未干。听雨则不同了。下雨的时候,闲来独坐一隅,只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洗刷万物,听着雨落的声音,嗅着氤氲在空气中来自雨的独特潮湿气味,然后缓缓闭上双目。是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届时若是有黄鹂正于枝头鸣翠柳,岂不更妙哉。回望大观园中,黛玉一行人是不是也曾伴着丝丝细雨在黄昏聚于轩榭之中,闲敲棋子,吟诗作赋。那时的烟雨之中该是怎样一幅景象啊!
我以为,听雨的最好时间是在夜里。万籁俱寂之时,旁无杂音,唯有雨声从天而降,尘世间,仿佛便只剩下雨和我了。微启窗牖,轻轻袭来的一缕微风钻入衣领,细雨拂面,泡一壶春茗,翻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风吹哪页读哪页。记得有一次正读着季羡林先生写雨的文章: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感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读着读着,头顶上的雨声还真的“霹雳”了起来。将一切尘嚣抛之窗外,脑中倏地想起了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那是王昌龄在一个寒冷的雨夜送别友人辛渐时所作。烟雨朦胧中,在芙蓉楼外送别友人,并托他在沿路途中跟自己的父老乡亲报平安。
只是那时一直不解,后来才知,在道教大盛的大唐,“壶”中自有一番天地,李白亦是称“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所以这诗句中的“壶”反过来被形容天地之间。前文道“寒雨连江”“楚山孤”,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与冰心置于玉壶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照应。“孤独楚山”就是王昌龄的心。纵使处于众口毁谤的恶劣处境之中,但他看到的亦是水天相接的吴江楚山,心中明朗,并无一丝凄风冷雨,寒雨之中,一袭白衣,一尘不染,衣袂翩跹。流言任在前,他有的仍然是一颗纯洁的玉壶冰心。
唐诗就是偏爱寓情于景,只是读者不爱深究罢了。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在这个雨夜,我与王昌龄共情。原来他也曾怕过,怕在风风雨雨中所有人会对他失望,会以为他已在官途中染上了淤泥。他也曾因为人言而畏惧过。但纵使这样,千里之外仕途正盛的李白也还是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他表态要陪王昌龄一起到龙标去。我一时间惊于李白与王昌龄的友谊,风雨诡谲中真正能暖人心的或许也就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友谊了吧。你落魄我追随,这样的友情我竟今天才了解到。这两首千古绝唱也便如此被联系到了一起。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回望,家中的历史书籍被翻得一团糟,我坐起,靠在了窗边。遐想着,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还有多少个被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这样的雨夜,还有多少种暗藏于句句段段中的真情实感。这样的雨是不是也曾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是不是也会靠在窗边听雨。也想问,雨声之中到底还藏了多少爱恨情愁。在中国,听雨原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但能不能真的照搬雅人的方式听雨也很难说。所有的这些情感也不过是一瞬间迸发出来的罢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夜,用心灵去感受雨的声音,不只是“滴答滴答”。是以,其实种种发生在雨中的故事它都记得,它在说给我们听,它要让你用心灵去领悟。我以为,雨是最能让我静下心来的。试问,若生在古代,谁不愿做一红尘隐士,听雨入眠。
这样一想,更是对雨喜欢得紧了。我该怎样表达我对雨的喜爱呢?
老师点评:一个喜欢聆听夜雨的人,应该有颗能够静下来的心,一颗丰富细腻的心,一颗素净雅致的心,故而可以在雨中远离尘嚣,在雨中听到情谊,在雨中悟出境界。本文文笔优美自然,起承转合一气呵成,颇具散文之韵。
合肥市45中九七班柳明
指导老师:蔡红梅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场春雨过后,落红满地,无声的落花在轻声的雨滴中翩跹,从枝头飘然坠落。怎一个美字了得?
记忆中的雨,多半是无声的。尤其是“沾衣不湿”的“杏花雨”。春风刚过,毛毛雨下个不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就是春雨,无声无息,无踪无影,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悄然落到树上,躲在花里,藏进草丛,远山近水,亭台楼阁,皆是烟雨朦胧……
看雨不如听雨。雨中世界模糊含蓄,视力受到制约,山水皆如墨染,似丹青未干。听雨则不同了。下雨的时候,闲来独坐一隅,只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洗刷万物,听着雨落的声音,嗅着氤氲在空气中来自雨的独特潮湿气味,然后缓缓闭上双目。是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届时若是有黄鹂正于枝头鸣翠柳,岂不更妙哉。回望大观园中,黛玉一行人是不是也曾伴着丝丝细雨在黄昏聚于轩榭之中,闲敲棋子,吟诗作赋。那时的烟雨之中该是怎样一幅景象啊!
我以为,听雨的最好时间是在夜里。万籁俱寂之时,旁无杂音,唯有雨声从天而降,尘世间,仿佛便只剩下雨和我了。微启窗牖,轻轻袭来的一缕微风钻入衣领,细雨拂面,泡一壶春茗,翻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风吹哪页读哪页。记得有一次正读着季羡林先生写雨的文章: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感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读着读着,头顶上的雨声还真的“霹雳”了起来。将一切尘嚣抛之窗外,脑中倏地想起了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那是王昌龄在一个寒冷的雨夜送别友人辛渐时所作。烟雨朦胧中,在芙蓉楼外送别友人,并托他在沿路途中跟自己的父老乡亲报平安。
只是那时一直不解,后来才知,在道教大盛的大唐,“壶”中自有一番天地,李白亦是称“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所以这诗句中的“壶”反过来被形容天地之间。前文道“寒雨连江”“楚山孤”,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与冰心置于玉壶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照应。“孤独楚山”就是王昌龄的心。纵使处于众口毁谤的恶劣处境之中,但他看到的亦是水天相接的吴江楚山,心中明朗,并无一丝凄风冷雨,寒雨之中,一袭白衣,一尘不染,衣袂翩跹。流言任在前,他有的仍然是一颗纯洁的玉壶冰心。
唐诗就是偏爱寓情于景,只是读者不爱深究罢了。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在这个雨夜,我与王昌龄共情。原来他也曾怕过,怕在风风雨雨中所有人会对他失望,会以为他已在官途中染上了淤泥。他也曾因为人言而畏惧过。但纵使这样,千里之外仕途正盛的李白也还是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他表态要陪王昌龄一起到龙标去。我一时间惊于李白与王昌龄的友谊,风雨诡谲中真正能暖人心的或许也就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友谊了吧。你落魄我追随,这样的友情我竟今天才了解到。这两首千古绝唱也便如此被联系到了一起。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回望,家中的历史书籍被翻得一团糟,我坐起,靠在了窗边。遐想着,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还有多少个被不经意间记录下来的这样的雨夜,还有多少种暗藏于句句段段中的真情实感。这样的雨是不是也曾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是不是也会靠在窗边听雨。也想问,雨声之中到底还藏了多少爱恨情愁。在中国,听雨原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但能不能真的照搬雅人的方式听雨也很难说。所有的这些情感也不过是一瞬间迸发出来的罢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夜,用心灵去感受雨的声音,不只是“滴答滴答”。是以,其实种种发生在雨中的故事它都记得,它在说给我们听,它要让你用心灵去领悟。我以为,雨是最能让我静下心来的。试问,若生在古代,谁不愿做一红尘隐士,听雨入眠。
这样一想,更是对雨喜欢得紧了。我该怎样表达我对雨的喜爱呢?
老师点评:一个喜欢聆听夜雨的人,应该有颗能够静下来的心,一颗丰富细腻的心,一颗素净雅致的心,故而可以在雨中远离尘嚣,在雨中听到情谊,在雨中悟出境界。本文文笔优美自然,起承转合一气呵成,颇具散文之韵。
合肥市45中九七班柳明
指导老师:蔡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