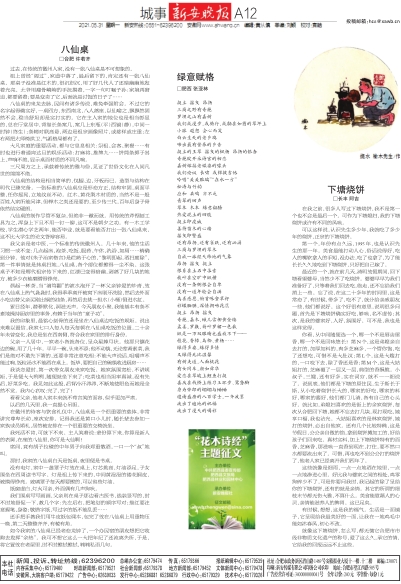发布日期:
八仙桌
□合肥许若齐
过去,在传统的徽州人家,没有一张八仙桌是不可想象的。
祖上曾经“阔过”,家道中落了,最后留下的,肯定还有一张八仙桌。那桌子没准是红木的,很沉很沉,用了好几代人了还暗幽幽地发着光亮。太爷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一字一句叮嘱子孙:家境再窘迫,都要留着;要是变卖了它,后面就是讨饭的日子了……
八仙桌的来龙去脉,民间有诸多传说,难免牵强附会。不过它的名字起得确实好,一桌四方,东西南北,八人落座,以仙喻之,飘飘然固然不会,稳当舒坦却是实打实的。它在主人家的地位也是相当彰显的,总在厅堂居中,背靠长条案几,案几上东瓶(平)西镜(静),中间一时钟(终生);条幛对联高悬,两边是祖宗画像照片,或慈祥或庄重;左右两把太师椅拱卫,气派格局都有了。
大凡家庭的重要活动,都与它息息相关:祭祖、会客、聚餐……有时也进行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打麻将、推牌九……饼筒条掷于其上,声响不绝,显示桌面材质的不同凡响。
三尺周方之上,承载着传统的雅与俗、见证了世俗文化在人间凡世的绵绵不绝。
八仙桌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仅腿、边、牙板而已。造型与结构在明代已臻完备。一张标准的八仙桌应是形态方正,结构牢固,桌面平整,任你摇晃,立地纹丝不动。红木、黄花梨木材质的,当然不是一般百姓人家所能问津,但榉木之类还是要的,至少传三代,百年后身子骨依然结实硬朗。
八仙桌的制作尽管不复杂,但绝非一蹴而就。用传统的斧锯刨工具为之,浑身上下且不用一钉一铆,这可不是朝夕之功。有一木工学校,学生潜心学艺两年,能否毕业,就是要看能否打出一张八仙桌来,这不比大学生的论文答辩容易。
我父亲是老中医,一个标准的传统徽州人。几十年来,他的生活习惯一成不变:几点起床、泡茶、吃饭、服药、午休、洗浴、如厕……精确到分钟。他对《朱子治家格言》是烂熟于心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第一件事情就是抹桌扫地,八仙桌,各个部位都擦得一尘不染。这张桌子不知是哪代祖宗传下来的,红漆已变得暗幽,剥落了好几块的地方,被多少衣袖磨蹭得铮亮。
晨起一杯茶,当“滴笃翻”的滚水泡开了一杯父亲钟爱的炒青,放在八仙桌上热气袅袅时,我得乖乖离开被窝下床刷牙洗脸,然后去外面小吃店替父亲买刚出锅的油条,再然后去挑一担水(小桶)倒进水缸。
累日经年,潜移默化,润滋无声。今天朋友小聚,我能基本有条不紊地操持厨房里的事务,有赖于当年的“童子功”。
我的印象里,最铭心刻骨的还是坐在八仙桌边吃饭的规矩。说出来难以置信,我家七口人每人每天每顿在八仙桌吃饭的位置,二十余年未曾变化,我总是坐在西南侧,符合我在家里的排行身份。
父亲一人居中,一家老小各就各位,呈众星捧月状。他那只镶花边的碗,用了几十年。平平一碗,从来不添;他不动筷,无论荤肴素菜,我们是绝对不敢先下箸的,还要非常注意吃相:不能大声说话,咀嚼声不能过响,饭粒汤水不能洒在桌上。饭毕,要把自己的碗筷收进厨房……
我谈恋爱时,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家吃饭。她家氛围宽松,不讲规矩,于是便大大咧咧,随便就坐下来了;吃菜也相当坦率真诚,没有先后,好菜多吃。我见如此这般,后背冷汗涔涔,不断地使眼色而她是全然不觉。我内心哀叹:完了,完了!
看看父亲,他老人家本来就不苟言笑的面容,似乎更加严肃。
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提心吊胆。
在徽州的待客与饮食礼仪中,八仙桌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非常讲究尊卑长幼,座次安排。记得我还是黄口小儿时,随长辈去参加一家族成员婚礼,居然被安排在一个很重要的交椅就坐。
我死活不肯,可就下不来。主人笑着说:辈份算下来,你算是新人的表舅,在座的八仙里,你可是大仙啊!
席间,竟有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向我郑重敬酒,一口一个“叔”地叫。
那时,我家的八仙桌白天是饭桌,夜里便是书桌。
没有电灯,家中一盏罩子灯放在桌上,灯芯挑高,灯油添足,子女围坐在四周读书写字。灯是祖上传下来的,中间黄澄澄的镂花铜皮,被摸得铮亮。玻璃罩子每天都要擦的,可以省些灯油。
纸窗虚白,灯火可亲,外面偶有几声狗吠。
我们围桌写写画画,父亲则在桌子那边看古医书,线装竖写的,时不时地督促一下,教几个字:先左后右,把笔划的顺序写对;描红要注意握笔、身姿;敬惜字纸,写过字的纸不能乱丢……
还手把手教我们用牛皮纸包课本,包完了放在八仙桌上用重物压一晚,第二天整整齐齐,有棱有角。
如今我家的八仙桌已经老态龙钟了,一个办民宿的朋友想把它收购去发挥“余热”。我可不想它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流离失所,于是,将它置放在老屋里,时不时擦拭擦拭,喃喃私语几句。
过去,在传统的徽州人家,没有一张八仙桌是不可想象的。
祖上曾经“阔过”,家道中落了,最后留下的,肯定还有一张八仙桌。那桌子没准是红木的,很沉很沉,用了好几代人了还暗幽幽地发着光亮。太爷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一字一句叮嘱子孙:家境再窘迫,都要留着;要是变卖了它,后面就是讨饭的日子了……
八仙桌的来龙去脉,民间有诸多传说,难免牵强附会。不过它的名字起得确实好,一桌四方,东西南北,八人落座,以仙喻之,飘飘然固然不会,稳当舒坦却是实打实的。它在主人家的地位也是相当彰显的,总在厅堂居中,背靠长条案几,案几上东瓶(平)西镜(静),中间一时钟(终生);条幛对联高悬,两边是祖宗画像照片,或慈祥或庄重;左右两把太师椅拱卫,气派格局都有了。
大凡家庭的重要活动,都与它息息相关:祭祖、会客、聚餐……有时也进行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打麻将、推牌九……饼筒条掷于其上,声响不绝,显示桌面材质的不同凡响。
三尺周方之上,承载着传统的雅与俗、见证了世俗文化在人间凡世的绵绵不绝。
八仙桌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仅腿、边、牙板而已。造型与结构在明代已臻完备。一张标准的八仙桌应是形态方正,结构牢固,桌面平整,任你摇晃,立地纹丝不动。红木、黄花梨木材质的,当然不是一般百姓人家所能问津,但榉木之类还是要的,至少传三代,百年后身子骨依然结实硬朗。
八仙桌的制作尽管不复杂,但绝非一蹴而就。用传统的斧锯刨工具为之,浑身上下且不用一钉一铆,这可不是朝夕之功。有一木工学校,学生潜心学艺两年,能否毕业,就是要看能否打出一张八仙桌来,这不比大学生的论文答辩容易。
我父亲是老中医,一个标准的传统徽州人。几十年来,他的生活习惯一成不变:几点起床、泡茶、吃饭、服药、午休、洗浴、如厕……精确到分钟。他对《朱子治家格言》是烂熟于心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第一件事情就是抹桌扫地,八仙桌,各个部位都擦得一尘不染。这张桌子不知是哪代祖宗传下来的,红漆已变得暗幽,剥落了好几块的地方,被多少衣袖磨蹭得铮亮。
晨起一杯茶,当“滴笃翻”的滚水泡开了一杯父亲钟爱的炒青,放在八仙桌上热气袅袅时,我得乖乖离开被窝下床刷牙洗脸,然后去外面小吃店替父亲买刚出锅的油条,再然后去挑一担水(小桶)倒进水缸。
累日经年,潜移默化,润滋无声。今天朋友小聚,我能基本有条不紊地操持厨房里的事务,有赖于当年的“童子功”。
我的印象里,最铭心刻骨的还是坐在八仙桌边吃饭的规矩。说出来难以置信,我家七口人每人每天每顿在八仙桌吃饭的位置,二十余年未曾变化,我总是坐在西南侧,符合我在家里的排行身份。
父亲一人居中,一家老小各就各位,呈众星捧月状。他那只镶花边的碗,用了几十年。平平一碗,从来不添;他不动筷,无论荤肴素菜,我们是绝对不敢先下箸的,还要非常注意吃相:不能大声说话,咀嚼声不能过响,饭粒汤水不能洒在桌上。饭毕,要把自己的碗筷收进厨房……
我谈恋爱时,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家吃饭。她家氛围宽松,不讲规矩,于是便大大咧咧,随便就坐下来了;吃菜也相当坦率真诚,没有先后,好菜多吃。我见如此这般,后背冷汗涔涔,不断地使眼色而她是全然不觉。我内心哀叹:完了,完了!
看看父亲,他老人家本来就不苟言笑的面容,似乎更加严肃。
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提心吊胆。
在徽州的待客与饮食礼仪中,八仙桌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非常讲究尊卑长幼,座次安排。记得我还是黄口小儿时,随长辈去参加一家族成员婚礼,居然被安排在一个很重要的交椅就坐。
我死活不肯,可就下不来。主人笑着说:辈份算下来,你算是新人的表舅,在座的八仙里,你可是大仙啊!
席间,竟有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向我郑重敬酒,一口一个“叔”地叫。
那时,我家的八仙桌白天是饭桌,夜里便是书桌。
没有电灯,家中一盏罩子灯放在桌上,灯芯挑高,灯油添足,子女围坐在四周读书写字。灯是祖上传下来的,中间黄澄澄的镂花铜皮,被摸得铮亮。玻璃罩子每天都要擦的,可以省些灯油。
纸窗虚白,灯火可亲,外面偶有几声狗吠。
我们围桌写写画画,父亲则在桌子那边看古医书,线装竖写的,时不时地督促一下,教几个字:先左后右,把笔划的顺序写对;描红要注意握笔、身姿;敬惜字纸,写过字的纸不能乱丢……
还手把手教我们用牛皮纸包课本,包完了放在八仙桌上用重物压一晚,第二天整整齐齐,有棱有角。
如今我家的八仙桌已经老态龙钟了,一个办民宿的朋友想把它收购去发挥“余热”。我可不想它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流离失所,于是,将它置放在老屋里,时不时擦拭擦拭,喃喃私语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