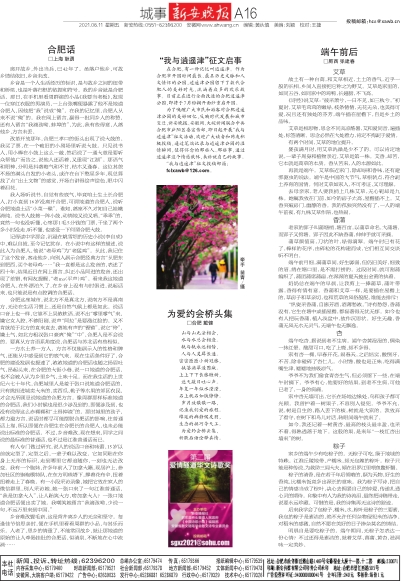发布日期:
端午前后
艾草
故土有一种白蒿,和艾草相近,土土的香气,近乎一般的长相,乡间人直接把它称之为野艾。艾草是家里的,如同五谷,如同家中的鸡鸭,长翅膀,不飞高。
《诗经》说艾草:“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初夏时,艾草毛茸茸的嫩绿,枝条倩倩,无花无朵,也美得可爱,况且还有独处的芬芳,端午插在屋檐下,自是乡土的品味。
艾草是相思物,思念不问炎凉酷暑,艾和爱同音,遍插处,标签清晰。思念必然在大处着力,肯定不拘泥于爱情。
有两个时间,艾草的地位提升。
婴孩满月时,用艾草洗澡是少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一辈子周身和植物亲近,艾草是第一株。艾香,却苦,它本就是蒿草的本质。香从苦来,人的本源如此。
再就是端午。艾草临近家门,除却绿和香味,还有避邪驱虫的说法。端午是中国的大节气,草根装点,符合泥土养育的国情。何时艾草如家人,不可考证,又可理解。
去母亲家,老人要我捎上几株艾草,无心呢却是九株。她嘱我放在门前,如今的房子太高,屋檐插不上。艾香突破房门,幽静的香。我的孤独突然没有了,一人的端午前夜,有九株艾草作陪,也热闹。
香蒲
老家的郢子叫蒲塘梢,塘百亩,以蒲草命名,大蒲塘,而郢子又傍塘。郢子因此不缺香蒲,伸伸手就可采摘。
蒲草颜值高,刀状的叶,绿得滴翠。端午时已有花了,棒样的花序,由碎粒的花构建而成,它们相互间交谈听不明白。
端午前月细,满蒲草间,好生孱弱,但仍旧美好,细致的眉,绣在塘口里,是不需打捞的。过段时间,就可割蒲编织了,蒲团蒲席蒲扇,在深深的夏天披出金黄的执着。
奶奶总在端午的早晨,让我剪上一捧蒲草,蒲叶带露,香得有情有意。香蒲和艾草一样,是要插在屋檐上的,草房子和草亲切,也和荒草的风俗般配,谁能去排斥?
“纵旋采香蒲,自斟芳酒,酒薄愁浓。”诗有愁怨,香蒲没有,它生在塘中或插屋檐,都磊落得无忧无郁。如今也有人把玩香蒲,植入浅盆中,故作沉思状。好生无趣,香蒲无风无水无灵气,无端午也无飘逸。
杏
端午吃杏,据说到老不生病。端午杏黄澄澄的,偶染一抹红晕。酸甜可口,吃了上瘾,却不多得。
家有杏一棵,早春开花,闹春天,之后结实,酸倒牙,不苦,除非碰碎了杏仁儿。小时馋,酸也是正味,吃得满嘴生津,嘘嘘地抽吸凉气。
爷爷不为我们偷食青杏生气,但必须留下一些,在端午时摘下。爷爷有心,他要好的结果,到老不生病,可他已老了,一身的病痛。
家中杏无墙可出,它长在场地边缘处,鸟和孩子都可光顾。我曾护着一树果子,不容别人侵犯。爷爷不允,说,树是自生的,路人丢下的核,树就是大家的。我放弃了看守,在树下和鸟儿对话,转眼间端午就来了。
如今,我还记着一树黄杏,最高的枝头最丰盈,也采不着,得熟透落于地下。这般的果,是来年“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树。
粽子
家乡的端午少有吃粽子的。无粽子可吃,缘于地域的特殊。江淮丘陵地带,产糯米,却无包缠的粽叶。粽子只能是种传说,为救助三闾大夫,倾在汨罗江里喂鱼鳖虾蟹。
粽子的清香,是在若干年后领略的,疑为天物,好生的香纯,比糯米饭竟多出深长的意味。我为粽子写诗,把自己的情感当成了棕叶,决心去拥紧自己的钟爱,传递扎透心灵的期待。印象中有人为我的诗流泪,最终把诗稿带走,说要永远珍藏。可惜的是,我的诗集再无这诗的踪迹。
后来我学会了包粽子,糯米、水、粽叶是粽子的三要素,我包的粽子是素洁的,绝不允许任何杂物侵犯米的洁净。对稻米的感激,自然不愿在美好的日子掺杂莫名的情结。
明晨自是要吃粽子的。端午期间,无粽子怎表达一份心情?不过还得是素洁的,就着艾草、菖蒲、黄杏,滋润味一定美妙。
故土有一种白蒿,和艾草相近,土土的香气,近乎一般的长相,乡间人直接把它称之为野艾。艾草是家里的,如同五谷,如同家中的鸡鸭,长翅膀,不飞高。
《诗经》说艾草:“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初夏时,艾草毛茸茸的嫩绿,枝条倩倩,无花无朵,也美得可爱,况且还有独处的芬芳,端午插在屋檐下,自是乡土的品味。
艾草是相思物,思念不问炎凉酷暑,艾和爱同音,遍插处,标签清晰。思念必然在大处着力,肯定不拘泥于爱情。
有两个时间,艾草的地位提升。
婴孩满月时,用艾草洗澡是少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一辈子周身和植物亲近,艾草是第一株。艾香,却苦,它本就是蒿草的本质。香从苦来,人的本源如此。
再就是端午。艾草临近家门,除却绿和香味,还有避邪驱虫的说法。端午是中国的大节气,草根装点,符合泥土养育的国情。何时艾草如家人,不可考证,又可理解。
去母亲家,老人要我捎上几株艾草,无心呢却是九株。她嘱我放在门前,如今的房子太高,屋檐插不上。艾香突破房门,幽静的香。我的孤独突然没有了,一人的端午前夜,有九株艾草作陪,也热闹。
香蒲
老家的郢子叫蒲塘梢,塘百亩,以蒲草命名,大蒲塘,而郢子又傍塘。郢子因此不缺香蒲,伸伸手就可采摘。
蒲草颜值高,刀状的叶,绿得滴翠。端午时已有花了,棒样的花序,由碎粒的花构建而成,它们相互间交谈听不明白。
端午前月细,满蒲草间,好生孱弱,但仍旧美好,细致的眉,绣在塘口里,是不需打捞的。过段时间,就可割蒲编织了,蒲团蒲席蒲扇,在深深的夏天披出金黄的执着。
奶奶总在端午的早晨,让我剪上一捧蒲草,蒲叶带露,香得有情有意。香蒲和艾草一样,是要插在屋檐上的,草房子和草亲切,也和荒草的风俗般配,谁能去排斥?
“纵旋采香蒲,自斟芳酒,酒薄愁浓。”诗有愁怨,香蒲没有,它生在塘中或插屋檐,都磊落得无忧无郁。如今也有人把玩香蒲,植入浅盆中,故作沉思状。好生无趣,香蒲无风无水无灵气,无端午也无飘逸。
杏
端午吃杏,据说到老不生病。端午杏黄澄澄的,偶染一抹红晕。酸甜可口,吃了上瘾,却不多得。
家有杏一棵,早春开花,闹春天,之后结实,酸倒牙,不苦,除非碰碎了杏仁儿。小时馋,酸也是正味,吃得满嘴生津,嘘嘘地抽吸凉气。
爷爷不为我们偷食青杏生气,但必须留下一些,在端午时摘下。爷爷有心,他要好的结果,到老不生病,可他已老了,一身的病痛。
家中杏无墙可出,它长在场地边缘处,鸟和孩子都可光顾。我曾护着一树果子,不容别人侵犯。爷爷不允,说,树是自生的,路人丢下的核,树就是大家的。我放弃了看守,在树下和鸟儿对话,转眼间端午就来了。
如今,我还记着一树黄杏,最高的枝头最丰盈,也采不着,得熟透落于地下。这般的果,是来年“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树。
粽子
家乡的端午少有吃粽子的。无粽子可吃,缘于地域的特殊。江淮丘陵地带,产糯米,却无包缠的粽叶。粽子只能是种传说,为救助三闾大夫,倾在汨罗江里喂鱼鳖虾蟹。
粽子的清香,是在若干年后领略的,疑为天物,好生的香纯,比糯米饭竟多出深长的意味。我为粽子写诗,把自己的情感当成了棕叶,决心去拥紧自己的钟爱,传递扎透心灵的期待。印象中有人为我的诗流泪,最终把诗稿带走,说要永远珍藏。可惜的是,我的诗集再无这诗的踪迹。
后来我学会了包粽子,糯米、水、粽叶是粽子的三要素,我包的粽子是素洁的,绝不允许任何杂物侵犯米的洁净。对稻米的感激,自然不愿在美好的日子掺杂莫名的情结。
明晨自是要吃粽子的。端午期间,无粽子怎表达一份心情?不过还得是素洁的,就着艾草、菖蒲、黄杏,滋润味一定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