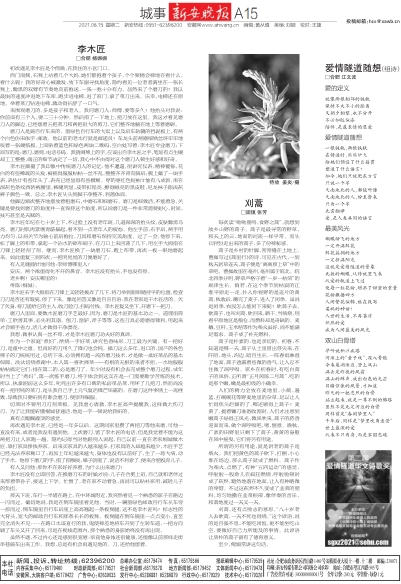发布日期:
刈蒿
□固镇张芳
每次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就想到故乡山野的蒿子。蒿子是最寻常的野草,和天上的云、地面的河流一样平常。而从《诗经》走出来的蒿子,多了份神秘感。
蒿子是乡村的针脚,密密缝在土地上。曹操写过《蒿里行》的诗,可见在古代,一到秋天衰草连天,蒿子便是“离离原上草”中的草吧。曹操故里在亳州,亳州属于皖北。皖北四季分明,野草严格守着“一岁一枯荣”的规律生长。倘若,在这个季节到枯寂的江淮平原走一走,扑入你视野的是连片的黄蒿,秋收后,耩完了麦子,进入了闲季。虽说是闲季,农民怎么能闲下来呢?砍蒿子去。砍蒿子,也叫刈蒿,砍回来,晒干,当柴烧,别看平原地区是粮仓,而燃料却是奇缺的。麦穰、豆秆、玉米秸等作为柴火虽好,尚不能满足需求。蒿子成了补充燃料。
蒿子是朴素的,也是亲切的。初春,不知道是哪一天,蒿子从土里冒出芽尖来,在阡陌、地头、沟边,暗自生长,一阵春雨淋湿了地面,蒿子透露着些微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做了深呼吸。家乡在初春时,有吃白蒿子的风俗,正所谓“正月茵陈二月蒿”,吃的是那个嫩,嫩是最初级的小确幸。
人们的精力全放在麦地里,小薊、遏蓝、打碗碗花等野麦地里的杂草,足以让人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哪还顾得上蒿子?麦黄了,提着镰刀准备收割时,人们才注意到嫩蒿子绿得正风光,微风吹来,蒿子的药香迎面而来,做个深呼吸吧,嗯,惬意。晚秋,广袤的田野里只剩下了蒿子,黄黄的身躯在风中摇曳,它们将另有用途。
所谓的另有用途,就是衰老的蒿子是柴火。我们把黄色的蒿子砍下、打捆,小心堆在场边,那么蒿子就成了燃料。蒿子作为柴火,点燃了,有种“五四运动”的感觉,呼啦啦一股劲儿在疯狂燃烧,呼啦啦顿时成了灰烬,黯然地落在地面,让人有种略微的疼惜。不过这灰烬不久变成了韭菜的肥料,均匀地撒在韭菜根部,像伴奏的音乐,和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刈蒿,还有点励志的意思。“八十岁老人去砍蒿,一天不死也得烧。”这个谚语,说的是自强不息,不能吃闲饭,更不能坐吃山空,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此谚语让质朴的蒿子富有了德育意义。
至少,俺娘常讲这句话。
每次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就想到故乡山野的蒿子。蒿子是最寻常的野草,和天上的云、地面的河流一样平常。而从《诗经》走出来的蒿子,多了份神秘感。
蒿子是乡村的针脚,密密缝在土地上。曹操写过《蒿里行》的诗,可见在古代,一到秋天衰草连天,蒿子便是“离离原上草”中的草吧。曹操故里在亳州,亳州属于皖北。皖北四季分明,野草严格守着“一岁一枯荣”的规律生长。倘若,在这个季节到枯寂的江淮平原走一走,扑入你视野的是连片的黄蒿,秋收后,耩完了麦子,进入了闲季。虽说是闲季,农民怎么能闲下来呢?砍蒿子去。砍蒿子,也叫刈蒿,砍回来,晒干,当柴烧,别看平原地区是粮仓,而燃料却是奇缺的。麦穰、豆秆、玉米秸等作为柴火虽好,尚不能满足需求。蒿子成了补充燃料。
蒿子是朴素的,也是亲切的。初春,不知道是哪一天,蒿子从土里冒出芽尖来,在阡陌、地头、沟边,暗自生长,一阵春雨淋湿了地面,蒿子透露着些微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做了深呼吸。家乡在初春时,有吃白蒿子的风俗,正所谓“正月茵陈二月蒿”,吃的是那个嫩,嫩是最初级的小确幸。
人们的精力全放在麦地里,小薊、遏蓝、打碗碗花等野麦地里的杂草,足以让人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哪还顾得上蒿子?麦黄了,提着镰刀准备收割时,人们才注意到嫩蒿子绿得正风光,微风吹来,蒿子的药香迎面而来,做个深呼吸吧,嗯,惬意。晚秋,广袤的田野里只剩下了蒿子,黄黄的身躯在风中摇曳,它们将另有用途。
所谓的另有用途,就是衰老的蒿子是柴火。我们把黄色的蒿子砍下、打捆,小心堆在场边,那么蒿子就成了燃料。蒿子作为柴火,点燃了,有种“五四运动”的感觉,呼啦啦一股劲儿在疯狂燃烧,呼啦啦顿时成了灰烬,黯然地落在地面,让人有种略微的疼惜。不过这灰烬不久变成了韭菜的肥料,均匀地撒在韭菜根部,像伴奏的音乐,和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刈蒿,还有点励志的意思。“八十岁老人去砍蒿,一天不死也得烧。”这个谚语,说的是自强不息,不能吃闲饭,更不能坐吃山空,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此谚语让质朴的蒿子富有了德育意义。
至少,俺娘常讲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