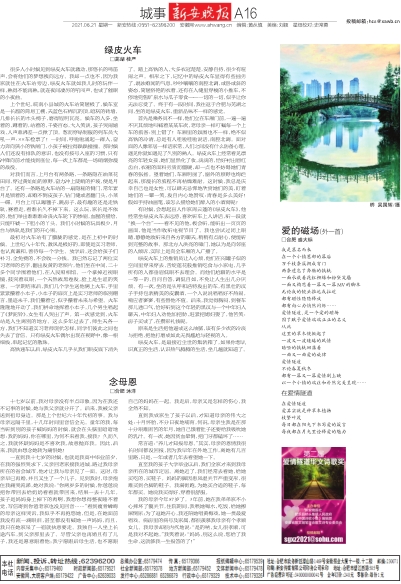发布日期:
绿皮火车
□芜湖桂严
很多人小时候见到绿皮火车就激动,那悠长的鸣笛声,会将他们的梦想拽向远方。我却一点也不,因为我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绿皮火车就如我儿时的玩伴一样,熟得不能再熟,就连夜间凄厉的吼叫声,也成了催眠的小夜曲。
上个世纪,皖南小县城的火车站简陋极了,候车室是一长溜的简易工棚,天蓝色石棉瓦的顶,暗灰的砖墙,几排长长的木头椅子,磨得锃明瓦亮。候车的人多,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千姿百态,大人笑谈,孩子哭闹嬉戏,人声鼎沸差一点掀了顶。忽而穿绿制服的列车员大吼一声:××车检票了!一时间,呼啦啦涌起一群人,奋力奔向狭小的铁闸门,小孩子被拉得跌跌撞撞。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排队的意识,也没有按号入座的习惯,只有冲锋向前才能找到座位,每一次上车都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役。
对我们而言,上月台有两条路,一条路隐在油菜花田间,穿过黄灿灿的原野,奋力冲上陡峭的护坡,便是月台了。还有一条路是火车站的一扇隐秘的侧门,常年累月是锁着的,却难不倒皮孩子,钻门缝或者翻门头,小菜一碟。月台上可以踢毽子、跳房子,最有趣的还是走铁轨,赛着走,看谁长久不掉下来。这么玩,家长是不依的,他们举出谁谁谁命丧火车轮下的惨剧,血腥的描绘,只能吓唬一下胆小的丫头。我们小时候的玩具极少,月台与铁轨是我们的开心果。
最初对火车站有了朦胧的感觉,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教风是极好的,即使是实习老师,也认真谦和,善待每一个学生。放学后,还会给孩子们补习,全免费的,不会收一分钱。我已然忘记了两位实习老师的名字,翻出发黄的老照片,他们坐在中间,二十多个同学围着他们,在人民照相馆。一个拿掉近视眼镜,鼓突着双眼,一个天然浓黑卷发,脸上是生涩的笑意。一学期结束后,我们几个学生送他俩上火车,手里紧紧攥着小本子,小本子的扉页上是实习老师的临别赠言,墨迹未干,我们攥着它,似乎攥着未来与希望。火车隆隆地开动了,我们拼命地挥着小本子,几个男生唱起了《梦驼铃》,女生有人哭出了声。第一次感觉到,火车站是人生离别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师生天各一方,我们不知道实习老师现状怎样,同学们彼此之间也失去了音信。只有绿皮火车偶尔出现在视野中,像一根细线,串起记忆的散珠。
高铁通车以后,绿皮火车几乎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了。踏上高铁的人,大多衣冠楚楚,安静自持,很少有喧闹之声。相形之下,记忆中的绿皮火车显得有些拙劣了,混浊难闻的气息,吵吵嚷嚷的南腔北调,或卧或斜的姿态,简陋俗艳的衣着,还有在人缝里穿梭的小推车,不停地兜售矿泉水与瓜子零食——一切的一切,似乎让你无法忍受了。终于有一段时间,我往返于合肥与芜湖之间,坐的是绿皮火车,重新品味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是乘务员不一样,他们立在车厢门前,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叫喊着某某车次,老母亲一样叮嘱每一个上车的旅客:别上错了!车厢里的氛围也不一样,绝不似高铁的冷清,总是有人哇啦哇啦说话,南腔北调。面对面的人像邻居一样话家常,人们之间没有什么防备心理,遇见你就如遇见了久别的熟人。绿皮火车上经常看见漂亮的年轻女孩,她们显然化了妆,淡淡的,恰好衬出唇红齿白,衣裙的面料劣质而僵硬,却一点也不妨碍她们青春的张扬。望着她们,车厢明丽了,窗外的原野也绚烂起来,那漫长的旅程不再枯燥难耐。这时候,我总是庆幸自己也是女性,可以肆无忌惮地欣赏她们的美,盯着她们的一颦一笑,发自内心地赞叹:青春是多么美好!假如手持油画笔,该怎么描绘她们醉人的小酒窝呢?
有时候,会想起盲人作家周云蓬的《绿皮火车》,他经常坐绿皮火车去远游,喜欢听车上人讲话,听一段就“换一个台”——看不见的他,极会听,能听出一页页的画面,他是当作收听电视节目了。我也尝试过闭上眼睛,静静地收听来自各方的聊天,稍稍有点耐心,便能听到完整的故事。那北方人洪亮的嗓门,她以为是向邻座的人倾诉,实际上是向全车厢的人广播了。
绿皮火车上的推销员让人心烦,他们在闷罐子似的空间里穿来穿去,舌绽莲花般推销吃食与小家电,几乎所有的人都垂眉低眼不去理会。而他们尬聊的水平是一等一的,自问自答,调侃自如,不免让人生出几分厌烦。有一次,坐的是从呼和浩特发出的车,有黑壮的汉子手持包装精美的皮囊酒,一个人说说唱唱好不热闹,响应者寥寥,有些替他不值。后来,我觉得胸闷,到餐车那儿透口气,恰好听到这个年轻的黑汉与一个中年妇人聊天,中年妇人劝他加把劲,赶紧把媳妇娶了,他苦笑:房子买成了,在攒彩礼钱呢。
原来是生活把他逼成这么油腻,该有多少次的冷淡与拒绝,把他打磨成如此无畏尴尬与轻视的人。
绿皮火车,是最接近尘世的集装箱了,如果你想认识真正的生活,认识热气腾腾的生活,坐几趟就知道了。
很多人小时候见到绿皮火车就激动,那悠长的鸣笛声,会将他们的梦想拽向远方。我却一点也不,因为我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绿皮火车就如我儿时的玩伴一样,熟得不能再熟,就连夜间凄厉的吼叫声,也成了催眠的小夜曲。
上个世纪,皖南小县城的火车站简陋极了,候车室是一长溜的简易工棚,天蓝色石棉瓦的顶,暗灰的砖墙,几排长长的木头椅子,磨得锃明瓦亮。候车的人多,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千姿百态,大人笑谈,孩子哭闹嬉戏,人声鼎沸差一点掀了顶。忽而穿绿制服的列车员大吼一声:××车检票了!一时间,呼啦啦涌起一群人,奋力奔向狭小的铁闸门,小孩子被拉得跌跌撞撞。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排队的意识,也没有按号入座的习惯,只有冲锋向前才能找到座位,每一次上车都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役。
对我们而言,上月台有两条路,一条路隐在油菜花田间,穿过黄灿灿的原野,奋力冲上陡峭的护坡,便是月台了。还有一条路是火车站的一扇隐秘的侧门,常年累月是锁着的,却难不倒皮孩子,钻门缝或者翻门头,小菜一碟。月台上可以踢毽子、跳房子,最有趣的还是走铁轨,赛着走,看谁长久不掉下来。这么玩,家长是不依的,他们举出谁谁谁命丧火车轮下的惨剧,血腥的描绘,只能吓唬一下胆小的丫头。我们小时候的玩具极少,月台与铁轨是我们的开心果。
最初对火车站有了朦胧的感觉,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教风是极好的,即使是实习老师,也认真谦和,善待每一个学生。放学后,还会给孩子们补习,全免费的,不会收一分钱。我已然忘记了两位实习老师的名字,翻出发黄的老照片,他们坐在中间,二十多个同学围着他们,在人民照相馆。一个拿掉近视眼镜,鼓突着双眼,一个天然浓黑卷发,脸上是生涩的笑意。一学期结束后,我们几个学生送他俩上火车,手里紧紧攥着小本子,小本子的扉页上是实习老师的临别赠言,墨迹未干,我们攥着它,似乎攥着未来与希望。火车隆隆地开动了,我们拼命地挥着小本子,几个男生唱起了《梦驼铃》,女生有人哭出了声。第一次感觉到,火车站是人生离别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师生天各一方,我们不知道实习老师现状怎样,同学们彼此之间也失去了音信。只有绿皮火车偶尔出现在视野中,像一根细线,串起记忆的散珠。
高铁通车以后,绿皮火车几乎从我们眼皮底下消失了。踏上高铁的人,大多衣冠楚楚,安静自持,很少有喧闹之声。相形之下,记忆中的绿皮火车显得有些拙劣了,混浊难闻的气息,吵吵嚷嚷的南腔北调,或卧或斜的姿态,简陋俗艳的衣着,还有在人缝里穿梭的小推车,不停地兜售矿泉水与瓜子零食——一切的一切,似乎让你无法忍受了。终于有一段时间,我往返于合肥与芜湖之间,坐的是绿皮火车,重新品味不一样的感觉。
首先是乘务员不一样,他们立在车厢门前,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叫喊着某某车次,老母亲一样叮嘱每一个上车的旅客:别上错了!车厢里的氛围也不一样,绝不似高铁的冷清,总是有人哇啦哇啦说话,南腔北调。面对面的人像邻居一样话家常,人们之间没有什么防备心理,遇见你就如遇见了久别的熟人。绿皮火车上经常看见漂亮的年轻女孩,她们显然化了妆,淡淡的,恰好衬出唇红齿白,衣裙的面料劣质而僵硬,却一点也不妨碍她们青春的张扬。望着她们,车厢明丽了,窗外的原野也绚烂起来,那漫长的旅程不再枯燥难耐。这时候,我总是庆幸自己也是女性,可以肆无忌惮地欣赏她们的美,盯着她们的一颦一笑,发自内心地赞叹:青春是多么美好!假如手持油画笔,该怎么描绘她们醉人的小酒窝呢?
有时候,会想起盲人作家周云蓬的《绿皮火车》,他经常坐绿皮火车去远游,喜欢听车上人讲话,听一段就“换一个台”——看不见的他,极会听,能听出一页页的画面,他是当作收听电视节目了。我也尝试过闭上眼睛,静静地收听来自各方的聊天,稍稍有点耐心,便能听到完整的故事。那北方人洪亮的嗓门,她以为是向邻座的人倾诉,实际上是向全车厢的人广播了。
绿皮火车上的推销员让人心烦,他们在闷罐子似的空间里穿来穿去,舌绽莲花般推销吃食与小家电,几乎所有的人都垂眉低眼不去理会。而他们尬聊的水平是一等一的,自问自答,调侃自如,不免让人生出几分厌烦。有一次,坐的是从呼和浩特发出的车,有黑壮的汉子手持包装精美的皮囊酒,一个人说说唱唱好不热闹,响应者寥寥,有些替他不值。后来,我觉得胸闷,到餐车那儿透口气,恰好听到这个年轻的黑汉与一个中年妇人聊天,中年妇人劝他加把劲,赶紧把媳妇娶了,他苦笑:房子买成了,在攒彩礼钱呢。
原来是生活把他逼成这么油腻,该有多少次的冷淡与拒绝,把他打磨成如此无畏尴尬与轻视的人。
绿皮火车,是最接近尘世的集装箱了,如果你想认识真正的生活,认识热气腾腾的生活,坐几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