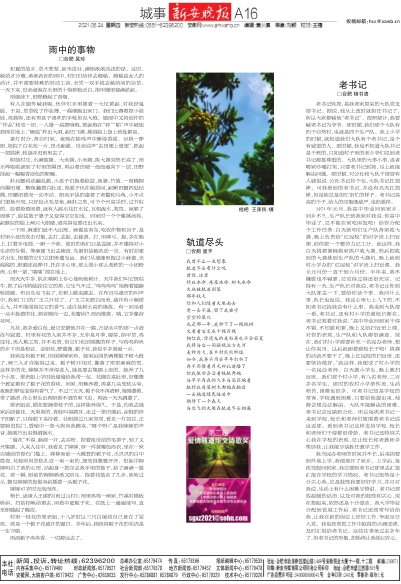发布日期:
雨中的事物
□合肥吴玲
初夏的故乡,草木葱翠,新禾茁壮,满眼浓浓浅浅的绿。这时,秧苗才分蘖,淅淅沥沥的雨中,村妇们结伴去薅秧。薅秧是女人的活计,并不需要特殊的劳动工具,全凭一双手拔去秧苗间的杂草。一天下来,母亲浸泡在水里的十指肿胀泛白,指甲缝里塞满淤泥。
雨继续下,田野腾起了青烟。
有人在窗外喊我呢,伙伴们手里捧着一大坨黄泥,对我扮鬼脸。于是,草草收了作业簿,一溜烟跑出家门。我们比赛着捏小娃娃、鸡猫狗,还有男孩子喜欢的手枪坦克大炮。嬉闹中又将创作的“作品”和成一团,一人掰一块掼响炮,黄泥炮在“砰”“啪”声中被使劲摔在地上,“碗底”炸出大洞,泥巴飞溅,溅得脸上身上到处都是。
掌灯时分,各自归家。夜晚在蛙鸣声中睡得香甜。早晨一睁眼,场院下白花花一片,田水痴涨。母亲说声“去田埂上望望”,抓起一把铁锹,转身冲进雨里去了。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大米塘、小米塘、陈大塘突然长高了,雨水哗啦啦滚到了村里的隰田,再沿着田埂一级级漫向下一层,田野挂起一幅幅青绿色的帐幔。
虾兵蟹将活蹦乱跳,小孩子们抱着脸盆、鱼篓、竹篮,一窝蜂拥向隰田埂。鲫鱼翻着白肚皮,青混子伏在秧苗间,泥鳅田蟹四处钻爬,田螺闭着壳一动不动。眼疾手快的逮着了老鳖和乌龟,小不点们望鱼兴叹,只好捡点毛草鱼、麻虾之类,可个个兴高采烈,过节似的。捡着抢着闹着,就有人踩水花打水仗,互相泼水,笑骂。疯够了闹够了,脸盆篮子篓子又变得空空如也。回家时一个个像落汤鸡,泥猴似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清亮得也要汪出水来。
一下雨,麻雀们就不大出窝。麻雀是害鸟,吃农作物和谷子,是村里小孩的攻击对象,去打,去捉,去偷袭。打,用弹弓。捉,多在晚上,打着手电筒,一瞅一个准。彼时的我们只是逞强,并不懂得对小生命的怜惜。等麻雀飞出去捕食,鸟蛋很快被洗劫一空。有时幼雀才出生,倒霉的它们立即惨遭厄运。我们从墙缝里掏过小麻雀,光溜溜的,眼睛还没睁开,托在手心里,那么弱小那么柔软的一小团粉肉,心里一紧,“噗嗤”掉在地上。
雨天天牛多,趴在楮树上专心地吮吸树汁。天牛我们叫它斑牯牛,抓了后用棉线拴住它的角,它生气不过,“呜呜呜呜”地舞着翅膀转圆圈。布谷鸟也飞来了,在树上跳来跳去。在布谷鸟凄厉的叫声中,我家门口的广玉兰开花了。广玉兰花肥白而美,盛开有小碗那么大,并不能闻得见它的香气,或许是树太高的缘故。有一回呆看一朵半拢着的花,颔首侧向一边,花瓣因久雨而微黄。咦,它多像荷花呵。
凡花,我多爱白色,爱它安静地开在一隅,万绿丛中的那一点清涩与寂寞。村里有花的人家并不多,无非是月季、蜀葵、指甲草、鸡冠花、美人蕉之类,并不名贵,但它们花团锦簇的样子,与鸡鸣狗吠的乡下很是相宜。金银花、野蔷薇、栀子花,我似乎多喜爱一点。
我家没有栀子树,但我婶婶家有。她家后园的两棵栀子树大极了,两三人才合抱得过来。栀子树开花时,像落了密密麻麻的雪。这样多的花,婶婶并不舍得送人,她是要去集镇上卖的。她养了九个小孩。翠表姐上学时就偷偷给我带一包。花搁在桌肚里,好像整个教室都有了栀子花的香味。回家,用碗养着,再拿几朵放枕头旁,夜晚的梦也变得有香气了。不过三五天,栀子花不再清鲜,慢慢萎黄,带了锈渍,花心里生出肉眼看不清的黑飞虫。再就一天天凋萎了。
翠表姐说,插花要摘带枝子的,这样能养得久。于是,约我去她家后园偷花。天黑黑的,青蛙叫得震耳,走过一条田埂后,凉鞋的绊子扭断了,只得脱下来拎着。壮胆绕过几家邻居,看见一灯如豆,正要跨进院门,昏暗中一条大狗向我蹿来。“哪个呀?”是我婶婶的声音,她刚巧出来倒涮锅水。
“偷花”不得,脑洞一开,去买呀。捏着祖母给的毛票子,到了义兴集镇。人来人往中,我看见了婶婶,穿一件黄褐色雨衣,坐在一家店铺前的青石门槛上。婶婶面前一大簸箕的栀子花,水灵灵的白中隐青,花苞则用草秸扎成一束一束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忸怩中婶婶明白了我的心思,站起身一把夺去我手里的篮子,装了满满一篮花。那一瞬,眼前的婶婶熟悉又陌生。抱着花篮走了几步,我转过头,瞥见婶婶的发髻旁斜插着一朵栀子花。
婶婶87岁时无疾而终。
稍长,读唐人王建的《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在纸上一遍遍地写,直至眼睛起了酸涩。
村里一枝花的翠表姐,十八岁时以三尺白绫将自己悬在了屋梁。那是一个栀子花盛开的夏日。多年后,我晓得栀子花的花语是一生守候。
雨浥栀子冉冉香。一切都远去了。
初夏的故乡,草木葱翠,新禾茁壮,满眼浓浓浅浅的绿。这时,秧苗才分蘖,淅淅沥沥的雨中,村妇们结伴去薅秧。薅秧是女人的活计,并不需要特殊的劳动工具,全凭一双手拔去秧苗间的杂草。一天下来,母亲浸泡在水里的十指肿胀泛白,指甲缝里塞满淤泥。
雨继续下,田野腾起了青烟。
有人在窗外喊我呢,伙伴们手里捧着一大坨黄泥,对我扮鬼脸。于是,草草收了作业簿,一溜烟跑出家门。我们比赛着捏小娃娃、鸡猫狗,还有男孩子喜欢的手枪坦克大炮。嬉闹中又将创作的“作品”和成一团,一人掰一块掼响炮,黄泥炮在“砰”“啪”声中被使劲摔在地上,“碗底”炸出大洞,泥巴飞溅,溅得脸上身上到处都是。
掌灯时分,各自归家。夜晚在蛙鸣声中睡得香甜。早晨一睁眼,场院下白花花一片,田水痴涨。母亲说声“去田埂上望望”,抓起一把铁锹,转身冲进雨里去了。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大米塘、小米塘、陈大塘突然长高了,雨水哗啦啦滚到了村里的隰田,再沿着田埂一级级漫向下一层,田野挂起一幅幅青绿色的帐幔。
虾兵蟹将活蹦乱跳,小孩子们抱着脸盆、鱼篓、竹篮,一窝蜂拥向隰田埂。鲫鱼翻着白肚皮,青混子伏在秧苗间,泥鳅田蟹四处钻爬,田螺闭着壳一动不动。眼疾手快的逮着了老鳖和乌龟,小不点们望鱼兴叹,只好捡点毛草鱼、麻虾之类,可个个兴高采烈,过节似的。捡着抢着闹着,就有人踩水花打水仗,互相泼水,笑骂。疯够了闹够了,脸盆篮子篓子又变得空空如也。回家时一个个像落汤鸡,泥猴似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清亮得也要汪出水来。
一下雨,麻雀们就不大出窝。麻雀是害鸟,吃农作物和谷子,是村里小孩的攻击对象,去打,去捉,去偷袭。打,用弹弓。捉,多在晚上,打着手电筒,一瞅一个准。彼时的我们只是逞强,并不懂得对小生命的怜惜。等麻雀飞出去捕食,鸟蛋很快被洗劫一空。有时幼雀才出生,倒霉的它们立即惨遭厄运。我们从墙缝里掏过小麻雀,光溜溜的,眼睛还没睁开,托在手心里,那么弱小那么柔软的一小团粉肉,心里一紧,“噗嗤”掉在地上。
雨天天牛多,趴在楮树上专心地吮吸树汁。天牛我们叫它斑牯牛,抓了后用棉线拴住它的角,它生气不过,“呜呜呜呜”地舞着翅膀转圆圈。布谷鸟也飞来了,在树上跳来跳去。在布谷鸟凄厉的叫声中,我家门口的广玉兰开花了。广玉兰花肥白而美,盛开有小碗那么大,并不能闻得见它的香气,或许是树太高的缘故。有一回呆看一朵半拢着的花,颔首侧向一边,花瓣因久雨而微黄。咦,它多像荷花呵。
凡花,我多爱白色,爱它安静地开在一隅,万绿丛中的那一点清涩与寂寞。村里有花的人家并不多,无非是月季、蜀葵、指甲草、鸡冠花、美人蕉之类,并不名贵,但它们花团锦簇的样子,与鸡鸣狗吠的乡下很是相宜。金银花、野蔷薇、栀子花,我似乎多喜爱一点。
我家没有栀子树,但我婶婶家有。她家后园的两棵栀子树大极了,两三人才合抱得过来。栀子树开花时,像落了密密麻麻的雪。这样多的花,婶婶并不舍得送人,她是要去集镇上卖的。她养了九个小孩。翠表姐上学时就偷偷给我带一包。花搁在桌肚里,好像整个教室都有了栀子花的香味。回家,用碗养着,再拿几朵放枕头旁,夜晚的梦也变得有香气了。不过三五天,栀子花不再清鲜,慢慢萎黄,带了锈渍,花心里生出肉眼看不清的黑飞虫。再就一天天凋萎了。
翠表姐说,插花要摘带枝子的,这样能养得久。于是,约我去她家后园偷花。天黑黑的,青蛙叫得震耳,走过一条田埂后,凉鞋的绊子扭断了,只得脱下来拎着。壮胆绕过几家邻居,看见一灯如豆,正要跨进院门,昏暗中一条大狗向我蹿来。“哪个呀?”是我婶婶的声音,她刚巧出来倒涮锅水。
“偷花”不得,脑洞一开,去买呀。捏着祖母给的毛票子,到了义兴集镇。人来人往中,我看见了婶婶,穿一件黄褐色雨衣,坐在一家店铺前的青石门槛上。婶婶面前一大簸箕的栀子花,水灵灵的白中隐青,花苞则用草秸扎成一束一束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忸怩中婶婶明白了我的心思,站起身一把夺去我手里的篮子,装了满满一篮花。那一瞬,眼前的婶婶熟悉又陌生。抱着花篮走了几步,我转过头,瞥见婶婶的发髻旁斜插着一朵栀子花。
婶婶87岁时无疾而终。
稍长,读唐人王建的《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在纸上一遍遍地写,直至眼睛起了酸涩。
村里一枝花的翠表姐,十八岁时以三尺白绫将自己悬在了屋梁。那是一个栀子花盛开的夏日。多年后,我晓得栀子花的花语是一生守候。
雨浥栀子冉冉香。一切都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