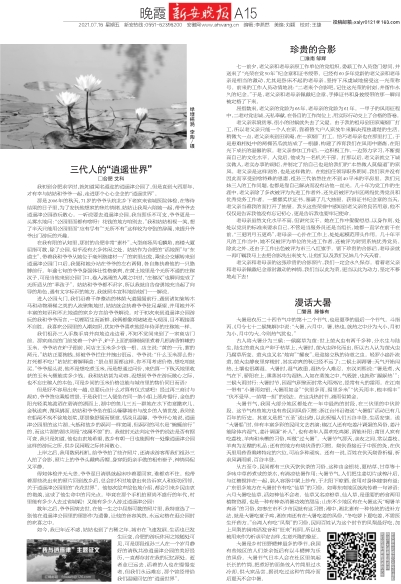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三代人的“逍遥世界”
□合肥艾科
我初到合肥求学时,就知道闻名遐迩的逍遥津公园了,但是直到大四那年,才有幸与姑姑和爷爷一起,走进那个心心念念的“逍遥世界”。
那是2006年的秋天,71岁的爷爷从皖北乡下老家来省城医院体检,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为了安抚他想家的焦灼情绪,姑姑让我周六陪她一起,带爷爷去逍遥津公园游玩散心。一听说要去逍遥津公园,我当即乐不可支,爷爷更是一头雾水地问:“公园里面都有啥呀?花钱的地方咱别去。”我和姑姑相视一笑,想了半天只能用公园里面“应有尽有”“无所不有”这样较为夸张的辞藻,来提升爷爷出门游玩的兴趣。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那时的合肥非常“素朴”,大型商场凤毛麟角,高楼大厦屈指可数,除了公园,似乎没有太多休闲之处。姑姑作为合肥的“活地图”与“东道主”,带着我和爷爷从她位于亳州路建材一厂的家里出发,乘坐公交辗转来到逍遥津公园门口后,我便和她分站在爷爷的左右两侧,各自搀扶着他的一只胳膊前行。年逾七旬的爷爷身强体壮性格豪爽,在黄土地里是个无所不通的庄稼汉子,可是当他来到公园门口、卷入汹涌的人潮之中时,“庄稼汉”也瞬间变成了无所适从的“乖孩子”。姑姑和爷爷都不识字,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了向导的角色,遇有文字标识的地方,我就照本宣科地给他们一一解说。
进入公园大门,我们沿着干净整洁的林荫大道缓缓前行,遇到诸如旋转木马和动物滑梯之类的人流聚集地时,姑姑就会扶着爷爷驻足凝望,并用她并不丰富的知识和不太地道的家乡方言给爷爷解说。对于初次来到逍遥津公园游玩的我和爷爷而言,一切都陌生而新鲜,我俩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目不暇接喜不自胜。我喜欢公园里的人潮如织,犹如爷爷喜欢他经年侍弄的庄稼地一样。
我们祖孙三人手挽手肩并肩地边走边看,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家商店门前。那家商店的门前放着一个炉子,炉子上面的钢精锅里煮着几根清香鲜嫩的玉米。爷爷站在炉子跟前,问店主玉米多少钱一根。店主说:“黄的一元,紫的两元。”姑姑正要掏钱,却被爷爷拦住并拽出很远。爷爷说:“什么玉米那么贵?打死都不吃!”姑姑忙着解释道:“景点里面都这样,你不用考虑价格,想吃咱就买。”爷爷摇头说,他不是想吃煮玉米,而是想通过问价,来估算一下秋天地里收获的玉米大概能卖多少钱。我和姑姑甚为动容,没想到爷爷在游玩散心之际,也不忘庄稼人的本色,可是乡间的玉米价格岂能与城市里的售价同日而语?
但是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总要玩点什么才算有仪式感吧?经过再三商讨与规劝,爷爷答应乘船赏景,于是我们三人便坐在同一条小船上荡舟慢行,金色的阳光轻柔地泼洒在碧清的湖面上,湖中的鱼儿三五一群地在水下恣意撒欢儿。金秋送爽,微风拂面,姑姑和爷爷坐在船头畅聊城市与故乡的人情世故,我则坐在船尾不疾不徐地划桨,那景象舒缓而惬意,恬淡且温馨。爷爷开心地说,逍遥津公园里的这片湖,大抵和故乡的涡河一样宽阔,但涡河的河水是“蜿蜒前行”的,而这片湖的湖水则是“波澜不惊”的。我彼时无法判定爷爷的说法是否有据可查,我只是知道,他也由衷地希望,故乡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处像逍遥津公园这样的游玩之所,供乡民闲暇之际休闲散心。
上岸之后,我用数码相机,给爷爷拍了些许照片,还请求游客帮我们祖孙三人拍了合影,照片上的爷爷头戴鸭舌帽,身穿奶奶亲手做的粗布褂子,神情局促又平静。
得知体检并无大恙,爷爷翌日清晨就起床吵着要回家,谁都劝不住。他带着那些洗出来的照片回到故乡后,总会时不时地拿出来告诉家人和街坊四邻,关于逍遥津公园里的“花花世界”。他每次绘声绘色地介绍,都会引来乡民由衷的艳羡,这成了他生命中的闪光点。毕竟在那个手机拍照尚不盛行的年代,村里能有多少人去过省城呢?又能有多少人游过逍遥津公园?
数年之后,爷爷因病去世,在他一生之中屈指可数的照片里,我特意选了一张他在逍遥津公园里的留影作为遗像,让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逛公园时的欢喜之中。
如今,我已年近不惑,姑姑也到了古稀之年,城市在飞速发展,生活也已发生巨变,合肥的游玩休闲之地随处可见,可是那段祖孙三人在一个岁月静好的清秋共游逍遥津公园的美好经历,一直都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逝者业已远去,活着的人也在慢慢变老,但我们永远难忘,那个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回忆的“逍遥世界”。
我初到合肥求学时,就知道闻名遐迩的逍遥津公园了,但是直到大四那年,才有幸与姑姑和爷爷一起,走进那个心心念念的“逍遥世界”。
那是2006年的秋天,71岁的爷爷从皖北乡下老家来省城医院体检,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为了安抚他想家的焦灼情绪,姑姑让我周六陪她一起,带爷爷去逍遥津公园游玩散心。一听说要去逍遥津公园,我当即乐不可支,爷爷更是一头雾水地问:“公园里面都有啥呀?花钱的地方咱别去。”我和姑姑相视一笑,想了半天只能用公园里面“应有尽有”“无所不有”这样较为夸张的辞藻,来提升爷爷出门游玩的兴趣。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那时的合肥非常“素朴”,大型商场凤毛麟角,高楼大厦屈指可数,除了公园,似乎没有太多休闲之处。姑姑作为合肥的“活地图”与“东道主”,带着我和爷爷从她位于亳州路建材一厂的家里出发,乘坐公交辗转来到逍遥津公园门口后,我便和她分站在爷爷的左右两侧,各自搀扶着他的一只胳膊前行。年逾七旬的爷爷身强体壮性格豪爽,在黄土地里是个无所不通的庄稼汉子,可是当他来到公园门口、卷入汹涌的人潮之中时,“庄稼汉”也瞬间变成了无所适从的“乖孩子”。姑姑和爷爷都不识字,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了向导的角色,遇有文字标识的地方,我就照本宣科地给他们一一解说。
进入公园大门,我们沿着干净整洁的林荫大道缓缓前行,遇到诸如旋转木马和动物滑梯之类的人流聚集地时,姑姑就会扶着爷爷驻足凝望,并用她并不丰富的知识和不太地道的家乡方言给爷爷解说。对于初次来到逍遥津公园游玩的我和爷爷而言,一切都陌生而新鲜,我俩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目不暇接喜不自胜。我喜欢公园里的人潮如织,犹如爷爷喜欢他经年侍弄的庄稼地一样。
我们祖孙三人手挽手肩并肩地边走边看,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家商店门前。那家商店的门前放着一个炉子,炉子上面的钢精锅里煮着几根清香鲜嫩的玉米。爷爷站在炉子跟前,问店主玉米多少钱一根。店主说:“黄的一元,紫的两元。”姑姑正要掏钱,却被爷爷拦住并拽出很远。爷爷说:“什么玉米那么贵?打死都不吃!”姑姑忙着解释道:“景点里面都这样,你不用考虑价格,想吃咱就买。”爷爷摇头说,他不是想吃煮玉米,而是想通过问价,来估算一下秋天地里收获的玉米大概能卖多少钱。我和姑姑甚为动容,没想到爷爷在游玩散心之际,也不忘庄稼人的本色,可是乡间的玉米价格岂能与城市里的售价同日而语?
但是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总要玩点什么才算有仪式感吧?经过再三商讨与规劝,爷爷答应乘船赏景,于是我们三人便坐在同一条小船上荡舟慢行,金色的阳光轻柔地泼洒在碧清的湖面上,湖中的鱼儿三五一群地在水下恣意撒欢儿。金秋送爽,微风拂面,姑姑和爷爷坐在船头畅聊城市与故乡的人情世故,我则坐在船尾不疾不徐地划桨,那景象舒缓而惬意,恬淡且温馨。爷爷开心地说,逍遥津公园里的这片湖,大抵和故乡的涡河一样宽阔,但涡河的河水是“蜿蜒前行”的,而这片湖的湖水则是“波澜不惊”的。我彼时无法判定爷爷的说法是否有据可查,我只是知道,他也由衷地希望,故乡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处像逍遥津公园这样的游玩之所,供乡民闲暇之际休闲散心。
上岸之后,我用数码相机,给爷爷拍了些许照片,还请求游客帮我们祖孙三人拍了合影,照片上的爷爷头戴鸭舌帽,身穿奶奶亲手做的粗布褂子,神情局促又平静。
得知体检并无大恙,爷爷翌日清晨就起床吵着要回家,谁都劝不住。他带着那些洗出来的照片回到故乡后,总会时不时地拿出来告诉家人和街坊四邻,关于逍遥津公园里的“花花世界”。他每次绘声绘色地介绍,都会引来乡民由衷的艳羡,这成了他生命中的闪光点。毕竟在那个手机拍照尚不盛行的年代,村里能有多少人去过省城呢?又能有多少人游过逍遥津公园?
数年之后,爷爷因病去世,在他一生之中屈指可数的照片里,我特意选了一张他在逍遥津公园里的留影作为遗像,让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逛公园时的欢喜之中。
如今,我已年近不惑,姑姑也到了古稀之年,城市在飞速发展,生活也已发生巨变,合肥的游玩休闲之地随处可见,可是那段祖孙三人在一个岁月静好的清秋共游逍遥津公园的美好经历,一直都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逝者业已远去,活着的人也在慢慢变老,但我们永远难忘,那个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回忆的“逍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