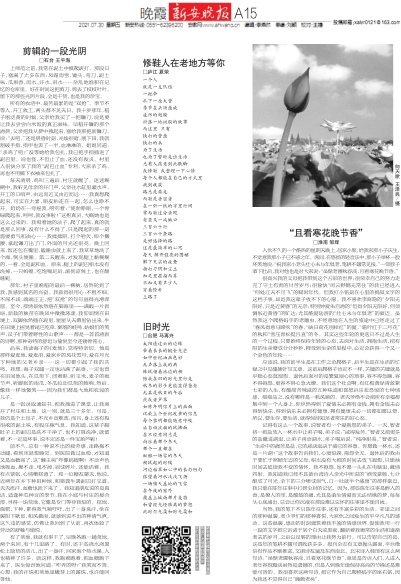发布日期:
剪辑的一段光阴
□石台王平海
上师范之前,我常在泥土中摸爬滚打。那段日子,塞满了太多东西:风霜雨雪,锄头、弯刀,泥土味、瓜果香,雨水、汗水、泪水……杂乱地堆积在记忆的仓库里。好在时间这把剪刀,剪去了枝枝叶叶,留下的那些光阴片段,全是干货,也是我的珍宝。
所有的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是“双抢”。季节不等人,开工收工,两头都不见天日。我十岁那年,稻子刚泛黄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把镰刀,说是要让我去尝尝白米饭的真正滋味。早稻开镰的那个清晨,父亲把我从梦中拽起来,塞给我那把新镰刀,说:“去吧。”还是晨昏时刻,光线很暗,刚下田,我就割破手指,指甲也丢了一半,血淋淋的。姐姐问道:“杀鸡了吧?”没等她给我包扎,我已把手指插进了泥巴里。说也怪,不但止了血,还没有发炎。村里人很快分享了我的“泥巴止血”专利,大家杀了鸡,再也不用撕下衣袖来包扎了。
每天清晨,鸡叫三遍后,村庄就醒了。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母亲的开门声,父亲往水缸里灌水声,开工的口哨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我真想爬起来,可实在太累,眼皮粘连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奶奶在一旁摇我,唠叨着:“使劲睁眼,一个骨碌爬起来,呵呵,就没事啦!”这招真灵,大概她也是这么过来的。我照着她的法子,爬了起来,真的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不得了,只是爬起的那一刻需要勇气和决心……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拿起镰刀出了门,外面的月光还很亮。晚上回来,饭还包在嘴里,瞌睡虫就上来了,我草草地洗了个澡,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腿上黏糊糊的,一看,全是泥和血。原来,腿上的泥巴根本没有洗掉,一只蚂蝗,吃饱喝足后,滚到凉凳上,也在酣睡呢。
那年,村子里晚稻的最后一棵秧,居然轮到了我,我感到莫名的兴奋。我栽得很用心:不粗不细,不深不浅,端端正正,把“双抢”的句号画得光滑浑圆。至今,那情景依然烙在脑海里——满畈一片新绿,新栽的秧苗在晚风中微微荡漾,我仰面倒在田埂上,双脚依然插在泥里,星星从天幕里钻出来,牛在田埂上摇晃着尾巴吃草,寥落的蛙鸣,姑娘们的笑声,汉子们带着野性的山歌声……都是一首首清新的诗啊,那种奇特的舒坦与愉悦至今还镂骨铭心。
后来,我读海子的《麦地》,觉得特亲切。他是那样爱麦地,爱麦浪,爱家乡的风花雪月,爱在月光下种地的父老乡亲……这一切都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想:海子双腿一定也沾满了泥香,一定也曾在田间地头,在瓜架下,闭着眼,听玉米、麦子的拔节声,听膨胀的南瓜、冬瓜拉动瓜架的脆响,然后,像我一样地傻笑——因为我们都是大地和农民的儿子。
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拽进了课堂,让我离开了村庄和土地。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可是,我仍是个土包子,不光乡音难改,而且,身上还有股很浓的泥土味,有股庄稼气息。我知道,这辈子脚肚子上的泥巴是洗不干净了,也不打算洗净,就留着,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件宝葫芦呢!
前不久,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劳感,走路拖不动腿,看到床就想睡觉。到医院做过血检,才知道又是血糖高了,这“懒王病”咋像蚂蝗啊?不动声色地吸血,撵不走,甩不掉,剁成碎片,还能活着。我有点紧张,心情糟糕透了。和一位糖友聊天,他说,近两年在乡下种田种地,和猪粪牛粪泥巴打交道,天天流汗,血糖也就下来了。我知道朋友说的是真话,适逢种瓜种豆的季节,我在小城与村庄的接合部,寻得一块荒地,它像是专门等待我似的。挖地、施肥、下种,累得我气喘吁吁,出了一身臭汗,坐在暖阳下歇息,和风拂面,就感到说不出的神清气爽,这久违的感觉,仿佛让我回到了从前,再次体验了劳动的舒畅与愉悦。
有了菜地,我就有事干了,早晚各跑一趟菜地,两个来回,有十几里路了。有时,还干些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的活儿,出了一身汗,回家泡个热水澡,人也精神了许多。就这样,我跑着跑着,把血糖跑下来了。医生惊讶地问道:“咋弄的呀?”我笑而不答,心想:我的汗珠和菜地里嫩芽上的露珠,也许能回答他。
上师范之前,我常在泥土中摸爬滚打。那段日子,塞满了太多东西:风霜雨雪,锄头、弯刀,泥土味、瓜果香,雨水、汗水、泪水……杂乱地堆积在记忆的仓库里。好在时间这把剪刀,剪去了枝枝叶叶,留下的那些光阴片段,全是干货,也是我的珍宝。
所有的农活中,最苦最累的是“双抢”。季节不等人,开工收工,两头都不见天日。我十岁那年,稻子刚泛黄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把镰刀,说是要让我去尝尝白米饭的真正滋味。早稻开镰的那个清晨,父亲把我从梦中拽起来,塞给我那把新镰刀,说:“去吧。”还是晨昏时刻,光线很暗,刚下田,我就割破手指,指甲也丢了一半,血淋淋的。姐姐问道:“杀鸡了吧?”没等她给我包扎,我已把手指插进了泥巴里。说也怪,不但止了血,还没有发炎。村里人很快分享了我的“泥巴止血”专利,大家杀了鸡,再也不用撕下衣袖来包扎了。
每天清晨,鸡叫三遍后,村庄就醒了。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母亲的开门声,父亲往水缸里灌水声,开工的口哨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我真想爬起来,可实在太累,眼皮粘连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奶奶在一旁摇我,唠叨着:“使劲睁眼,一个骨碌爬起来,呵呵,就没事啦!”这招真灵,大概她也是这么过来的。我照着她的法子,爬了起来,真的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不得了,只是爬起的那一刻需要勇气和决心……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拿起镰刀出了门,外面的月光还很亮。晚上回来,饭还包在嘴里,瞌睡虫就上来了,我草草地洗了个澡,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腿上黏糊糊的,一看,全是泥和血。原来,腿上的泥巴根本没有洗掉,一只蚂蝗,吃饱喝足后,滚到凉凳上,也在酣睡呢。
那年,村子里晚稻的最后一棵秧,居然轮到了我,我感到莫名的兴奋。我栽得很用心:不粗不细,不深不浅,端端正正,把“双抢”的句号画得光滑浑圆。至今,那情景依然烙在脑海里——满畈一片新绿,新栽的秧苗在晚风中微微荡漾,我仰面倒在田埂上,双脚依然插在泥里,星星从天幕里钻出来,牛在田埂上摇晃着尾巴吃草,寥落的蛙鸣,姑娘们的笑声,汉子们带着野性的山歌声……都是一首首清新的诗啊,那种奇特的舒坦与愉悦至今还镂骨铭心。
后来,我读海子的《麦地》,觉得特亲切。他是那样爱麦地,爱麦浪,爱家乡的风花雪月,爱在月光下种地的父老乡亲……这一切都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想:海子双腿一定也沾满了泥香,一定也曾在田间地头,在瓜架下,闭着眼,听玉米、麦子的拔节声,听膨胀的南瓜、冬瓜拉动瓜架的脆响,然后,像我一样地傻笑——因为我们都是大地和农民的儿子。
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把我拽进了课堂,让我离开了村庄和土地。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可是,我仍是个土包子,不光乡音难改,而且,身上还有股很浓的泥土味,有股庄稼气息。我知道,这辈子脚肚子上的泥巴是洗不干净了,也不打算洗净,就留着,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件宝葫芦呢!
前不久,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劳感,走路拖不动腿,看到床就想睡觉。到医院做过血检,才知道又是血糖高了,这“懒王病”咋像蚂蝗啊?不动声色地吸血,撵不走,甩不掉,剁成碎片,还能活着。我有点紧张,心情糟糕透了。和一位糖友聊天,他说,近两年在乡下种田种地,和猪粪牛粪泥巴打交道,天天流汗,血糖也就下来了。我知道朋友说的是真话,适逢种瓜种豆的季节,我在小城与村庄的接合部,寻得一块荒地,它像是专门等待我似的。挖地、施肥、下种,累得我气喘吁吁,出了一身臭汗,坐在暖阳下歇息,和风拂面,就感到说不出的神清气爽,这久违的感觉,仿佛让我回到了从前,再次体验了劳动的舒畅与愉悦。
有了菜地,我就有事干了,早晚各跑一趟菜地,两个来回,有十几里路了。有时,还干些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的活儿,出了一身汗,回家泡个热水澡,人也精神了许多。就这样,我跑着跑着,把血糖跑下来了。医生惊讶地问道:“咋弄的呀?”我笑而不答,心想:我的汗珠和菜地里嫩芽上的露珠,也许能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