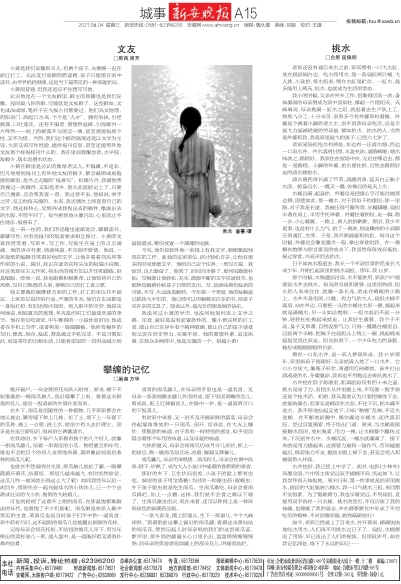发布日期:
文友
□肥西周芳
小黄是我们安徽利辛人,有两个孩子,夫妻俩一直在浙江打工。无法支付高额的借读费,孩子只能留在家中读书,由爷爷奶奶照顾,这是当下最常见的一种家庭状况。
小黄很普通,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写写他。
认识他是在一个文友群里,群主的原籍也是我们安徽。民间最八卦的群,可能就是文友群了。这些群友,文化或浅或深,笔杆子在大报小刊都耍过。他们天文地理,阴阳奇门,洒起口水来,个个是“人才”。偶有争执,引经据典,口吐莲花。还有不服者,愤愤然退群,引得群内一片哗然——网上的群莫不与现实一致,甚至更能张扬个性,实不为怪。当然,我们这个群的氛围还是以文学为主导,大家交流写作经验,提供报刊信息,甚至还能帮外地文友寄个样报样刊什么的。我在里面算懈怠者,水平低,发稿少,基本是潜水状态。
小黄在群里是公认的敦厚老实人,不偏激,不是非。但凡他看到报刊上有外地文友的稿子,都会截图或发链接到群里,是当之无愧的“报喜鸟”。机缘巧合,我请他帮我搜过一次稿件,又知是老乡,他从此就惦记上了,只要自己搜索,总会帮我查一查。我过意不去,他却说,举手之劳,反正他每天搜的。本来,我还偶尔上网查查自己的文字,他这样热心,反倒养成我投出去的稿件,像泼出去的水般,不管不问了。每当看到他头像闪动,心里就止不住地乐,报喜来了。
这一来一往的,我们的话题也逐渐宽泛,聊聊读书,聊聊写作,对有些报刊的版面要求相互探讨。小黄的文章我经常看,写家乡,写工作,写发生在身上的点点滴滴。他的语言朴素,情感纯真,不空洞不矫情。他说,一家报纸的编辑非常看好他的文字,让他多看看刘庆邦等作家的小说。彼时,我正在读刘庆邦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对这类现实主义作家,将生活的阅历加以升华和提炼,很是佩服。经他一说,我也跟着积极推荐,让他坚持自己的风格,写自己熟悉的人事,奏响自己的打工者之歌。
他主要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打工的单位并不固定。上家单位是纺织行业,严寒的冬天,他们在车间都是一身短打扮,有时还挥汗如雨。别人眼中的辛劳,他却乐呵地说,相较夏天的蒸笼,冬天是纺织工们最受欢迎的季节。他在单位吃食堂,中午难得的一小段休息时间,他或者在手机上写作,或者构思一篇篇腹稿。他所有稿件的写出、修改、保存、发送,都是通过手机完成。不是习惯如此,而是常年的出租生活,只能将屋里的一切用品减少到最低需求,哪怕放置一个薄薄的电脑。
今天,他告知我外地一家报上有我文字,顺便聊起他现在的工作。新找的这家单位,活计轻松许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琢磨文字。他给自己定个任务,一周写五篇。我惊讶,这太勤奋了。他笑了,时间完全够了,更何况勤能补拙。写稿能让他轻松、充实,源源不断的文字见诸报刊,也能挣些稿费补贴孩子日常的支出。写,就意味着有发表的可能;不写,永远就是断档。今年第一个季度,他的发稿量已抵我大半年的。他已经可以用稿费买许多的书,给孩子买许多的文具了。除此以外,最无价的便是他的快乐。
我没问过小黄的学历,也没问他如何走上文学之路。毕竟,爱好是没有前置条件的。像小黄这样的打工者,能让自己在异乡有个精神慰藉,能让自己的孩子感受到父亲在同步努力,实属不易。他的愿望朴素,追求执着,在我众多榜样中,他是无愧的一个。祝福小黄!
小黄是我们安徽利辛人,有两个孩子,夫妻俩一直在浙江打工。无法支付高额的借读费,孩子只能留在家中读书,由爷爷奶奶照顾,这是当下最常见的一种家庭状况。
小黄很普通,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写写他。
认识他是在一个文友群里,群主的原籍也是我们安徽。民间最八卦的群,可能就是文友群了。这些群友,文化或浅或深,笔杆子在大报小刊都耍过。他们天文地理,阴阳奇门,洒起口水来,个个是“人才”。偶有争执,引经据典,口吐莲花。还有不服者,愤愤然退群,引得群内一片哗然——网上的群莫不与现实一致,甚至更能张扬个性,实不为怪。当然,我们这个群的氛围还是以文学为主导,大家交流写作经验,提供报刊信息,甚至还能帮外地文友寄个样报样刊什么的。我在里面算懈怠者,水平低,发稿少,基本是潜水状态。
小黄在群里是公认的敦厚老实人,不偏激,不是非。但凡他看到报刊上有外地文友的稿子,都会截图或发链接到群里,是当之无愧的“报喜鸟”。机缘巧合,我请他帮我搜过一次稿件,又知是老乡,他从此就惦记上了,只要自己搜索,总会帮我查一查。我过意不去,他却说,举手之劳,反正他每天搜的。本来,我还偶尔上网查查自己的文字,他这样热心,反倒养成我投出去的稿件,像泼出去的水般,不管不问了。每当看到他头像闪动,心里就止不住地乐,报喜来了。
这一来一往的,我们的话题也逐渐宽泛,聊聊读书,聊聊写作,对有些报刊的版面要求相互探讨。小黄的文章我经常看,写家乡,写工作,写发生在身上的点点滴滴。他的语言朴素,情感纯真,不空洞不矫情。他说,一家报纸的编辑非常看好他的文字,让他多看看刘庆邦等作家的小说。彼时,我正在读刘庆邦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对这类现实主义作家,将生活的阅历加以升华和提炼,很是佩服。经他一说,我也跟着积极推荐,让他坚持自己的风格,写自己熟悉的人事,奏响自己的打工者之歌。
他主要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打工的单位并不固定。上家单位是纺织行业,严寒的冬天,他们在车间都是一身短打扮,有时还挥汗如雨。别人眼中的辛劳,他却乐呵地说,相较夏天的蒸笼,冬天是纺织工们最受欢迎的季节。他在单位吃食堂,中午难得的一小段休息时间,他或者在手机上写作,或者构思一篇篇腹稿。他所有稿件的写出、修改、保存、发送,都是通过手机完成。不是习惯如此,而是常年的出租生活,只能将屋里的一切用品减少到最低需求,哪怕放置一个薄薄的电脑。
今天,他告知我外地一家报上有我文字,顺便聊起他现在的工作。新找的这家单位,活计轻松许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琢磨文字。他给自己定个任务,一周写五篇。我惊讶,这太勤奋了。他笑了,时间完全够了,更何况勤能补拙。写稿能让他轻松、充实,源源不断的文字见诸报刊,也能挣些稿费补贴孩子日常的支出。写,就意味着有发表的可能;不写,永远就是断档。今年第一个季度,他的发稿量已抵我大半年的。他已经可以用稿费买许多的书,给孩子买许多的文具了。除此以外,最无价的便是他的快乐。
我没问过小黄的学历,也没问他如何走上文学之路。毕竟,爱好是没有前置条件的。像小黄这样的打工者,能让自己在异乡有个精神慰藉,能让自己的孩子感受到父亲在同步努力,实属不易。他的愿望朴素,追求执着,在我众多榜样中,他是无愧的一个。祝福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