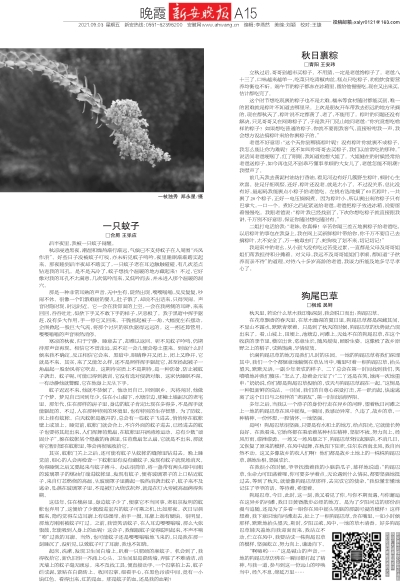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一只蚊子
□合肥王张应
后半夜里,我被一只蚊子闹醒。
秋凉浸透黑夜,潮湿和燥热渐行渐远,气候已不支持蚊子在人周围“兴风作浪”。好些日子没被蚊子叮咬,亦未听见蚊子鸣吟,夜里睡眠渐渐踏实起来。那夜睡到后半夜却不踏实了,一只蚊子老在耳边触触碰碰,有几次差点钻进我的耳孔。是不是天冷了,蚊子想找个温暖的地方藏起来?不过,它好像对我的耳孔不太满意,几次低吟而来,又低吟而去,并未进入那个温暖的洞穴。
那是一种非常耳熟的声音,无中生有,陡然出现,嘤嘤嗡嗡,反反复复,吵闹不休。很像一个饥饿难耐的婴儿,肚子饿了,却说不出话来,只得哭闹。声音时隐时现,时远时近。它一会在我仰面的上空,一会在我两侧的耳畔,来来回回,吞吞吐吐,似欲下手又不敢下手的样子,厌恶极了。我于黑暗中挥手驱赶,没有多大作用,手一停它又回来。干脆扬起被子一角,大幅度左右摆动,企图掀起一股巨大气流,将那个讨厌的家伙驱得远远的。这一招还算管用,嘤嘤嗡嗡的声音果然消停。
寒凉的秋夜,归于宁静。睡意去了,却难以返回。听不见蚊子吟鸣,仍期待那声音再现。相信它不曾走远,说不定一会儿便会卷土重来。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不确定,反正相信它会来。黑暗中,眼睛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它就是不来。其实,来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挥手驱赶它,甚至扬起被子一角扇起一股劲风将它吹走。这期待实质上不是期待,是一种防备,防止被蚊子袭击。蚊子呢,可能已得到教训,它没有选对侵袭对象。这家伙睡眠不深,一有动静他就警醒,它在他身上无从下手。
蚊子迟迟不来,他就不恭候了。他动员自己,回到眠乡。天将亮时,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年少,住在小山脚下,水塘岸边,那幢土墙泥瓦的老宅里。那年代,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身边的蚊子肯定比现在多得多,不是挥手就能驱赶的。不过,人在那种特别的环境里,也有特别的生存智慧。为了防蚊,床上挂有蚊帐。白天蚊帐是敞开的,总会有一些蚊子飞进去,悄悄停在蚊帐壁上或顶上。睡觉前,蚊帐门就会合上,不许外面的蚊子进去,已经进去的蚊子也要将其赶出来,人们挥舞芭蕉扇,在蚊帐里开展清场运动。总有少数“顽固分子”,躲在蚊帐某个隐蔽的角落里,任芭蕉扇怎么扇,它就是不出来,那就将它暂时留在蚊帐里,等会再彻底收拾它。
其实,蚊帐门关上之后,还可能有蚊子从蚊帐的缝隙里钻进去。晚上睡觉前,细心的人会再检查一下蚊帐里有没有藏蚊子,发现有蚊子就现场消灭,免得睡倒之后又要起来与蚊子搏斗。办法很简单,将一盏带有两头细中间粗的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端进蚊帐里,发现有蚊子,便将玻璃罩子的上口贴近蚊子,来自灯芯燃烧的高温,从玻璃罩子里腾起一股热浪袭击蚊子,蚊子来不及逃命,坠落在玻璃罩子里,不是被灯火烧成灰烬,就是在灯火旁被高温烤得焦糊。
这些年,住在楼房里,身边蚊子少了,便拿它不当回事,老祖宗发明的蚊帐也弃用了,这便给了少数溜进室内的蚊子可乘之机,比如那夜。次日早晨醒来,隐约觉得左边耳廓上有些瘙痒,抬手一摸,耳廓上端有硬块。很明显,那地方刚刚被蚊子叮过。之前,我曾笑话蚊子,在人耳边嘤嘤嗡嗡,那么大张旗鼓,怎能吸到人身上的血呢?这会子,我佩服蚊子变得聪明起来,不声不响“吻”过我的耳廓。当然,也可能蚊子还是嘤嘤嗡嗡地飞来的,只是我在那一刻睡沉了,没听见,以致蚊子叮了耳廓,我也不知晓。
起床,洗漱,发现卫生间白墙上,趴着一只肥硕的麻蚊子。机会到了,我得收拾它,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卫生间里是瓷砖墙,弄脏了不难清洁,消灭墙上的蚊子毫无顾忌。来不及找工具,便直接动手,一个巴掌拍上去,蚊子烂成泥,紧贴在白瓷砖上。收回巴掌,细看手心,在黑色污渍中间,竟有一小块红色。看得出来,红的是血。那是蚊子的血,还是我的血呢?
后半夜里,我被一只蚊子闹醒。
秋凉浸透黑夜,潮湿和燥热渐行渐远,气候已不支持蚊子在人周围“兴风作浪”。好些日子没被蚊子叮咬,亦未听见蚊子鸣吟,夜里睡眠渐渐踏实起来。那夜睡到后半夜却不踏实了,一只蚊子老在耳边触触碰碰,有几次差点钻进我的耳孔。是不是天冷了,蚊子想找个温暖的地方藏起来?不过,它好像对我的耳孔不太满意,几次低吟而来,又低吟而去,并未进入那个温暖的洞穴。
那是一种非常耳熟的声音,无中生有,陡然出现,嘤嘤嗡嗡,反反复复,吵闹不休。很像一个饥饿难耐的婴儿,肚子饿了,却说不出话来,只得哭闹。声音时隐时现,时远时近。它一会在我仰面的上空,一会在我两侧的耳畔,来来回回,吞吞吐吐,似欲下手又不敢下手的样子,厌恶极了。我于黑暗中挥手驱赶,没有多大作用,手一停它又回来。干脆扬起被子一角,大幅度左右摆动,企图掀起一股巨大气流,将那个讨厌的家伙驱得远远的。这一招还算管用,嘤嘤嗡嗡的声音果然消停。
寒凉的秋夜,归于宁静。睡意去了,却难以返回。听不见蚊子吟鸣,仍期待那声音再现。相信它不曾走远,说不定一会儿便会卷土重来。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不确定,反正相信它会来。黑暗中,眼睛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它就是不来。其实,来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照样挥手驱赶它,甚至扬起被子一角扇起一股劲风将它吹走。这期待实质上不是期待,是一种防备,防止被蚊子袭击。蚊子呢,可能已得到教训,它没有选对侵袭对象。这家伙睡眠不深,一有动静他就警醒,它在他身上无从下手。
蚊子迟迟不来,他就不恭候了。他动员自己,回到眠乡。天将亮时,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年少,住在小山脚下,水塘岸边,那幢土墙泥瓦的老宅里。那年代,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身边的蚊子肯定比现在多得多,不是挥手就能驱赶的。不过,人在那种特别的环境里,也有特别的生存智慧。为了防蚊,床上挂有蚊帐。白天蚊帐是敞开的,总会有一些蚊子飞进去,悄悄停在蚊帐壁上或顶上。睡觉前,蚊帐门就会合上,不许外面的蚊子进去,已经进去的蚊子也要将其赶出来,人们挥舞芭蕉扇,在蚊帐里开展清场运动。总有少数“顽固分子”,躲在蚊帐某个隐蔽的角落里,任芭蕉扇怎么扇,它就是不出来,那就将它暂时留在蚊帐里,等会再彻底收拾它。
其实,蚊帐门关上之后,还可能有蚊子从蚊帐的缝隙里钻进去。晚上睡觉前,细心的人会再检查一下蚊帐里有没有藏蚊子,发现有蚊子就现场消灭,免得睡倒之后又要起来与蚊子搏斗。办法很简单,将一盏带有两头细中间粗的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端进蚊帐里,发现有蚊子,便将玻璃罩子的上口贴近蚊子,来自灯芯燃烧的高温,从玻璃罩子里腾起一股热浪袭击蚊子,蚊子来不及逃命,坠落在玻璃罩子里,不是被灯火烧成灰烬,就是在灯火旁被高温烤得焦糊。
这些年,住在楼房里,身边蚊子少了,便拿它不当回事,老祖宗发明的蚊帐也弃用了,这便给了少数溜进室内的蚊子可乘之机,比如那夜。次日早晨醒来,隐约觉得左边耳廓上有些瘙痒,抬手一摸,耳廓上端有硬块。很明显,那地方刚刚被蚊子叮过。之前,我曾笑话蚊子,在人耳边嘤嘤嗡嗡,那么大张旗鼓,怎能吸到人身上的血呢?这会子,我佩服蚊子变得聪明起来,不声不响“吻”过我的耳廓。当然,也可能蚊子还是嘤嘤嗡嗡地飞来的,只是我在那一刻睡沉了,没听见,以致蚊子叮了耳廓,我也不知晓。
起床,洗漱,发现卫生间白墙上,趴着一只肥硕的麻蚊子。机会到了,我得收拾它,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卫生间里是瓷砖墙,弄脏了不难清洁,消灭墙上的蚊子毫无顾忌。来不及找工具,便直接动手,一个巴掌拍上去,蚊子烂成泥,紧贴在白瓷砖上。收回巴掌,细看手心,在黑色污渍中间,竟有一小块红色。看得出来,红的是血。那是蚊子的血,还是我的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