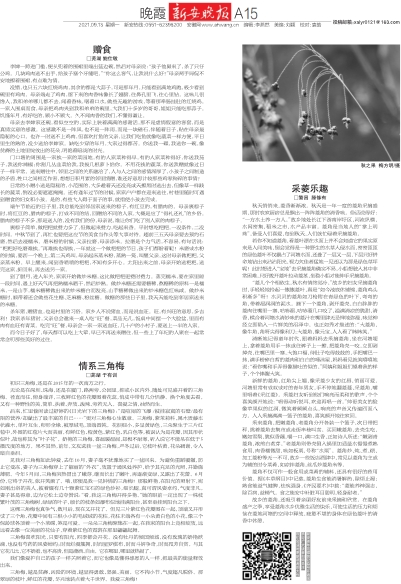发布日期:
赠食
□芜湖鲍仕敏
李婶一跨进门槛,便从兜着的围裙里端出蓝边碗,然后对母亲说:“孩子他舅来了,杀了只仔公鸡。几块鸡肉送不出手,给孩子塞个牙缝吧。”“你这么客气,让我说什么好!”母亲两手局促不安地擦着围裙,有点难为情。
没错,也只五六块红烧鸡肉,其余的都是大蒜子,可是那年月,只能看到满地鸡跑,极少看到碗里有鸡肉。母亲端走了鸡肉,留下来的肉香味像长了翅膀,往鼻孔里飞,往心里钻。这味儿很馋人,我和弟弟哪儿都不去,闻着香味,咽着口水,做些无趣的游戏,等着那牵肠挂肚的红烧鸡。一家人围桌而食,母亲把鸡肉夹到我和弟弟的碗里,大我们十多岁的哥哥、姐姐只能吃那蒜子。饥馑年月,有好吃的,顾小不顾大。久不闻肉香的我们,不懂得谦让。
母亲去李婶家还碗,看似空空的,实际上装着满满的感谢话,那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真情实意的感激。这感激不是一阵风,也不是一阵雨,而是一块磁石,伴随着日子,贴在母亲最隐秘的心口。也许一时送不上鸡肉,但喜欢打鱼的父亲,让我们吃鱼就像吃蔬菜一样方便,平日里生的熟的,没少送给李婶家。缺吃少穿的年月,大家过得都苦。你送我一碟,我送你一碗,像贫瘠的土地里绽放出的花朵,明艳着暗淡的时光。
门口塘的周围是一家挨一家的菜园地,有的人家菜种得早,有的人家菜种得好,你送我茄子,我送你辣椒;你割几丛韭菜给我,我拔几根萝卜给你。不用花钱的蔬菜,你送我赠就像过日子一样平常。送来赠往中,邻里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深厚了,小孩子之间制造的矛盾,牲口之间相互作害,想想日积月累的邻里馈赠,谁还好意思计较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
日常的小赠小送是隐秘的,小范围的,大多趁着天还没亮或天擦黑时送出去,但像草一样贱长的蔬菜,倒没必要遮遮掩掩。还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迎来送往,村巷里随时可遇到赠食的妇女和小孩。是的,有些大人碍于面子的事,就指使小孩去完成。
端午节临近的日子里,我总能吃到邻居家送来的粽子,有红豆的,有腊肉的。母亲裹粽子时,将红豆的、腊肉的粽子,打成不同的结,回赠给不同的人家,大概是应了“得礼还礼”的乡俗。腊肉的粽子不多,那是送人的,没有我们的份,母亲说,谁让你们吃了别人家的肉粽子。
裹粽子简单,做粑粑就费力多了,但做起来费力,吃起来香。平时想吃粑粑,一没条件,二没时间。中秋节到了,再忙也要把这应节的美食当作头等大事对待。超前三五天母亲要去预约石磨,然后去浸糯米。磨米粉的时候,父亲拉磨,母亲添米。拉磨是个力气活,不容易,有句话说:“粑粑好吃磨难挨。”再难挨也得挨,一年就这一个做粑粑的节日,孩子们都盼着呢!米磨成水粉的时候,要沥一个晚上,第二天鸡叫,母亲起床蒸米粉,蒸熟一笼,叫醒父亲,这时母亲做粑粑,父亲蒸米粉。早上醒来,闻到香喷喷的粑粑,不知有多开心。太阳出来之前,母亲开始送粑粑,送完这家,折回来,再去送另一家。
到了腊月,进入年关,家家开始做炒米糖,这比做粑粑更费时费力。蒸完糯米,要在家里晾一段时间,遇上好天气再把熟糯米晒干,然后炒熟。做炒米糖还需要糖稀,熬糖稀的原料一是糯米,一是山芋,糯米糖稀做出来的炒米糖白而发亮,山芋糖稀做出来的炒米糖色红味咸。做炒米糖时,顺带着还会做些花生糖、芝麻糖、粉丝糖。做糖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能吃到邻居家送来的米糖。
杀年猪,赠猪血,也是村里的习俗。家乡人不说猪血,而是说血旺。旺,有兴旺的意思,多吉利!我家杀年猪时,父亲总会邀来一桌人吃“旺”餐,菜品无几,饭桌中间摆一个大脸盆,里面有肉有血旺有青菜。吃完“旺”餐,母亲会一家一家送血旺,几十户的小村子,要送上一半的人家。
而今日子好了,每天都可以吃上大荤,早已不再送来赠往,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聚在一起常常念叨那些美好的过往。
李婶一跨进门槛,便从兜着的围裙里端出蓝边碗,然后对母亲说:“孩子他舅来了,杀了只仔公鸡。几块鸡肉送不出手,给孩子塞个牙缝吧。”“你这么客气,让我说什么好!”母亲两手局促不安地擦着围裙,有点难为情。
没错,也只五六块红烧鸡肉,其余的都是大蒜子,可是那年月,只能看到满地鸡跑,极少看到碗里有鸡肉。母亲端走了鸡肉,留下来的肉香味像长了翅膀,往鼻孔里飞,往心里钻。这味儿很馋人,我和弟弟哪儿都不去,闻着香味,咽着口水,做些无趣的游戏,等着那牵肠挂肚的红烧鸡。一家人围桌而食,母亲把鸡肉夹到我和弟弟的碗里,大我们十多岁的哥哥、姐姐只能吃那蒜子。饥馑年月,有好吃的,顾小不顾大。久不闻肉香的我们,不懂得谦让。
母亲去李婶家还碗,看似空空的,实际上装着满满的感谢话,那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真情实意的感激。这感激不是一阵风,也不是一阵雨,而是一块磁石,伴随着日子,贴在母亲最隐秘的心口。也许一时送不上鸡肉,但喜欢打鱼的父亲,让我们吃鱼就像吃蔬菜一样方便,平日里生的熟的,没少送给李婶家。缺吃少穿的年月,大家过得都苦。你送我一碟,我送你一碗,像贫瘠的土地里绽放出的花朵,明艳着暗淡的时光。
门口塘的周围是一家挨一家的菜园地,有的人家菜种得早,有的人家菜种得好,你送我茄子,我送你辣椒;你割几丛韭菜给我,我拔几根萝卜给你。不用花钱的蔬菜,你送我赠就像过日子一样平常。送来赠往中,邻里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深厚了,小孩子之间制造的矛盾,牲口之间相互作害,想想日积月累的邻里馈赠,谁还好意思计较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
日常的小赠小送是隐秘的,小范围的,大多趁着天还没亮或天擦黑时送出去,但像草一样贱长的蔬菜,倒没必要遮遮掩掩。还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迎来送往,村巷里随时可遇到赠食的妇女和小孩。是的,有些大人碍于面子的事,就指使小孩去完成。
端午节临近的日子里,我总能吃到邻居家送来的粽子,有红豆的,有腊肉的。母亲裹粽子时,将红豆的、腊肉的粽子,打成不同的结,回赠给不同的人家,大概是应了“得礼还礼”的乡俗。腊肉的粽子不多,那是送人的,没有我们的份,母亲说,谁让你们吃了别人家的肉粽子。
裹粽子简单,做粑粑就费力多了,但做起来费力,吃起来香。平时想吃粑粑,一没条件,二没时间。中秋节到了,再忙也要把这应节的美食当作头等大事对待。超前三五天母亲要去预约石磨,然后去浸糯米。磨米粉的时候,父亲拉磨,母亲添米。拉磨是个力气活,不容易,有句话说:“粑粑好吃磨难挨。”再难挨也得挨,一年就这一个做粑粑的节日,孩子们都盼着呢!米磨成水粉的时候,要沥一个晚上,第二天鸡叫,母亲起床蒸米粉,蒸熟一笼,叫醒父亲,这时母亲做粑粑,父亲蒸米粉。早上醒来,闻到香喷喷的粑粑,不知有多开心。太阳出来之前,母亲开始送粑粑,送完这家,折回来,再去送另一家。
到了腊月,进入年关,家家开始做炒米糖,这比做粑粑更费时费力。蒸完糯米,要在家里晾一段时间,遇上好天气再把熟糯米晒干,然后炒熟。做炒米糖还需要糖稀,熬糖稀的原料一是糯米,一是山芋,糯米糖稀做出来的炒米糖白而发亮,山芋糖稀做出来的炒米糖色红味咸。做炒米糖时,顺带着还会做些花生糖、芝麻糖、粉丝糖。做糖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能吃到邻居家送来的米糖。
杀年猪,赠猪血,也是村里的习俗。家乡人不说猪血,而是说血旺。旺,有兴旺的意思,多吉利!我家杀年猪时,父亲总会邀来一桌人吃“旺”餐,菜品无几,饭桌中间摆一个大脸盆,里面有肉有血旺有青菜。吃完“旺”餐,母亲会一家一家送血旺,几十户的小村子,要送上一半的人家。
而今日子好了,每天都可以吃上大荤,早已不再送来赠往,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聚在一起常常念叨那些美好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