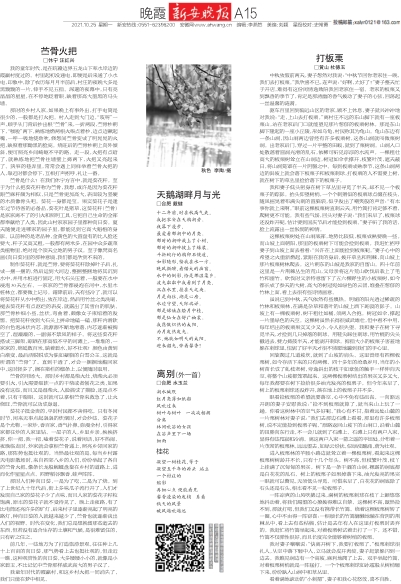发布日期:
苎骨火把
□休宁汪红兴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皖赣边界五龙山下率水岸边的霞瀛村度过的。村里起初没通电,即便是后来通了小水电,印象中,除了农历每月月半前后,村庄的夜晚大多是黑黢黢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深邃的夜幕中,只有亮晶晶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着眼,映着那高大墨黑的马头墙。
那时的乡村人家,如果晚上有事外出,打手电筒是很少的,一般都是打火把。村人走到大门边,“吱呀”一声,顺手从门背后抄出根“苎骨”来,一折两段,苎骨杪朝下,“嗤啦”两下,熟练地燃两根火柴点着杪,边点边噘起嘴,一呼一吸地使劲吹,倏忽间苎骨变成了明晃晃的火把,映照着那黝黑的脸庞。烧旺后的苎骨杪朝上向外倾斜,便可照亮乡间崎岖不平的路。走一段,火把有点暗了,就熟练地把苎骨往墙壁上捣两下,火把又亮起来了。狭窄的巷弄里,常常会遇上同样举着苎骨火把的人,靠近时都会停下,互相打声招呼,礼让一番。
苎骨是什么?在我们休宁方言中,就是葵花秆。至于为什么把葵花秆称为苎骨,我想,或许是因为葵花秆跟苎麻秆颇为相似,只是苎骨更加高大,表面较为坚硬的木质像骨头吧。葵花一身都是宝。果实葵花子是逢年过节待客的必备品,葵花叶是猪草,这葵花秆(苎骨)是家家离不了的引火和照明工具,它把自己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人类,因此山村家家园子里都种向日葵。夏天随便走进哪家的园子里,都能见到它高大魁梧的身影。以前种的是老品种,金黄色的大圆盘有的比人脸还要大,秆子又高又粗,一般都有两米多,在园中众多蔬菜类植物里,绝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至于像梵高名画《向日葵》里的那种意境,我们都是欣赏不来的。
制作葵花秆,就是苎骨,要将葵花秆除掉叶子后,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运到大河边,整捆整捆地将其沉到水中,并用木桩进行固定,用大石头压着,一般要在水中浸泡30天左右。一家家的苎骨都浸泡在河中,水里木桩林立,都要做上记号。霜降前后,天有些冷了,就可以将葵花秆从水中捞出,放在岸边,然后用竹丝之类洗刷,褪去葵花秆有点沤烂的表皮,就露出了其雪白的肌肤。那苎骨杪细小些,丝状,弯曲着,颇像女子束绾着的发髻。把葵花秆放到大石头上拼命地磕一磕,那秆内滑软的白色泡沫状内芯,就源源不断地滑落,内芯逐渐被掏空了,湿漉漉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将这些葵花秆搭成三脚架,晾晒在那高低不平的河滩上,一堆堆的,一家家的,绵延数百米,映着碧水,好不壮观!颜色由黄到白渐变,最后活脱脱成为肤如凝脂的白雪公主,这就是所谓的“苎骨”了。直到干透了,才会一捆捆地搬回家中,这时轻多了,搁在猪栏的檩条上,以便随时取用。
苎骨的用场大。那时乡村都是柴火灶,烧柴火必须要引火,引火需要细软一点的干柴或者刨花之类,如果没有这些,而且又是湿柴火,人脸搞成了猫脸,还是点不着,只有干瞪眼。这时就可以拿根苎骨来救急了,让火烧旺,苎骨就可以功成身退。
葵花子挺金贵的,平时村民都不舍得吃。只有冬闲时节,闲来无事点起袅袅的炊烟时,才会炒些。葵花子是个尤物,一家炒,香百家,香气扑鼻,弥漫全村,引得家家都往炒的人家里钻。一屋子的人,乡里乡亲,挨挨挤挤,你一把,我一把,嗑着葵花子,说着闲话,好不热闹。夜晚临走时,炒家就会拿根苎骨递上,照亮乡邻回家的路,那阵势也挺壮观的。当然最壮观的是,每当乡村露天电影散场时,来自四邻八乡的人们,纷纷举起了各自的苎骨火把,像条长龙般蜿蜒盘旋在乡村的道路上,进而化作星星点点。四野稻谷飘香,蛙声阵阵。
那时人们种向日葵,一是为了吃,二是为了烧。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街上多味瓜子流行开了,人们才发现自己家的葵花子少了点味,而且人家的葵花子籽粒饱满,原本的葵花子就不受待见了。晚上走夜路,有了比电筒还亮许多的矿灯,后来村子里逐渐亮起了明亮的路灯,种向日葵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苎骨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代在变化,我们总是想挽留那些逝去的东西,但若没有适合生存的土壤和气候,是很难留住的,只有听之任之。
前几年,一些地方为了打造旅游景观,往往种上几十上百亩的向日葵,那气势看上去也挺壮观的,但走近一瞧,这种观赏性的向日葵,大多矮矮小小的,就像是小家碧玉,不比记忆中苎骨那样威武高大的男子汉了。
我童年时代的霞瀛村,和这乡村火把一同消失了,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皖赣边界五龙山下率水岸边的霞瀛村度过的。村里起初没通电,即便是后来通了小水电,印象中,除了农历每月月半前后,村庄的夜晚大多是黑黢黢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深邃的夜幕中,只有亮晶晶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着眼,映着那高大墨黑的马头墙。
那时的乡村人家,如果晚上有事外出,打手电筒是很少的,一般都是打火把。村人走到大门边,“吱呀”一声,顺手从门背后抄出根“苎骨”来,一折两段,苎骨杪朝下,“嗤啦”两下,熟练地燃两根火柴点着杪,边点边噘起嘴,一呼一吸地使劲吹,倏忽间苎骨变成了明晃晃的火把,映照着那黝黑的脸庞。烧旺后的苎骨杪朝上向外倾斜,便可照亮乡间崎岖不平的路。走一段,火把有点暗了,就熟练地把苎骨往墙壁上捣两下,火把又亮起来了。狭窄的巷弄里,常常会遇上同样举着苎骨火把的人,靠近时都会停下,互相打声招呼,礼让一番。
苎骨是什么?在我们休宁方言中,就是葵花秆。至于为什么把葵花秆称为苎骨,我想,或许是因为葵花秆跟苎麻秆颇为相似,只是苎骨更加高大,表面较为坚硬的木质像骨头吧。葵花一身都是宝。果实葵花子是逢年过节待客的必备品,葵花叶是猪草,这葵花秆(苎骨)是家家离不了的引火和照明工具,它把自己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人类,因此山村家家园子里都种向日葵。夏天随便走进哪家的园子里,都能见到它高大魁梧的身影。以前种的是老品种,金黄色的大圆盘有的比人脸还要大,秆子又高又粗,一般都有两米多,在园中众多蔬菜类植物里,绝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至于像梵高名画《向日葵》里的那种意境,我们都是欣赏不来的。
制作葵花秆,就是苎骨,要将葵花秆除掉叶子后,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运到大河边,整捆整捆地将其沉到水中,并用木桩进行固定,用大石头压着,一般要在水中浸泡30天左右。一家家的苎骨都浸泡在河中,水里木桩林立,都要做上记号。霜降前后,天有些冷了,就可以将葵花秆从水中捞出,放在岸边,然后用竹丝之类洗刷,褪去葵花秆有点沤烂的表皮,就露出了其雪白的肌肤。那苎骨杪细小些,丝状,弯曲着,颇像女子束绾着的发髻。把葵花秆放到大石头上拼命地磕一磕,那秆内滑软的白色泡沫状内芯,就源源不断地滑落,内芯逐渐被掏空了,湿漉漉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将这些葵花秆搭成三脚架,晾晒在那高低不平的河滩上,一堆堆的,一家家的,绵延数百米,映着碧水,好不壮观!颜色由黄到白渐变,最后活脱脱成为肤如凝脂的白雪公主,这就是所谓的“苎骨”了。直到干透了,才会一捆捆地搬回家中,这时轻多了,搁在猪栏的檩条上,以便随时取用。
苎骨的用场大。那时乡村都是柴火灶,烧柴火必须要引火,引火需要细软一点的干柴或者刨花之类,如果没有这些,而且又是湿柴火,人脸搞成了猫脸,还是点不着,只有干瞪眼。这时就可以拿根苎骨来救急了,让火烧旺,苎骨就可以功成身退。
葵花子挺金贵的,平时村民都不舍得吃。只有冬闲时节,闲来无事点起袅袅的炊烟时,才会炒些。葵花子是个尤物,一家炒,香百家,香气扑鼻,弥漫全村,引得家家都往炒的人家里钻。一屋子的人,乡里乡亲,挨挨挤挤,你一把,我一把,嗑着葵花子,说着闲话,好不热闹。夜晚临走时,炒家就会拿根苎骨递上,照亮乡邻回家的路,那阵势也挺壮观的。当然最壮观的是,每当乡村露天电影散场时,来自四邻八乡的人们,纷纷举起了各自的苎骨火把,像条长龙般蜿蜒盘旋在乡村的道路上,进而化作星星点点。四野稻谷飘香,蛙声阵阵。
那时人们种向日葵,一是为了吃,二是为了烧。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街上多味瓜子流行开了,人们才发现自己家的葵花子少了点味,而且人家的葵花子籽粒饱满,原本的葵花子就不受待见了。晚上走夜路,有了比电筒还亮许多的矿灯,后来村子里逐渐亮起了明亮的路灯,种向日葵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苎骨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代在变化,我们总是想挽留那些逝去的东西,但若没有适合生存的土壤和气候,是很难留住的,只有听之任之。
前几年,一些地方为了打造旅游景观,往往种上几十上百亩的向日葵,那气势看上去也挺壮观的,但走近一瞧,这种观赏性的向日葵,大多矮矮小小的,就像是小家碧玉,不比记忆中苎骨那样威武高大的男子汉了。
我童年时代的霞瀛村,和这乡村火把一同消失了,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