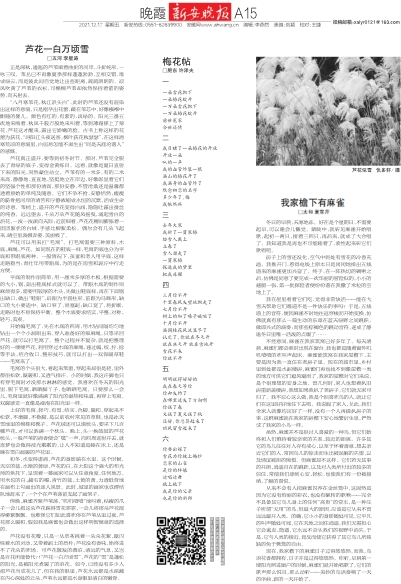发布日期:
芦花一白万顷雪
□五河李星涛
正是深秋,逶迤的芦苇顺着曲折的河岸,斗折蛇形,一咏三叹。苇丛已不再像夏季那样蓬蓬勃勃,互相交错,堆成绿云,而是彼此间自觉地让出些距离,疏疏朗朗的。凉风吹黄了芦苇的衣衫,可棵棵芦苇却依然保持着箭的姿势,向天射去。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此时的芦苇还没有渲染出这样的意境,只是刚孕出花蕾,藏在苇芯中,好像襁褓中酣睡的婴儿。颜色有红的,有紫的,淡绿的。阳光三番五次地来唤着,秋风千般万般地来叫着,等到薄霜搽上了菊花,芦花这才醒来,露出它娇嫩的脸。古书上称这样的花蕾为荻花,“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这样清寒荒凉的意境里,白居易怎能不滋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芦花真正盛开,要等到初冬时节。那时,芦苇完全脱去了青绿的底子,变得金黄烁目。远看,就像是夏日直射下来的阳光,突然凝住站立。芦苇有的一米多,有的二米来高,静静地、直直地、坚挺地立在岸边,好像彰显着它们的坚强个性和那份清高,那份安静,不管沧桑还是温馨都透着原始的单纯及随意。它们不争不抢,安静恬然,瘦瘦的筋骨把河岸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永恒的沉默,活成生命的诗意。苇梢上,盛开的芦花变得白润,隐隐吐露出蚕丝的纯香。远远望去,千朵万朵芦花随风摇曳,涌起雪白的浪花,一波一波滚向天际;近前细看,芦花花穗间膨胀着一团团絮状的白绒,手感比柳絮柔松。偶尔会有几朵飞起来,晴空里袅娜弄姿,美丽极了。
芦花可以用来打“毛窝”。打毛窝需要三种原料,木底、麻绳、芦花。如同现在的鞋底一样,毛窝的底也分为平底和带跟底两种。一般情况下,孩童和老人用平底,这样走路稳当;青壮年用带跟底,为的是在雨雪和泥泞中行走方便。
平底的制作很简单,用一厘米多厚的木板,根据需要的大小,锯、刻出鞋底样式就可以了。带跟木底的制作则麻烦得多,需要用较厚的木头,先做出鞋底样,再在下面锯出缺口,做出“鞋跟”,后跟为半圆柱形,前跟为马蹄形,缺口的大小要适中。缺口窄了,易塞泥;缺口宽了,易折断,走路时也不易保持平衡。整个木底要求结实、平整、对称、轻巧、美观。
开始编毛窝了,先在木底的四周,用木钻间隔均匀地钻出一个个小洞眼出来,穿入准备好的细麻绳,只等采回芦花,就可以打毛窝了。整个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把整理好的一缕缕芦花,利用穿过木底的麻绳,通过编、绞、拧、捻等手法,结合收口、整形技巧,就可以打出一双保暖草鞋——毛窝来了。
毛窝的个头很大,看起来笨重,穿起来却很是轻,里外都很松软,既暖和,又透气排汗。小的时候,我这汗脚也只有穿毛窝时才没那水淋淋的感觉。我喜欢在冬天的阳光里,脱下毛窝,晒晒脚丫子,也晒晒毛窝。只要那么一会儿,毛窝里就好像盛满了阳光的温热和味道,再穿上毛窝,双脚感觉一直像是浸泡在阳光里一样。
上好的毛窝,轻巧,有型,结实,合脚,暖和,穿起来不松软,不磨脚,不勒脚,是以前农村常见的草鞋,也是冰天雪地里的棉鞋和靴子。芦花绒还可以填枕头,要采下几百穗芦花,才可以装满一个枕头。晚上,头一挨鼓鼓的芦花枕头,一股芦苇的清香便会“噗”一声,向四周迸射开去,就连梦也会做得波光粼粼的,让人不知道是睡在床上,还是睡在雪白温暖的芦花里。
初冬,水变得虚清,芦花的身影映在水里。这个时候,天空的蓝,水塘的黄绿,芦花的白,在太阳这个强大的布光师的烘托下,呈现着一幕画家可以从任意角度、任何地方,用米坨的白、赭石的褐、青竹的蓝、土黄的黄,力透纸背地在画布上勾画出的迷人风景。此时,城里的画家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一个个在芦苇荡前支起了画架子。
傍晚,麻雀齐聚芦苇荡,“叽叽喳喳”地叫着,枯瘦的爪子一会儿把这朵芦花踩得雪花霏霏,一会儿将那朵芦花摇得柳絮飘飘。也难怪它们如此喜欢停在芦苇丛里过夜,芦花那么暖和,假如我是麻雀也会做出这样明智惬意的选择的。
芦花没有花瓣,只是一丛草茎挑着一朵朵花絮,既闪烁着水的灵动,又带着泥土的质朴;芦花没有香味,始终进不了花朵的欢场。可芦花散发的澹泊、清远的气息,又岂是百花所能替代?!“芦花一白万顷雪”,芦花的“雪”是蓬松的阳光,是被阳光煮暖了的浪花。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把芦花当成花儿了,但在我的眼里,芦花永远都是水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云朵,芦苇永远都是水身躯里清白的嫩骨。
正是深秋,逶迤的芦苇顺着曲折的河岸,斗折蛇形,一咏三叹。苇丛已不再像夏季那样蓬蓬勃勃,互相交错,堆成绿云,而是彼此间自觉地让出些距离,疏疏朗朗的。凉风吹黄了芦苇的衣衫,可棵棵芦苇却依然保持着箭的姿势,向天射去。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此时的芦苇还没有渲染出这样的意境,只是刚孕出花蕾,藏在苇芯中,好像襁褓中酣睡的婴儿。颜色有红的,有紫的,淡绿的。阳光三番五次地来唤着,秋风千般万般地来叫着,等到薄霜搽上了菊花,芦花这才醒来,露出它娇嫩的脸。古书上称这样的花蕾为荻花,“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这样清寒荒凉的意境里,白居易怎能不滋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芦花真正盛开,要等到初冬时节。那时,芦苇完全脱去了青绿的底子,变得金黄烁目。远看,就像是夏日直射下来的阳光,突然凝住站立。芦苇有的一米多,有的二米来高,静静地、直直地、坚挺地立在岸边,好像彰显着它们的坚强个性和那份清高,那份安静,不管沧桑还是温馨都透着原始的单纯及随意。它们不争不抢,安静恬然,瘦瘦的筋骨把河岸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永恒的沉默,活成生命的诗意。苇梢上,盛开的芦花变得白润,隐隐吐露出蚕丝的纯香。远远望去,千朵万朵芦花随风摇曳,涌起雪白的浪花,一波一波滚向天际;近前细看,芦花花穗间膨胀着一团团絮状的白绒,手感比柳絮柔松。偶尔会有几朵飞起来,晴空里袅娜弄姿,美丽极了。
芦花可以用来打“毛窝”。打毛窝需要三种原料,木底、麻绳、芦花。如同现在的鞋底一样,毛窝的底也分为平底和带跟底两种。一般情况下,孩童和老人用平底,这样走路稳当;青壮年用带跟底,为的是在雨雪和泥泞中行走方便。
平底的制作很简单,用一厘米多厚的木板,根据需要的大小,锯、刻出鞋底样式就可以了。带跟木底的制作则麻烦得多,需要用较厚的木头,先做出鞋底样,再在下面锯出缺口,做出“鞋跟”,后跟为半圆柱形,前跟为马蹄形,缺口的大小要适中。缺口窄了,易塞泥;缺口宽了,易折断,走路时也不易保持平衡。整个木底要求结实、平整、对称、轻巧、美观。
开始编毛窝了,先在木底的四周,用木钻间隔均匀地钻出一个个小洞眼出来,穿入准备好的细麻绳,只等采回芦花,就可以打毛窝了。整个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把整理好的一缕缕芦花,利用穿过木底的麻绳,通过编、绞、拧、捻等手法,结合收口、整形技巧,就可以打出一双保暖草鞋——毛窝来了。
毛窝的个头很大,看起来笨重,穿起来却很是轻,里外都很松软,既暖和,又透气排汗。小的时候,我这汗脚也只有穿毛窝时才没那水淋淋的感觉。我喜欢在冬天的阳光里,脱下毛窝,晒晒脚丫子,也晒晒毛窝。只要那么一会儿,毛窝里就好像盛满了阳光的温热和味道,再穿上毛窝,双脚感觉一直像是浸泡在阳光里一样。
上好的毛窝,轻巧,有型,结实,合脚,暖和,穿起来不松软,不磨脚,不勒脚,是以前农村常见的草鞋,也是冰天雪地里的棉鞋和靴子。芦花绒还可以填枕头,要采下几百穗芦花,才可以装满一个枕头。晚上,头一挨鼓鼓的芦花枕头,一股芦苇的清香便会“噗”一声,向四周迸射开去,就连梦也会做得波光粼粼的,让人不知道是睡在床上,还是睡在雪白温暖的芦花里。
初冬,水变得虚清,芦花的身影映在水里。这个时候,天空的蓝,水塘的黄绿,芦花的白,在太阳这个强大的布光师的烘托下,呈现着一幕画家可以从任意角度、任何地方,用米坨的白、赭石的褐、青竹的蓝、土黄的黄,力透纸背地在画布上勾画出的迷人风景。此时,城里的画家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一个个在芦苇荡前支起了画架子。
傍晚,麻雀齐聚芦苇荡,“叽叽喳喳”地叫着,枯瘦的爪子一会儿把这朵芦花踩得雪花霏霏,一会儿将那朵芦花摇得柳絮飘飘。也难怪它们如此喜欢停在芦苇丛里过夜,芦花那么暖和,假如我是麻雀也会做出这样明智惬意的选择的。
芦花没有花瓣,只是一丛草茎挑着一朵朵花絮,既闪烁着水的灵动,又带着泥土的质朴;芦花没有香味,始终进不了花朵的欢场。可芦花散发的澹泊、清远的气息,又岂是百花所能替代?!“芦花一白万顷雪”,芦花的“雪”是蓬松的阳光,是被阳光煮暖了的浪花。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把芦花当成花儿了,但在我的眼里,芦花永远都是水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云朵,芦苇永远都是水身躯里清白的嫩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