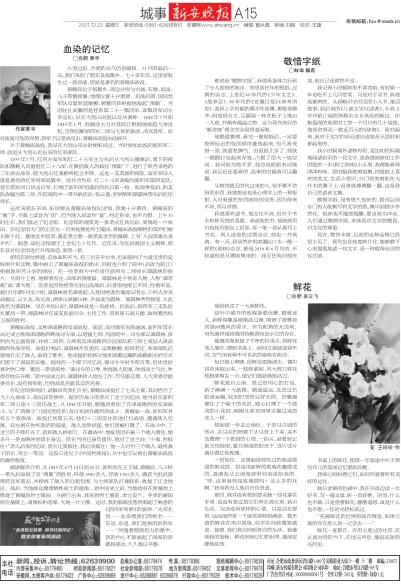发布日期:
敬惜字纸
□蚌埠魏莉
都说是“敬惜字纸”,我爸是身体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家里面往年的报纸、过期的杂志,上世纪80年代的《少年文艺》、《故事会》,90年代的《安徽日报》《参考消息》,连我上学时候的课本作业簿,都收得整齐、码放得方正,豆腐块一样在柜子上堆出一人高,并渐有漫溢之势。这与现在流行的“断舍离”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
他酷爱整理,看完一摞报纸后,一定要按照标出的版面顺序叠放起来,但凡我放错一张,就要发脾气。旧报纸太多了,他就一捆捆打包起来存放,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我问他为啥不丢,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后还要看的,没事的时候我可以翻翻。
从物资匮乏时代过来的人,似乎都不舍得丢东西,我猜想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投射,人对看重的东西就特别宝贵,因为得来不易,所以珍惜。
我爸喜欢读书,他文化不高,但对于书本有种天然的喜爱。我送他的书,他统统用白色挂历纸包上封面,再一笔一划认真写上书名。别人送他的过期杂志,他也一并笑纳。有一天,我居然在他家翻出3本一模一样的《意林》杂志,都是2018年8月号的,不知道他是从哪收集来的。我忍住笑问他究竟,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不算宽裕,有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荤菜。可是对于买书,我爸是豪爽的。从我略识字时买的小人书、童话故事,到后来的《儿童文学》《读者》,从我上学开始订阅的各种杂志从来没有断过。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他却舍得买一套近百元的《辞海》。深究起来,我对于文字的亲近感应该就是从那时积累起来的。
我小时候课外读物有限,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到手的一切文字,连我爸刚参加工作时发的一本《焊工指南》小手册,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我做剪报集,把报纸上喜欢的美文、生活小常识,分门别类剪贴在大开本的簿子上,没事就捧着翻一翻,这是我自己的读者文摘。
敬惜字纸,是有悠久传统的,据说以前专门有人收集写有文字的纸,集中到惜字亭焚化。纸灰也不随意抛撒,要由流水冲走。人们通过敬惜字纸,来体现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尊重。
现在,物资丰富,以前的这种品格已经很少见了。现代信息高度碎片化,能够静下心来慢慢地读一些文字,是一种值得追寻的仪式感。
都说是“敬惜字纸”,我爸是身体力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家里面往年的报纸、过期的杂志,上世纪80年代的《少年文艺》、《故事会》,90年代的《安徽日报》《参考消息》,连我上学时候的课本作业簿,都收得整齐、码放得方正,豆腐块一样在柜子上堆出一人高,并渐有漫溢之势。这与现在流行的“断舍离”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
他酷爱整理,看完一摞报纸后,一定要按照标出的版面顺序叠放起来,但凡我放错一张,就要发脾气。旧报纸太多了,他就一捆捆打包起来存放,占据了很大一块空间。我问他为啥不丢,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后还要看的,没事的时候我可以翻翻。
从物资匮乏时代过来的人,似乎都不舍得丢东西,我猜想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投射,人对看重的东西就特别宝贵,因为得来不易,所以珍惜。
我爸喜欢读书,他文化不高,但对于书本有种天然的喜爱。我送他的书,他统统用白色挂历纸包上封面,再一笔一划认真写上书名。别人送他的过期杂志,他也一并笑纳。有一天,我居然在他家翻出3本一模一样的《意林》杂志,都是2018年8月号的,不知道他是从哪收集来的。我忍住笑问他究竟,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不算宽裕,有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荤菜。可是对于买书,我爸是豪爽的。从我略识字时买的小人书、童话故事,到后来的《儿童文学》《读者》,从我上学开始订阅的各种杂志从来没有断过。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他却舍得买一套近百元的《辞海》。深究起来,我对于文字的亲近感应该就是从那时积累起来的。
我小时候课外读物有限,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到手的一切文字,连我爸刚参加工作时发的一本《焊工指南》小手册,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我做剪报集,把报纸上喜欢的美文、生活小常识,分门别类剪贴在大开本的簿子上,没事就捧着翻一翻,这是我自己的读者文摘。
敬惜字纸,是有悠久传统的,据说以前专门有人收集写有文字的纸,集中到惜字亭焚化。纸灰也不随意抛撒,要由流水冲走。人们通过敬惜字纸,来体现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尊重。
现在,物资丰富,以前的这种品格已经很少见了。现代信息高度碎片化,能够静下心来慢慢地读一些文字,是一种值得追寻的仪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