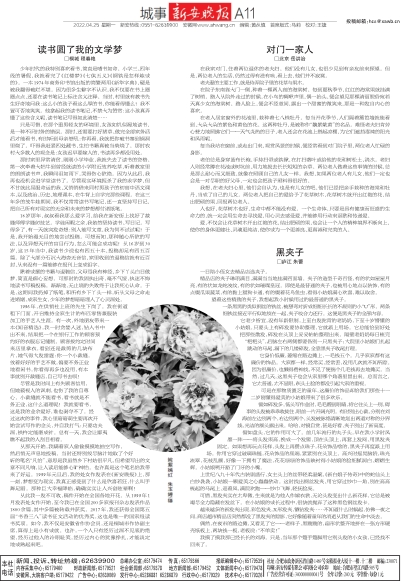发布日期:
读书圆了我的文学梦
□桐城程春艳
少年时代的我特别喜欢看书,简直是嗜书如命。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我就看完了《红楼梦》《七侠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197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繁两用《新华字典》,硬是被我翻得破烂不堪。因为很多生僻字不认识,我不仅要在书上圈圈点点,还要在读书笔记上标注含义注释。当时,村里就有教书先生好奇地问我:这么小的孩子看这么厚的书,你能看得懂么?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他拿起我的读书笔记,不禁大为赞赏:这小孩真弄懂了这些含义呢,读书笔记写得如此清楚……
只是可惜,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环境里,女孩如饥似渴地读书,是一种不识时务的错误。那时,还需要打好猪草、做完全部家务活后才能看书,有时听到母亲怒吼:你再看,我就把你破书塞到锅洞里烧了。吓得我赶紧四处藏书,生怕书籍真被当柴烧了。那时农村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女孩迟早要嫁人的,书读再多都没用处。
那时家里异常清贫,刚刚小学毕业,我就失去了读书的资格。第一次牵着大牯牛到曾经就读的小学附近放养吃草,听着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我瞬间泪如雨下,哭得伤心欲绝。因为从此后,我再也没机会进学堂读书了。尽管现实环境扼杀了我的求学梦,但不甘就此屈服命运的我,又悄悄借来同村男孩子的初高中语文课本,以及政治、历史、地理课本,在牛背上自学完那些课程。在这三年多的放牛娃期间,我不仅常常读书写笔记,还一直坚持写日记,把自己所有对现实的无奈和未来的梦想都付诸纸笔。
18岁那年,叔叔看我那么爱学习,给我在新安街上找好了裁缝师傅学缝纫技艺。学徒闲暇之余,我依然坚持读书、写日记。写得多了,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别人能写文章,我为何不试试呢?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尝试投稿。可想而知,那种随心所欲的写法,以及异想天开的盲目行为,怎么可能会成功呢!从16岁到30岁,这15年当中,我读书少说也有四五十本,投稿却足有四五百篇。除了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家里收到的退稿信就有近百封,从来没有一篇能够在报刊上变成铅字。
瞅着成摞的书籍与退稿信,父母骂我有神经,乡下丫头白日做梦,简直是痴心妄想。可那时的我固执出奇,毫不气馁,执迷不悔地读书写稿投稿。渐渐地,无止境的失败终于让我死心认命。于是,这期间我扔掉了纸笔,和所有乡下丫头一样,听从父母之命走进婚姻,成家生女,少年的梦想暗暗埋入了心灵深处。
1996年,在供销社上班的先生下岗了。我在街道租下门面,开启维持全家生计的布匹零售兼服装加工的手艺人生涯。有一次,外地朋友带来一本《知音精选》,我一时贪婪入迷,钻入书中出不来,结果把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顾客预约好的衣服忘记缝制。顾客按约定时间来店里拿衣,看到还是裁剪的几块布片,她气得大发雷霆:你一个小裁缝,放着好好的手艺不做,偏要不务正业地看闲书,你看得再多也没用,有本事就别开裁缝店,自己写书去呗!
尽管是我时间上有失顾客信用,但她藐视人的讽刺,也伤了我的自尊心。小裁缝就不能看书,看书就是不务正业,这什么道理呢!我就要看书,这是我的业余爱好,谁也剥夺不了。经过这次的事件,我心里暗暗萌生要再次开始尝试写作的念头,并自我打气:只要功夫深,铁杵定能磨成针。总有一天,我会让鄙夷瞧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
从那天开始,我瞒着家人偷偷摸摸地抽空写作,然后悄无声息地投稿。当时还特别绞尽脑汁地取了个好听的笔名“凡怡”,意思是我虽然乡下村姑很平凡,但希望写出的文章不同凡响,让人读后能够心旷神怡。也许真是这个笔名给我带来了好运。1999年元旦后,我的处女作发表在《新安晚报》上,那一刻,梦想变为现实,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欣喜若狂,什么叫手舞足蹈。那种巨大幸福降临,确确实实让人兴奋眩晕啊!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稿件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花。从1999年1月发表处女作开始,至今我已在全国2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1800余篇,其中多篇被转载并获奖。2017年,我还获得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的优秀奖,这也是唯一的国家级读书奖项。如今,我不仅是安徽省作协会员,还是桐城市作协副主席,算得上是小有成就。也许,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深不见底的绝望,经历过他人的冷眼耻笑,经历过内心的犹豫挣扎,才能淡定地成熟起来吧。
少年时代的我特别喜欢看书,简直是嗜书如命。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我就看完了《红楼梦》《七侠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197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繁两用《新华字典》,硬是被我翻得破烂不堪。因为很多生僻字不认识,我不仅要在书上圈圈点点,还要在读书笔记上标注含义注释。当时,村里就有教书先生好奇地问我:这么小的孩子看这么厚的书,你能看得懂么?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他拿起我的读书笔记,不禁大为赞赏:这小孩真弄懂了这些含义呢,读书笔记写得如此清楚……
只是可惜,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环境里,女孩如饥似渴地读书,是一种不识时务的错误。那时,还需要打好猪草、做完全部家务活后才能看书,有时听到母亲怒吼:你再看,我就把你破书塞到锅洞里烧了。吓得我赶紧四处藏书,生怕书籍真被当柴烧了。那时农村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女孩迟早要嫁人的,书读再多都没用处。
那时家里异常清贫,刚刚小学毕业,我就失去了读书的资格。第一次牵着大牯牛到曾经就读的小学附近放养吃草,听着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我瞬间泪如雨下,哭得伤心欲绝。因为从此后,我再也没机会进学堂读书了。尽管现实环境扼杀了我的求学梦,但不甘就此屈服命运的我,又悄悄借来同村男孩子的初高中语文课本,以及政治、历史、地理课本,在牛背上自学完那些课程。在这三年多的放牛娃期间,我不仅常常读书写笔记,还一直坚持写日记,把自己所有对现实的无奈和未来的梦想都付诸纸笔。
18岁那年,叔叔看我那么爱学习,给我在新安街上找好了裁缝师傅学缝纫技艺。学徒闲暇之余,我依然坚持读书、写日记。写得多了,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别人能写文章,我为何不试试呢?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尝试投稿。可想而知,那种随心所欲的写法,以及异想天开的盲目行为,怎么可能会成功呢!从16岁到30岁,这15年当中,我读书少说也有四五十本,投稿却足有四五百篇。除了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家里收到的退稿信就有近百封,从来没有一篇能够在报刊上变成铅字。
瞅着成摞的书籍与退稿信,父母骂我有神经,乡下丫头白日做梦,简直是痴心妄想。可那时的我固执出奇,毫不气馁,执迷不悔地读书写稿投稿。渐渐地,无止境的失败终于让我死心认命。于是,这期间我扔掉了纸笔,和所有乡下丫头一样,听从父母之命走进婚姻,成家生女,少年的梦想暗暗埋入了心灵深处。
1996年,在供销社上班的先生下岗了。我在街道租下门面,开启维持全家生计的布匹零售兼服装加工的手艺人生涯。有一次,外地朋友带来一本《知音精选》,我一时贪婪入迷,钻入书中出不来,结果把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顾客预约好的衣服忘记缝制。顾客按约定时间来店里拿衣,看到还是裁剪的几块布片,她气得大发雷霆:你一个小裁缝,放着好好的手艺不做,偏要不务正业地看闲书,你看得再多也没用,有本事就别开裁缝店,自己写书去呗!
尽管是我时间上有失顾客信用,但她藐视人的讽刺,也伤了我的自尊心。小裁缝就不能看书,看书就是不务正业,这什么道理呢!我就要看书,这是我的业余爱好,谁也剥夺不了。经过这次的事件,我心里暗暗萌生要再次开始尝试写作的念头,并自我打气:只要功夫深,铁杵定能磨成针。总有一天,我会让鄙夷瞧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
从那天开始,我瞒着家人偷偷摸摸地抽空写作,然后悄无声息地投稿。当时还特别绞尽脑汁地取了个好听的笔名“凡怡”,意思是我虽然乡下村姑很平凡,但希望写出的文章不同凡响,让人读后能够心旷神怡。也许真是这个笔名给我带来了好运。1999年元旦后,我的处女作发表在《新安晚报》上,那一刻,梦想变为现实,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欣喜若狂,什么叫手舞足蹈。那种巨大幸福降临,确确实实让人兴奋眩晕啊!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稿件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花。从1999年1月发表处女作开始,至今我已在全国2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1800余篇,其中多篇被转载并获奖。2017年,我还获得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的优秀奖,这也是唯一的国家级读书奖项。如今,我不仅是安徽省作协会员,还是桐城市作协副主席,算得上是小有成就。也许,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深不见底的绝望,经历过他人的冷眼耻笑,经历过内心的犹豫挣扎,才能淡定地成熟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