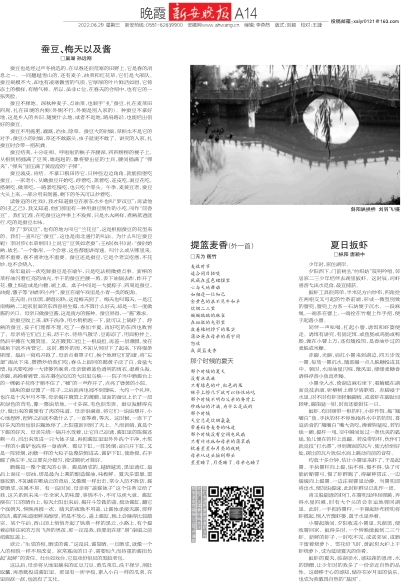发布日期:
蚕豆、梅天以及酱
□巢湖孙远刚
蚕豆也是经过严冬挑选的,在早春还很荒寒的田野上,它是春的消息之一。一同翻越雪山的,还有麦子、油菜和红花草,它们是大部队。蚕豆规模不大,却也有凌寒傲雪的气质,它厚厚的叶片鲜活如唇,它倚冻土的模样,有精气神。所以,虽非C位,在春天的合照中,也有它的一张笑脸。
蚕豆不择地。深秋种麦子、点油菜,也顺手“扎”蚕豆,扎在麦菜田四周,扎在田埂的内侧(外侧不行,外侧是别人家的)。种蚕豆不拿好地,这是乡人的共识,随便什么地,或者不是地,路肩路沿,也能结出很好的蚕豆。
蚕豆不用施肥,灌溉,治虫,除草。蚕豆大的时候,草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蚕豆小的时候,草还不敢露头,虫子就更不敢了。讲究的人家,扎蚕豆时会带一把灰粪。
蚕豆结荚,十分旺相。呼啦啦的秧子齐腰深,四四楞楞的梗子上,从根到梢插满了豆荚,雄赳赳的,像将要出征的士兵,腰间插满了“弹夹”,“弹夹”里压满了黄澄澄的“子弹”。
蚕豆泼皮,肯结。不拿口粮田待它,只种些边边角角,就能指望吃蚕豆。一家老小,从嫩蚕豆开始吃,烀着吃,蒸着吃,连皮吃,剥豆花吃,搭粥吃,做菜吃,一路紧吃慢吃,也只吃个零头。午季,麦黄豆老,蚕豆大头上来,一部分用来制酱,剩下的冬天可以炒着吃。
读鲁迅的《社戏》,我才知道蚕豆在浙东水乡也叫“罗汉豆”;再读他的《孔乙己》,我又知道,他们那里有一种用蚕豆制作的小吃,叫作“茴香豆”。我们江淮,在吃蚕豆这件事上不发挥,只是水火两样,煮熟蒸透就行,吃的是蚕豆本味。
除了“罗汉豆”,也有的地方叫它“兰花豆”,这是根据蚕豆的花型来的。我们一直叫它“蚕豆”,这也是南北通行的叫法。为什么叫它蚕豆呢?李时珍《本草纲目》上说它“豆荚如老蚕”;王祯《农书》说:“蚕时始熟,故名。”一个象形,一个会意,这些都能讲得通。叫什么或从哪里来,都不重要,喜不喜欢也不重要。蚕豆还是蚕豆,它是个老实疙瘩,不花妙,也不会绕人。
每年最后一次吃鲜蚕豆是在端午,只是吃法稍微费点事。新榨的菜籽油闪着红亮的油光,半干的蚕豆拦腰一剪,丢下油锅去炸,炸开了花,撒上细盐或是白糖,端上桌。桌子中间是一大提粽子,四周是蚕豆、油提、馓子等“油炸四小件”,蚕豆在端午戏里是小青一类的配角。
连天雨,白加黑,潮湿闷热,这是梅天到了。梅天也叫霉天,一是江南梅熟,二是家里面的东西容易生霉,本不算什么好天,却是一年一度做酱的关口。母亲只做蚕豆酱,这是南方的酱种。蚕豆易得,一“酱”难求。
新蚕豆收上来,晒干洗净,用水稍稍泡一下,就可以上锅烀了。烀熟的蚕豆,孩子们理都不理,吃了一春加半夏,再好吃的东西也败胃了。母亲将它们舀上来,沥干水,待热气散尽,豆晾凉了,用面粉拌上,然后平摊在大簸箕里。又在簸箕口担上一根扁担,再盖一层薄膜,放在墙角下就不再管它。这时,檐外的雨,不知从何时下了起来,下得慢条斯理。最后一窝鸡开抱了,母亲点着罩子灯,挨个地照它们的蛋,将“忘蛋”淘汰下来,攒攒炒给我们吃;春头上捉回的鹅黄子泛了白,食量大增,每天要吃掉一大背篓苦麻菜;母亲套着蓝色透明的雨衣,湿着头发,赤脚,高挽着裤管,站在暮色沉沉的大田里乌秧……院子当中晒酱台上的一棵栀子花终于绷不住了,“嗵”的一声炸开了,点亮了昏黄的小院。
墙角的蚕豆馊了一阵子,之后就再也闻不到馊味。大约一个礼拜,也许是十天半月不等,母亲揭开簸箕上的薄膜,里面的蚕豆上长了一层灰绿色的茸毛,像一整块草地,一寸多深,毛色很华贵。蚕豆发酵得充分,做出来的酱便有了肉的味道。母亲很满意,将它们一块块掰开,小心地捏碎,捏碎之后就不做什么了,一直等着,等天。这时候,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也很识趣地停了,太阳重新回到了天上。久雨新晴,真是个下酱的好天。母亲先烧一锅开水放着,让它自己凉透,酱缸里的陈酱还剩一点,舀出来放进一只大钵子里,再把酱缸里里外外洗个干净,木桨一样的小酱铲也洗得一身清爽。霉豆下缸,一阵轻烟;凉白开下缸,又是一阵轻烟,冰糖一样的大粒子盐整袋倒进去,酱铲下缸,使劲搅,右手酸了换左手,反正要充分搅匀,搅成糊状才算好。
晒酱是一整个夏天的心事。酱是晒成的,越晒越黑,黑里透红,最后上面汪一层油,那是最为上乘的酿造酱油,味极鲜。夏天多雷暴,雷暴狡黠,不知藏在哪块云的背后,又像鹰一样出击,常令人防不胜防,酱要晒成,实属不易。有一段时间,母亲将“盖酱钵子”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关系到未来一年全家人的味蕾,事情不小,不可马虎大意。酱缸摆在门口的晒台上,每天太阳出来后,揭开斗笠做的盖,搅动酱缸,翻它个底朝天,傍晚再搅一次。晴天的夜晚不用盖,让酱体承接天露,那样的话,酱的味道更鲜美醇厚,若是不放心,盖上酱缸,晚上会睡得比较踏实。某个午后,西山顶上悄悄升起了铁塔一样的黑云,小路上,有个提着凉鞋往家的方向飞奔的男孩,那一定是我,我要赶在那“塔”崩塌之前把酱缸盖上。
谚云:“生成的相,晒成的酱。”这是说,酱靠晒,一旦晒成,就像一个人的相貌一样不易改变。家常寡淡的日子,需要恒久而持重的酱担负起“起鲜”的责任。灶台如戏台,它是戏份很足的黑脸老包。
这以后,母亲将从地里摘来的豇豆刀豆、黄瓜菜瓜,洗干择尽,剖肚取瓤,再悉数投进酱缸里。那里有一所学校,素人小白一样的瓜菜,在里面沤一沤,也就有了文化。
蚕豆也是经过严冬挑选的,在早春还很荒寒的田野上,它是春的消息之一。一同翻越雪山的,还有麦子、油菜和红花草,它们是大部队。蚕豆规模不大,却也有凌寒傲雪的气质,它厚厚的叶片鲜活如唇,它倚冻土的模样,有精气神。所以,虽非C位,在春天的合照中,也有它的一张笑脸。
蚕豆不择地。深秋种麦子、点油菜,也顺手“扎”蚕豆,扎在麦菜田四周,扎在田埂的内侧(外侧不行,外侧是别人家的)。种蚕豆不拿好地,这是乡人的共识,随便什么地,或者不是地,路肩路沿,也能结出很好的蚕豆。
蚕豆不用施肥,灌溉,治虫,除草。蚕豆大的时候,草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蚕豆小的时候,草还不敢露头,虫子就更不敢了。讲究的人家,扎蚕豆时会带一把灰粪。
蚕豆结荚,十分旺相。呼啦啦的秧子齐腰深,四四楞楞的梗子上,从根到梢插满了豆荚,雄赳赳的,像将要出征的士兵,腰间插满了“弹夹”,“弹夹”里压满了黄澄澄的“子弹”。
蚕豆泼皮,肯结。不拿口粮田待它,只种些边边角角,就能指望吃蚕豆。一家老小,从嫩蚕豆开始吃,烀着吃,蒸着吃,连皮吃,剥豆花吃,搭粥吃,做菜吃,一路紧吃慢吃,也只吃个零头。午季,麦黄豆老,蚕豆大头上来,一部分用来制酱,剩下的冬天可以炒着吃。
读鲁迅的《社戏》,我才知道蚕豆在浙东水乡也叫“罗汉豆”;再读他的《孔乙己》,我又知道,他们那里有一种用蚕豆制作的小吃,叫作“茴香豆”。我们江淮,在吃蚕豆这件事上不发挥,只是水火两样,煮熟蒸透就行,吃的是蚕豆本味。
除了“罗汉豆”,也有的地方叫它“兰花豆”,这是根据蚕豆的花型来的。我们一直叫它“蚕豆”,这也是南北通行的叫法。为什么叫它蚕豆呢?李时珍《本草纲目》上说它“豆荚如老蚕”;王祯《农书》说:“蚕时始熟,故名。”一个象形,一个会意,这些都能讲得通。叫什么或从哪里来,都不重要,喜不喜欢也不重要。蚕豆还是蚕豆,它是个老实疙瘩,不花妙,也不会绕人。
每年最后一次吃鲜蚕豆是在端午,只是吃法稍微费点事。新榨的菜籽油闪着红亮的油光,半干的蚕豆拦腰一剪,丢下油锅去炸,炸开了花,撒上细盐或是白糖,端上桌。桌子中间是一大提粽子,四周是蚕豆、油提、馓子等“油炸四小件”,蚕豆在端午戏里是小青一类的配角。
连天雨,白加黑,潮湿闷热,这是梅天到了。梅天也叫霉天,一是江南梅熟,二是家里面的东西容易生霉,本不算什么好天,却是一年一度做酱的关口。母亲只做蚕豆酱,这是南方的酱种。蚕豆易得,一“酱”难求。
新蚕豆收上来,晒干洗净,用水稍稍泡一下,就可以上锅烀了。烀熟的蚕豆,孩子们理都不理,吃了一春加半夏,再好吃的东西也败胃了。母亲将它们舀上来,沥干水,待热气散尽,豆晾凉了,用面粉拌上,然后平摊在大簸箕里。又在簸箕口担上一根扁担,再盖一层薄膜,放在墙角下就不再管它。这时,檐外的雨,不知从何时下了起来,下得慢条斯理。最后一窝鸡开抱了,母亲点着罩子灯,挨个地照它们的蛋,将“忘蛋”淘汰下来,攒攒炒给我们吃;春头上捉回的鹅黄子泛了白,食量大增,每天要吃掉一大背篓苦麻菜;母亲套着蓝色透明的雨衣,湿着头发,赤脚,高挽着裤管,站在暮色沉沉的大田里乌秧……院子当中晒酱台上的一棵栀子花终于绷不住了,“嗵”的一声炸开了,点亮了昏黄的小院。
墙角的蚕豆馊了一阵子,之后就再也闻不到馊味。大约一个礼拜,也许是十天半月不等,母亲揭开簸箕上的薄膜,里面的蚕豆上长了一层灰绿色的茸毛,像一整块草地,一寸多深,毛色很华贵。蚕豆发酵得充分,做出来的酱便有了肉的味道。母亲很满意,将它们一块块掰开,小心地捏碎,捏碎之后就不做什么了,一直等着,等天。这时候,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也很识趣地停了,太阳重新回到了天上。久雨新晴,真是个下酱的好天。母亲先烧一锅开水放着,让它自己凉透,酱缸里的陈酱还剩一点,舀出来放进一只大钵子里,再把酱缸里里外外洗个干净,木桨一样的小酱铲也洗得一身清爽。霉豆下缸,一阵轻烟;凉白开下缸,又是一阵轻烟,冰糖一样的大粒子盐整袋倒进去,酱铲下缸,使劲搅,右手酸了换左手,反正要充分搅匀,搅成糊状才算好。
晒酱是一整个夏天的心事。酱是晒成的,越晒越黑,黑里透红,最后上面汪一层油,那是最为上乘的酿造酱油,味极鲜。夏天多雷暴,雷暴狡黠,不知藏在哪块云的背后,又像鹰一样出击,常令人防不胜防,酱要晒成,实属不易。有一段时间,母亲将“盖酱钵子”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关系到未来一年全家人的味蕾,事情不小,不可马虎大意。酱缸摆在门口的晒台上,每天太阳出来后,揭开斗笠做的盖,搅动酱缸,翻它个底朝天,傍晚再搅一次。晴天的夜晚不用盖,让酱体承接天露,那样的话,酱的味道更鲜美醇厚,若是不放心,盖上酱缸,晚上会睡得比较踏实。某个午后,西山顶上悄悄升起了铁塔一样的黑云,小路上,有个提着凉鞋往家的方向飞奔的男孩,那一定是我,我要赶在那“塔”崩塌之前把酱缸盖上。
谚云:“生成的相,晒成的酱。”这是说,酱靠晒,一旦晒成,就像一个人的相貌一样不易改变。家常寡淡的日子,需要恒久而持重的酱担负起“起鲜”的责任。灶台如戏台,它是戏份很足的黑脸老包。
这以后,母亲将从地里摘来的豇豆刀豆、黄瓜菜瓜,洗干择尽,剖肚取瓤,再悉数投进酱缸里。那里有一所学校,素人小白一样的瓜菜,在里面沤一沤,也就有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