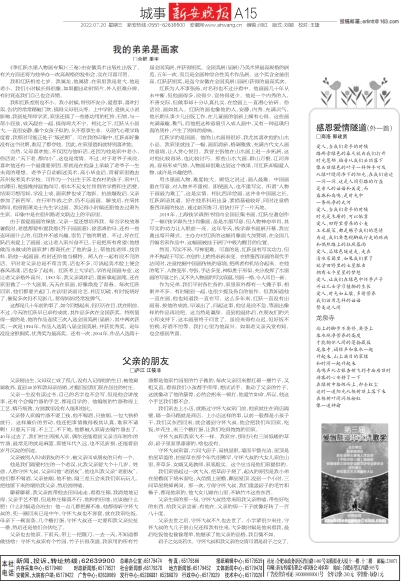发布日期:
我的弟弟是画家
□合肥季宇
《季红跃水墨人物画专集》(三卷)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方面还将为他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发布会,实在可喜可贺。
我和红跃相差七岁。我属龙,他属猪,在家里我是老大,他是老小。我们小时候长得很像,如果翻出幼时照片,外人很难分辨,有时竟连我们自己也会弄错。
我和红跃差别也不小。我小时候,特别不安分,爱惹事,喜欢打架,告状的常常踏破门坎,搞得父母很头疼。上中学时,受侠义小说影响,我到处拜师学武,家里还搞了一些练功用的杠铃、石锁,与一帮小屁孩,成天混在一起,搞得鸡犬不宁。相比之下,红跃从小到大,一直很安静,像个女孩子似的,从不惹事生非。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我那时可能正处于“叛逆期”。可在我的印象中,红跃却好像没有这个时期,谁见了都夸他。因此,在家里爸妈就特别喜欢他。
当然,父母喜欢他,不仅因为他听话,还因为他是家中老小。俗话说:“天下老,都向小”,这也是常情。不过,对于老爷子来说,喜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他身上承载了老爷子一生未竟的理想。老爷子自幼痴迷美术,高小毕业后,背着家里跑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可作为一个出生于苏北农村的孩子,家中几亩薄田,勉强维持温饱尚可,根本不足支付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结果可想而知,学没上成,画家梦也成了泡影。抗战爆发后,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在行军作战之余,仍不忘画画。解放后,在病休期间,他曾跟萧龙士先生学过画。我记得小时候还跟他去过萧先生家。印象中是在宿州路老文联边上的平房里。
由于喜爱画画的缘故,父亲一度还想培养我。每当学校放寒暑假时,老爸都要布置我描《芥子园画谱》、徐悲鸿的马,还有一些连环画什么的,但我并不感兴趣,辜负了他的期望。不过,好在红跃后来爱上了画画,这让老人家兴奋不已,于是把所有希望(他想做而未做成的画家梦)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帮他找老师、找资料,陪他一起画画,有时还给他当模特。两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平时老父亲总是不苟言笑,话也不多,可谈起美术脸上便会春风荡漾,话也多了起来。红跃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国画专业,这让老父亲格外高兴。1983年,我父亲离休后,重新拿起画笔,还在家里做了一个大画案,天天在家画,好像焕发了青春。每次红跃回家,他们都要关起门,在房里谈画论艺,相互切磋,有时饭烧好了,催促多次仍不见影儿,惹得妈妈经常发脾气。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犹在眼前。不过,今天的红跃早已卓有成就,其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连续三次入选全国美展(届展),其中两次获奖:一次是1994年,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是年没设金银铜奖,优秀奖为最高奖。还有一次,2004年,作品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获得银奖。全国美展(届展)乃美术界最高规格的展览,五年一次,而且是全画种综合性美术作品展。这个奖含金量很高,红跃获银奖,是迄今安徽在全国美展(届展)获得的最高奖次。
红跃为人不事张扬,对名利也不过分看中。他画画几十年从未中断,但他画得多,说得少,宣传得更少。他是一个内秀的人,不善交际,但做事却十分认真扎实,在绘画上一直潜心钻研。俗话说,画如其人。红跃的画也像他的人,安静,内秀,充满灵气。他长期从事少儿出版工作,在儿童画的创新上颇有心得。这些画充满童趣,稚气,而他把这种意境引入成人画中,又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质朴,产生了别样的韵味。
红跃学的是国画。他的山水画得很好,我尤其喜欢他的山水小品。我家里就挂了一幅,画面清新,格调雅致,充满古代文人画的意境,让人赏心悦目。我曾主张他在山水画上进一步拓展,这对他比较容易,也比较讨巧。那些山水大画,群山万壑,江河奔流,容易形成气势,人物画却很难达到这个效果,可红跃却偏爱人物,或许是兴趣使然。
用水墨画人物,难度较大。顾恺之说过,画人最难。中国画重在写意,对人物并不重视。即便画人,也不重写实。所谓“人物于画最为难工”,这是实情。相比西洋绘画,这并非中国画之长。红跃深谙其道。好在他系科班出身,素描基础较好,同时注意借鉴西洋画的技法,通过刻苦练习,很快打开了一片天地。
2019年,上海钱学森图书馆向全国征集书画,红跃应邀创作了一幅《钱学森先生》肖像画,虽是水墨写意,但人物神态毕肖,其写实的功力让人眼前一亮。这年冬天,钱学森书画展开幕,我应邀出席开幕式。主办方对红跃的这幅肖像画大加赞颂,在全国几百幅名家作品中,这幅画被挂于展厅中极为醒目的位置。
然而,写实不易,写神更难。可喜的是,红跃虽有写实功力,但并不拘泥于写实,在创作上始终求新求变。在借鉴西洋画的现代手法同时,注意挖掘中国画传统的意境,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他的笔下,人物变形、夸张,手法多变,神似胜于形似,充分发挥了水墨画的写意之长,又不失人物画的写实底蕴,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兄弟,我们平时各忙各的,家里家外都有一大摊子事,相聚并不多。有时碰到一起,也很少提及各自的创作。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画,他也知道我一直在写。这么多年来,红跃一直没有出画册,按他的成就,早该出了,问起这事,他总是说不急,等画出像样的作品再说吧。这当然是谦辞。直到他退休后,在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这本画册终于问世了。虽说来得有点迟,但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等。我打心里为他高兴。如果老父亲天堂有知,也会感到欣喜。
《季红跃水墨人物画专集》(三卷)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方面还将为他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发布会,实在可喜可贺。
我和红跃相差七岁。我属龙,他属猪,在家里我是老大,他是老小。我们小时候长得很像,如果翻出幼时照片,外人很难分辨,有时竟连我们自己也会弄错。
我和红跃差别也不小。我小时候,特别不安分,爱惹事,喜欢打架,告状的常常踏破门坎,搞得父母很头疼。上中学时,受侠义小说影响,我到处拜师学武,家里还搞了一些练功用的杠铃、石锁,与一帮小屁孩,成天混在一起,搞得鸡犬不宁。相比之下,红跃从小到大,一直很安静,像个女孩子似的,从不惹事生非。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我那时可能正处于“叛逆期”。可在我的印象中,红跃却好像没有这个时期,谁见了都夸他。因此,在家里爸妈就特别喜欢他。
当然,父母喜欢他,不仅因为他听话,还因为他是家中老小。俗话说:“天下老,都向小”,这也是常情。不过,对于老爷子来说,喜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他身上承载了老爷子一生未竟的理想。老爷子自幼痴迷美术,高小毕业后,背着家里跑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可作为一个出生于苏北农村的孩子,家中几亩薄田,勉强维持温饱尚可,根本不足支付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结果可想而知,学没上成,画家梦也成了泡影。抗战爆发后,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在行军作战之余,仍不忘画画。解放后,在病休期间,他曾跟萧龙士先生学过画。我记得小时候还跟他去过萧先生家。印象中是在宿州路老文联边上的平房里。
由于喜爱画画的缘故,父亲一度还想培养我。每当学校放寒暑假时,老爸都要布置我描《芥子园画谱》、徐悲鸿的马,还有一些连环画什么的,但我并不感兴趣,辜负了他的期望。不过,好在红跃后来爱上了画画,这让老人家兴奋不已,于是把所有希望(他想做而未做成的画家梦)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帮他找老师、找资料,陪他一起画画,有时还给他当模特。两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平时老父亲总是不苟言笑,话也不多,可谈起美术脸上便会春风荡漾,话也多了起来。红跃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国画专业,这让老父亲格外高兴。1983年,我父亲离休后,重新拿起画笔,还在家里做了一个大画案,天天在家画,好像焕发了青春。每次红跃回家,他们都要关起门,在房里谈画论艺,相互切磋,有时饭烧好了,催促多次仍不见影儿,惹得妈妈经常发脾气。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犹在眼前。不过,今天的红跃早已卓有成就,其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连续三次入选全国美展(届展),其中两次获奖:一次是1994年,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是年没设金银铜奖,优秀奖为最高奖。还有一次,2004年,作品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获得银奖。全国美展(届展)乃美术界最高规格的展览,五年一次,而且是全画种综合性美术作品展。这个奖含金量很高,红跃获银奖,是迄今安徽在全国美展(届展)获得的最高奖次。
红跃为人不事张扬,对名利也不过分看中。他画画几十年从未中断,但他画得多,说得少,宣传得更少。他是一个内秀的人,不善交际,但做事却十分认真扎实,在绘画上一直潜心钻研。俗话说,画如其人。红跃的画也像他的人,安静,内秀,充满灵气。他长期从事少儿出版工作,在儿童画的创新上颇有心得。这些画充满童趣,稚气,而他把这种意境引入成人画中,又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质朴,产生了别样的韵味。
红跃学的是国画。他的山水画得很好,我尤其喜欢他的山水小品。我家里就挂了一幅,画面清新,格调雅致,充满古代文人画的意境,让人赏心悦目。我曾主张他在山水画上进一步拓展,这对他比较容易,也比较讨巧。那些山水大画,群山万壑,江河奔流,容易形成气势,人物画却很难达到这个效果,可红跃却偏爱人物,或许是兴趣使然。
用水墨画人物,难度较大。顾恺之说过,画人最难。中国画重在写意,对人物并不重视。即便画人,也不重写实。所谓“人物于画最为难工”,这是实情。相比西洋绘画,这并非中国画之长。红跃深谙其道。好在他系科班出身,素描基础较好,同时注意借鉴西洋画的技法,通过刻苦练习,很快打开了一片天地。
2019年,上海钱学森图书馆向全国征集书画,红跃应邀创作了一幅《钱学森先生》肖像画,虽是水墨写意,但人物神态毕肖,其写实的功力让人眼前一亮。这年冬天,钱学森书画展开幕,我应邀出席开幕式。主办方对红跃的这幅肖像画大加赞颂,在全国几百幅名家作品中,这幅画被挂于展厅中极为醒目的位置。
然而,写实不易,写神更难。可喜的是,红跃虽有写实功力,但并不拘泥于写实,在创作上始终求新求变。在借鉴西洋画的现代手法同时,注意挖掘中国画传统的意境,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他的笔下,人物变形、夸张,手法多变,神似胜于形似,充分发挥了水墨画的写意之长,又不失人物画的写实底蕴,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兄弟,我们平时各忙各的,家里家外都有一大摊子事,相聚并不多。有时碰到一起,也很少提及各自的创作。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画,他也知道我一直在写。这么多年来,红跃一直没有出画册,按他的成就,早该出了,问起这事,他总是说不急,等画出像样的作品再说吧。这当然是谦辞。直到他退休后,在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下,这本画册终于问世了。虽说来得有点迟,但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等。我打心里为他高兴。如果老父亲天堂有知,也会感到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