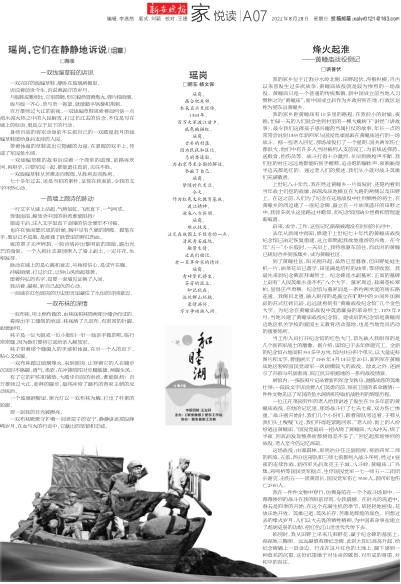发布日期:
烽火起淮
□谈善伏
我的家乡位于江淮分水岭北侧,田野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以来曾发生过多次战争,黄疃庙战役就是较为惨烈的一场战役。黄疃庙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集镇,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黄疃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乡政府所在地,行政区划称为肥东县黄疃乡。
我的家乡距黄疃庙有10多里的路程,在我很小的时候,夜晚,忙碌一天的人们就会坐到村里的一棵大槐树下“讲经”(讲故事),最令我们这群孩子感兴趣的当属打仗的故事,年长一点的常常会说到1945年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在黄疃庙进行的一场战斗。据一些老人回忆,那场战役打了一个星期,国共两军伤亡都很大,他们中有许多人当时被列入支前民工,为前线送弹药、送粮食、抬伤员等。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早到晚枪声不断,我们住的村庄远远地都能听到手榴弹、迫击炮的爆炸声,夜晚映得半边天都是红的。通过老人们的描述,我们从小就对战斗英雄们充满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经过黄疃乡一片高坡时,还隐约看到当年战士们挖的战壕,深深浅浅地横亘在大路的两侧以及田野上。在这之前,人们为了纪念在这场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将士,在黄疃乡的西边建了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一片油菜盛开的田野之中,我曾多次从这里路过并瞻仰,而纪念馆因缺少经费和管理逐渐破落。
后来,求学、工作,这些记忆渐渐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去年从新闻中得知,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疃庙战役纪念馆已决定恢复重建,这立即燃起我故地重游的兴致。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时,一天早上,我特意驱车前往,而此时的黄疃已规划合并到张集乡,成为黄疃社区。
到了黄疃社区,阳光刚升起,虽然已至暮春,但田野处处生机一片,油菜花早已落尽,田里满是结籽的油菜,等待收割。我最先来到纪念碑前拜谒烈士。纪念碑是水泥墓冢,正面的墓碑上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墓冢周边,栽满苍松翠柏,显得庄严肃穆。纪念馆与墓冢间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砖石路连通。我侧目北望,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旷野中的10间外加厢房的苏式红砖瓦房,远远就看到有“黄疃战役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为纪念在黄疃庙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1978年9月,当地兴建了黄疃庙战役纪念馆。建成后的纪念馆是黄疃周边地区机关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基地,也是当地党员活动的重要场所。
当工作人员打开纪念馆的红色大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几个新四军战士的雕像。据介绍,该馆已于去年修建完工。全新的纪念馆占地面积350多平方米,馆内共分四个单元,以大量史料图片和文字,着重展示了1945年4月14日至20日,新四军在黄疃庙地区粉碎国民党顽军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除此之外,还展示了开辟与巩固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战役情景。
展馆内,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新四军金戈铁马、驰骋战场的英雄壮举;一段段文字诉说着人们英勇向前、保家卫国的革命激情;一件件文物见证了军民的鱼水深情和夺取抗战胜利的辉煌历程。
一位正在菜园劳作的老人给我讲述了发生在70多年前的黄疃庙战役,在他的记忆里,那场战斗打了七天七夜,双方伤亡惨重。“战斗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小伢们,跟着部队旁边看,子弹从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我们吓得赶紧跑回家。”老人说,街上的人纷纷逃出黄疃庙,“国民党最后一把火烧了黄疃庙,大火冲天,烧了半夜,回家后发现整条街都烧得差不多了。”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老人至今仍记忆深刻。
这场战役,由谭震林、彭明治分任正副指挥,将新四军二师的四旅、五旅、西分区部队和三师七旅都列入战斗序列,经过6昼夜的连续作战,新四军先后攻克王子城、八斗岭、黄疃庙、广兴集、鸡鸣桥等国民党军据点,生俘国民党军一七一师五一二团团长谢克,击伤五一一团黄团长,国民党军伤亡3600人,新四军也伤亡2500人。
我在一件件文物中穿行,仿佛身陷在一个个战斗场景中,一幕幕惨烈的战斗在我的眼前浮现,令我震撼。在时光的流逝中,春天是四季的开始,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草轻轻地摇曳,花快乐地开放。英雄已逝,英风长存,苦难是辉煌的底色。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人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临别时,我从田野上采来几束野花,献于纪念碑的基座上,深深地三鞠躬。远远凝望英雄纪念碑,此时太阳已高高升起,给纪念碑镀上一层金边。行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脚下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这份沉重缘于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和平的向往。
我的家乡位于江淮分水岭北侧,田野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以来曾发生过多次战争,黄疃庙战役就是较为惨烈的一场战役。黄疃庙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集镇,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黄疃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乡政府所在地,行政区划称为肥东县黄疃乡。
我的家乡距黄疃庙有10多里的路程,在我很小的时候,夜晚,忙碌一天的人们就会坐到村里的一棵大槐树下“讲经”(讲故事),最令我们这群孩子感兴趣的当属打仗的故事,年长一点的常常会说到1945年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在黄疃庙进行的一场战斗。据一些老人回忆,那场战役打了一个星期,国共两军伤亡都很大,他们中有许多人当时被列入支前民工,为前线送弹药、送粮食、抬伤员等。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早到晚枪声不断,我们住的村庄远远地都能听到手榴弹、迫击炮的爆炸声,夜晚映得半边天都是红的。通过老人们的描述,我们从小就对战斗英雄们充满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经过黄疃乡一片高坡时,还隐约看到当年战士们挖的战壕,深深浅浅地横亘在大路的两侧以及田野上。在这之前,人们为了纪念在这场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将士,在黄疃乡的西边建了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一片油菜盛开的田野之中,我曾多次从这里路过并瞻仰,而纪念馆因缺少经费和管理逐渐破落。
后来,求学、工作,这些记忆渐渐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去年从新闻中得知,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疃庙战役纪念馆已决定恢复重建,这立即燃起我故地重游的兴致。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时,一天早上,我特意驱车前往,而此时的黄疃已规划合并到张集乡,成为黄疃社区。
到了黄疃社区,阳光刚升起,虽然已至暮春,但田野处处生机一片,油菜花早已落尽,田里满是结籽的油菜,等待收割。我最先来到纪念碑前拜谒烈士。纪念碑是水泥墓冢,正面的墓碑上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墓冢周边,栽满苍松翠柏,显得庄严肃穆。纪念馆与墓冢间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砖石路连通。我侧目北望,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旷野中的10间外加厢房的苏式红砖瓦房,远远就看到有“黄疃战役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为纪念在黄疃庙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1978年9月,当地兴建了黄疃庙战役纪念馆。建成后的纪念馆是黄疃周边地区机关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基地,也是当地党员活动的重要场所。
当工作人员打开纪念馆的红色大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几个新四军战士的雕像。据介绍,该馆已于去年修建完工。全新的纪念馆占地面积350多平方米,馆内共分四个单元,以大量史料图片和文字,着重展示了1945年4月14日至20日,新四军在黄疃庙地区粉碎国民党顽军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除此之外,还展示了开辟与巩固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战役情景。
展馆内,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新四军金戈铁马、驰骋战场的英雄壮举;一段段文字诉说着人们英勇向前、保家卫国的革命激情;一件件文物见证了军民的鱼水深情和夺取抗战胜利的辉煌历程。
一位正在菜园劳作的老人给我讲述了发生在70多年前的黄疃庙战役,在他的记忆里,那场战斗打了七天七夜,双方伤亡惨重。“战斗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小伢们,跟着部队旁边看,子弹从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我们吓得赶紧跑回家。”老人说,街上的人纷纷逃出黄疃庙,“国民党最后一把火烧了黄疃庙,大火冲天,烧了半夜,回家后发现整条街都烧得差不多了。”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老人至今仍记忆深刻。
这场战役,由谭震林、彭明治分任正副指挥,将新四军二师的四旅、五旅、西分区部队和三师七旅都列入战斗序列,经过6昼夜的连续作战,新四军先后攻克王子城、八斗岭、黄疃庙、广兴集、鸡鸣桥等国民党军据点,生俘国民党军一七一师五一二团团长谢克,击伤五一一团黄团长,国民党军伤亡3600人,新四军也伤亡2500人。
我在一件件文物中穿行,仿佛身陷在一个个战斗场景中,一幕幕惨烈的战斗在我的眼前浮现,令我震撼。在时光的流逝中,春天是四季的开始,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草轻轻地摇曳,花快乐地开放。英雄已逝,英风长存,苦难是辉煌的底色。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人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临别时,我从田野上采来几束野花,献于纪念碑的基座上,深深地三鞠躬。远远凝望英雄纪念碑,此时太阳已高高升起,给纪念碑镀上一层金边。行走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脚下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这份沉重缘于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对和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