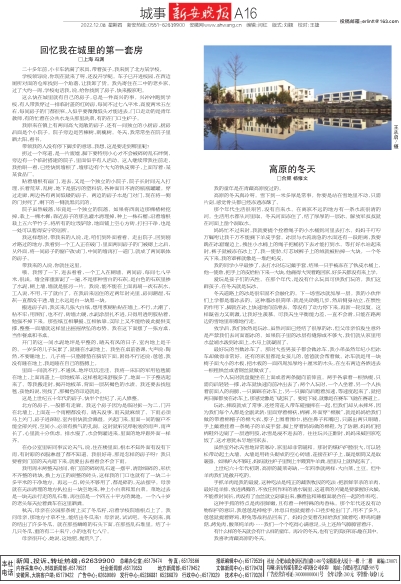发布日期:
回忆我在城里的第一套房
□上海冯渊
二十多年前,小卡车装满了家具,带着孩子,我来到了北方某学校。
学校领导说,你现在就来了呀,还没开学呢。车子已开进校园,在西边厕所对面的仓库找到一个角落,让我卸了货。我先寄住在二中的老乡家。过了大约一周,学校电话我,说,给你找到了房子,快来搬家吧。
这么快在城里就有自己的房子,总是一件高兴的事。兴冲冲跑到学校,有人带我穿过一排临时盖的红砖房,每间不过七八平米,高度两米五左右,每间房子的门都很窄,人似乎要微微低头才能进去,门口走动的是青年教师,有的忙着在公共水龙头那里洗菜,有的在门口生炉子。
我原来在镇上有两间高大宽敞的房子,还有一间独立的小厨房,厨房后面是个小院子。院子旁边是苦楝树、刺槐树。冬天,我常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
带领我的人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我想,这是要走到哪里呢?
拐过一个弯道,是一片废墟,脚下要特别小心才不会被碎砖乱石绊倒,旁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院子,里面似乎有人活动。这人继续带我往前走,我抬眼一看,已经快到墙根了,墙那边有个大大的铁皮牌子,上面写着:某某食品厂。
贴着墙根有扇门,进去,又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子长时间无人打理,长着荒草,乱树,地下是脏污的塑料袋,各种面目不清的瓶瓶罐罐。穿过走廊,两边各有两间低矮的房子。两边的房子本是门对门,现在将一侧的门封死了,剩下的一侧就黑沉沉的。
院子虽然破落,毕竟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如果将西南边那棵楮树挖掉,栽上一棵木樨;靠近房子的那丛灌木清理掉,种上一株石榴;沿着墙根栽上五六竿竹子,将所有的垃圾铲除,地面铺上空心方砖,打扫干净,也是一处可以暂得安宁的居所。
我这样想时,带我来的人说,走,咱们到外面看看。走出院子,回到刚才路过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破门:里面两间房子的门被砌上之后,从外面,将一间房子的窗户改成门,中间的墙再打一道门,就成了两间联体的房子。
带我来的人说,你就住这里。
哦。我愣了一下,进去看看,一个工人在糊墙。两间房,每间七八平米,很浅。墙全部重新泥了一遍,不是那种雪白的石灰,是白色的石灰里掺了水泥,糊上墙,墙就是脏污一片。我说,能不能在上面再刷一次石灰水。工人说,不用,干了就白了。在我后来居住的近两年时光里,房间潮湿,石灰一直都没干透,墙上永远是白一块黑一块。
搬进房子后,我买来几张大白纸,想用浆糊粘贴在墙上,不行,太潮了,粘不牢;用图钉,也不行,砖墙太硬,水泥涂层扎不进,只得用透明胶粘着,勉强不掉下来。那些纸互相攀援、互相依靠,实际上又不能给彼此提供支撑,整整一面墙就这样显出摇摇欲坠的态势。我在这下面摆了一张方桌,当作餐桌和书桌。
开门的这一间水泥地坪是平整的,晴天有风的日子,室内地上是干的。一岁多的儿子玩累了,就睡在水泥地上。我坐在桌前备课,大声说:陶然,不要睡地上。儿子将一只胳膊垫在脑袋下面,困得不行还说:爸爸,我没有睡在地上,我是睡在自己的胳膊上。
里面一间就不行,不通风,地坪坑坑洼洼。我将一床旧的军用毡毯铺在地上,上面再盖上一层地板革,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地面一下子整洁起来了。等我搬走时,揭开地板革,背面一层灰褐色的水渍。我还要去找毡毯,孩他妈说,别找了,那褐色的印迹就是。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子,快半个世纪了,无人修整。
北方的房子,一般都有走廊。我这个房子因为是临时拆一为二,门开在北墙上,上面连一个雨棚都没有。晴天没事,雨天就麻烦了。下雨必须马上关门,房子进深短,室内很快就会溅湿。关起门来,里面一间的窗户不能全部关死,空间小,必须有换气的孔洞。这时就听见哗啦啦的雨声,雨声长了,心里就十分焦虑。排水慢了,水会倒灌进来,里面的地坪跟外面一样齐。
在办公室里听同事议论天气,说,住在楼里面,根本不知外面有没有下雨,有时晾的衣服淋湿了都不知道。我很好奇,那是怎样的房子呀?我只要看到门前的天光暗下来,就要出去看看会不会下雨。
我用周末两整天时间,将门前的碎砖乱石逐一摆平,清除细碎的、形状不齐整的砖块,换上方正的规整的砖头,这样我的门口也就有了一块二十多平米的干净地方。再远一点,砖头不够用了,都是碎的,无法摆平。母亲就在无法清理的地方扒拉出一块空地来,种上小白菜和黑白菜。菜地过去是一块无法行走的乱石堆,再往前是一个四五十平方的粪池。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每天拉着粪车在这里晒粪。
秋天,母亲在公园那条街上买了冬瓜籽,沿着学校院墙根点上了。我问母亲,那地方寸草不生,能结出冬瓜来?母亲说,试试吧。冬天到来,真的结出了许多冬瓜。就在那些嶙峋的石头下面,在那些乱石堆里。结了十几只冬瓜,重的有二十来斤,小的也有七八斤。
母亲很开心,她说,这地肥,抛荒久了。
二十多年前,小卡车装满了家具,带着孩子,我来到了北方某学校。
学校领导说,你现在就来了呀,还没开学呢。车子已开进校园,在西边厕所对面的仓库找到一个角落,让我卸了货。我先寄住在二中的老乡家。过了大约一周,学校电话我,说,给你找到了房子,快来搬家吧。
这么快在城里就有自己的房子,总是一件高兴的事。兴冲冲跑到学校,有人带我穿过一排临时盖的红砖房,每间不过七八平米,高度两米五左右,每间房子的门都很窄,人似乎要微微低头才能进去,门口走动的是青年教师,有的忙着在公共水龙头那里洗菜,有的在门口生炉子。
我原来在镇上有两间高大宽敞的房子,还有一间独立的小厨房,厨房后面是个小院子。院子旁边是苦楝树、刺槐树。冬天,我常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
带领我的人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我想,这是要走到哪里呢?
拐过一个弯道,是一片废墟,脚下要特别小心才不会被碎砖乱石绊倒,旁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院子,里面似乎有人活动。这人继续带我往前走,我抬眼一看,已经快到墙根了,墙那边有个大大的铁皮牌子,上面写着:某某食品厂。
贴着墙根有扇门,进去,又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子长时间无人打理,长着荒草,乱树,地下是脏污的塑料袋,各种面目不清的瓶瓶罐罐。穿过走廊,两边各有两间低矮的房子。两边的房子本是门对门,现在将一侧的门封死了,剩下的一侧就黑沉沉的。
院子虽然破落,毕竟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如果将西南边那棵楮树挖掉,栽上一棵木樨;靠近房子的那丛灌木清理掉,种上一株石榴;沿着墙根栽上五六竿竹子,将所有的垃圾铲除,地面铺上空心方砖,打扫干净,也是一处可以暂得安宁的居所。
我这样想时,带我来的人说,走,咱们到外面看看。走出院子,回到刚才路过的地方,我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破门:里面两间房子的门被砌上之后,从外面,将一间房子的窗户改成门,中间的墙再打一道门,就成了两间联体的房子。
带我来的人说,你就住这里。
哦。我愣了一下,进去看看,一个工人在糊墙。两间房,每间七八平米,很浅。墙全部重新泥了一遍,不是那种雪白的石灰,是白色的石灰里掺了水泥,糊上墙,墙就是脏污一片。我说,能不能在上面再刷一次石灰水。工人说,不用,干了就白了。在我后来居住的近两年时光里,房间潮湿,石灰一直都没干透,墙上永远是白一块黑一块。
搬进房子后,我买来几张大白纸,想用浆糊粘贴在墙上,不行,太潮了,粘不牢;用图钉,也不行,砖墙太硬,水泥涂层扎不进,只得用透明胶粘着,勉强不掉下来。那些纸互相攀援、互相依靠,实际上又不能给彼此提供支撑,整整一面墙就这样显出摇摇欲坠的态势。我在这下面摆了一张方桌,当作餐桌和书桌。
开门的这一间水泥地坪是平整的,晴天有风的日子,室内地上是干的。一岁多的儿子玩累了,就睡在水泥地上。我坐在桌前备课,大声说:陶然,不要睡地上。儿子将一只胳膊垫在脑袋下面,困得不行还说:爸爸,我没有睡在地上,我是睡在自己的胳膊上。
里面一间就不行,不通风,地坪坑坑洼洼。我将一床旧的军用毡毯铺在地上,上面再盖上一层地板革,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地面一下子整洁起来了。等我搬走时,揭开地板革,背面一层灰褐色的水渍。我还要去找毡毯,孩他妈说,别找了,那褐色的印迹就是。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子,快半个世纪了,无人修整。
北方的房子,一般都有走廊。我这个房子因为是临时拆一为二,门开在北墙上,上面连一个雨棚都没有。晴天没事,雨天就麻烦了。下雨必须马上关门,房子进深短,室内很快就会溅湿。关起门来,里面一间的窗户不能全部关死,空间小,必须有换气的孔洞。这时就听见哗啦啦的雨声,雨声长了,心里就十分焦虑。排水慢了,水会倒灌进来,里面的地坪跟外面一样齐。
在办公室里听同事议论天气,说,住在楼里面,根本不知外面有没有下雨,有时晾的衣服淋湿了都不知道。我很好奇,那是怎样的房子呀?我只要看到门前的天光暗下来,就要出去看看会不会下雨。
我用周末两整天时间,将门前的碎砖乱石逐一摆平,清除细碎的、形状不齐整的砖块,换上方正的规整的砖头,这样我的门口也就有了一块二十多平米的干净地方。再远一点,砖头不够用了,都是碎的,无法摆平。母亲就在无法清理的地方扒拉出一块空地来,种上小白菜和黑白菜。菜地过去是一块无法行走的乱石堆,再往前是一个四五十平方的粪池。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每天拉着粪车在这里晒粪。
秋天,母亲在公园那条街上买了冬瓜籽,沿着学校院墙根点上了。我问母亲,那地方寸草不生,能结出冬瓜来?母亲说,试试吧。冬天到来,真的结出了许多冬瓜。就在那些嶙峋的石头下面,在那些乱石堆里。结了十几只冬瓜,重的有二十来斤,小的也有七八斤。
母亲很开心,她说,这地肥,抛荒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