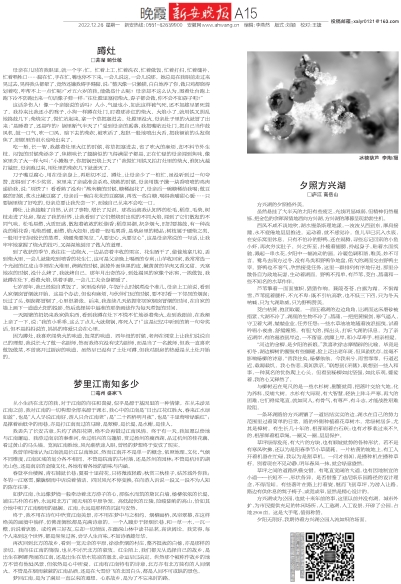发布日期:
蹲灶
□芜湖鲍仕敏
母亲在儿时的我眼里,就一个字:忙。忙着上工,忙着洗衣,忙着做饭,忙着打扫,忙着缝补,忙着喂牲口……脚在忙,手在忙,嘴也停不下来,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她总是在我眼前走过来晃过去,晃得我头都晕了,竟然还嫌我碍手碍脚,说:“整天像一只懒猫,白白地养了你,做只鸡都晓得划着吃,咋帮不上一点忙呢?”才五六岁的我,能做些什么呢?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围着灶台跑上跑下冷不防跑出来一句话像子弹一样:“往灶膛里塞把柴火,孬子都会做,你不会不如孬子吧!”
这话多伤人!像一个亲娘说的话吗?人小,气量也小,如此这样被气死,还不如趁早累死算了。我拎来比我还小的凳子,小狗一样蹲在灶门,盯着那赤红的柴火。火焰小了,就用铁叉胡乱地捣鼓几下;柴烧完了,慌忙站起来,拿一个草把塞进去。灶膛里没火,母亲肚子里的火就冒了出来:“是睡着了,还是咋的?锅里断气半天了!”受到母亲的奚落,我把嘴贴近灶门,把自己当作鼓风机,鼓一口气,吹一口风。暗下去的柴灰,被吹活了,发狠一般地喷出火舌,把我额前的头发烧焦了,眼眶里的泪水也呛出来了。
吃一堑,长一智,我趁着灶里火红的时候,将草把塞进去,省了吹火的麻烦,却不料节外生枝。闷饭的时候柴添多了,焦糊味长了翅膀似的飞得满屋子都是,正在忙碌的母亲闻到焦味,像家里失了火一样大叫:“小摊炮子,你把锅巴烧上天了!”我慌忙用铁叉拍打灶里的柴火,谁知火越打越旺,母亲跑过来,用灶里的柴灰几下就盖灭了。
刀子嘴豆腐心,用在母亲身上,再贴切不过。蹲灶,让母亲少了一桩忙,虽没听到过一句夸赞,却得到了不少奖赏。家里来了亲戚准会杀鸡,烧熟的时候,母亲用筷子搛一块香喷喷的鸡肉递给我,说:“别烫了!看看熟了没有?”熬米糖的时候,糖稀起花了,母亲舀一碗糖稀给我喝;做豆腐的时候,浆水出嫩豆腐了,母亲舀一碗白花花的豆腐脑,再放一些白糖,喝得我嘴甜心暖……只要锅里烧了好吃的,母亲总要让我先尝一下,而她自己从来不会吃一口。
蹲灶,让我接触了自然,认识了事物,增长了见识。那些远离我认知界的松毛、稻草、毛柴、树枝走进了灶房,靠近了我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它们燃烧时出现的不同火焰,闻到了它们散发的不同气味。松毛易燃,火质旺盛,散发着浓浓的松脂香;稻草易潮,灰多烟大,时时要捣鼓,有一种淡淡的稻花香;毛柴质硬,耐燃,焰火如炬,透着一股毛栗香,是柴房里的精品;树枝属于硬柴之类,一般用于时间较长的蒸煮。烧硬柴要架空,“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让我牢牢地掌握了烧火的技巧,又深深地刻印了做人的道理。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往往一边烧火,一边品尝着丰收的果实。花生晒干了,偷偷地拿几粒,丢到柴火里,一会儿就能吃到喷香的花生仁,这可是父亲晚上喝酒的专利;山芋收回家,我常常选一个光润的红皮山芋埋在火堆里,烤熟的时候,剥掉外面焦黑的皮,嫩黄黄的芋肉又香又甜。天寒地冻的时候,没什么烤了,我就烤自己。那年月出奇的冷,到处漏风的家像个冰窖,一挨做饭,我就蹲在灶下,看着火焰,烘着手脚,一会儿工夫全身都暖了。
七岁那年,我已经独自煮饭了。家里没有钟,午饭什么时候煮没个准儿,母亲上工前说,看到人家烟囱冒烟就开始。这是个办法,但也有麻烦,与伙伴们玩的时候,要不时看一下邻居的烟囱;玩过了头,烟囱都冒烟了,心里很紧张。后来,我连续几天依据邻居家烟囱冒烟的时间,在自家的墙上画下一道道太阳的投影,然后选择其中最准的那条画线作为每天煮饭的时间。
一天隔壁的奶奶来我家借东西,看到我蹲在灶下不慌不忙地添着柴火,走到我跟前,在我额上亲了一下,说:“我的小乖乖,这么丁点儿大就烧锅,疼死人了!”这是记忆中听到的第一句夸奖话,但不是妈妈说的,妈妈的疼爱只会在心里。
因为蹲灶,我喜欢闻柴火的味道,饭菜的味道。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说说自己的理想,我说长大了做一名厨师,然而我终究没有成为厨师,而是当了一名教师,但我一直喜欢做饭做菜,不曾离开过厨房的味道。虽然早已没有了土灶可蹲,但我对厨房的热爱是从土灶开始的。
母亲在儿时的我眼里,就一个字:忙。忙着上工,忙着洗衣,忙着做饭,忙着打扫,忙着缝补,忙着喂牲口……脚在忙,手在忙,嘴也停不下来,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她总是在我眼前走过来晃过去,晃得我头都晕了,竟然还嫌我碍手碍脚,说:“整天像一只懒猫,白白地养了你,做只鸡都晓得划着吃,咋帮不上一点忙呢?”才五六岁的我,能做些什么呢?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围着灶台跑上跑下冷不防跑出来一句话像子弹一样:“往灶膛里塞把柴火,孬子都会做,你不会不如孬子吧!”
这话多伤人!像一个亲娘说的话吗?人小,气量也小,如此这样被气死,还不如趁早累死算了。我拎来比我还小的凳子,小狗一样蹲在灶门,盯着那赤红的柴火。火焰小了,就用铁叉胡乱地捣鼓几下;柴烧完了,慌忙站起来,拿一个草把塞进去。灶膛里没火,母亲肚子里的火就冒了出来:“是睡着了,还是咋的?锅里断气半天了!”受到母亲的奚落,我把嘴贴近灶门,把自己当作鼓风机,鼓一口气,吹一口风。暗下去的柴灰,被吹活了,发狠一般地喷出火舌,把我额前的头发烧焦了,眼眶里的泪水也呛出来了。
吃一堑,长一智,我趁着灶里火红的时候,将草把塞进去,省了吹火的麻烦,却不料节外生枝。闷饭的时候柴添多了,焦糊味长了翅膀似的飞得满屋子都是,正在忙碌的母亲闻到焦味,像家里失了火一样大叫:“小摊炮子,你把锅巴烧上天了!”我慌忙用铁叉拍打灶里的柴火,谁知火越打越旺,母亲跑过来,用灶里的柴灰几下就盖灭了。
刀子嘴豆腐心,用在母亲身上,再贴切不过。蹲灶,让母亲少了一桩忙,虽没听到过一句夸赞,却得到了不少奖赏。家里来了亲戚准会杀鸡,烧熟的时候,母亲用筷子搛一块香喷喷的鸡肉递给我,说:“别烫了!看看熟了没有?”熬米糖的时候,糖稀起花了,母亲舀一碗糖稀给我喝;做豆腐的时候,浆水出嫩豆腐了,母亲舀一碗白花花的豆腐脑,再放一些白糖,喝得我嘴甜心暖……只要锅里烧了好吃的,母亲总要让我先尝一下,而她自己从来不会吃一口。
蹲灶,让我接触了自然,认识了事物,增长了见识。那些远离我认知界的松毛、稻草、毛柴、树枝走进了灶房,靠近了我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它们燃烧时出现的不同火焰,闻到了它们散发的不同气味。松毛易燃,火质旺盛,散发着浓浓的松脂香;稻草易潮,灰多烟大,时时要捣鼓,有一种淡淡的稻花香;毛柴质硬,耐燃,焰火如炬,透着一股毛栗香,是柴房里的精品;树枝属于硬柴之类,一般用于时间较长的蒸煮。烧硬柴要架空,“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让我牢牢地掌握了烧火的技巧,又深深地刻印了做人的道理。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往往一边烧火,一边品尝着丰收的果实。花生晒干了,偷偷地拿几粒,丢到柴火里,一会儿就能吃到喷香的花生仁,这可是父亲晚上喝酒的专利;山芋收回家,我常常选一个光润的红皮山芋埋在火堆里,烤熟的时候,剥掉外面焦黑的皮,嫩黄黄的芋肉又香又甜。天寒地冻的时候,没什么烤了,我就烤自己。那年月出奇的冷,到处漏风的家像个冰窖,一挨做饭,我就蹲在灶下,看着火焰,烘着手脚,一会儿工夫全身都暖了。
七岁那年,我已经独自煮饭了。家里没有钟,午饭什么时候煮没个准儿,母亲上工前说,看到人家烟囱冒烟就开始。这是个办法,但也有麻烦,与伙伴们玩的时候,要不时看一下邻居的烟囱;玩过了头,烟囱都冒烟了,心里很紧张。后来,我连续几天依据邻居家烟囱冒烟的时间,在自家的墙上画下一道道太阳的投影,然后选择其中最准的那条画线作为每天煮饭的时间。
一天隔壁的奶奶来我家借东西,看到我蹲在灶下不慌不忙地添着柴火,走到我跟前,在我额上亲了一下,说:“我的小乖乖,这么丁点儿大就烧锅,疼死人了!”这是记忆中听到的第一句夸奖话,但不是妈妈说的,妈妈的疼爱只会在心里。
因为蹲灶,我喜欢闻柴火的味道,饭菜的味道。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说说自己的理想,我说长大了做一名厨师,然而我终究没有成为厨师,而是当了一名教师,但我一直喜欢做饭做菜,不曾离开过厨房的味道。虽然早已没有了土灶可蹲,但我对厨房的热爱是从土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