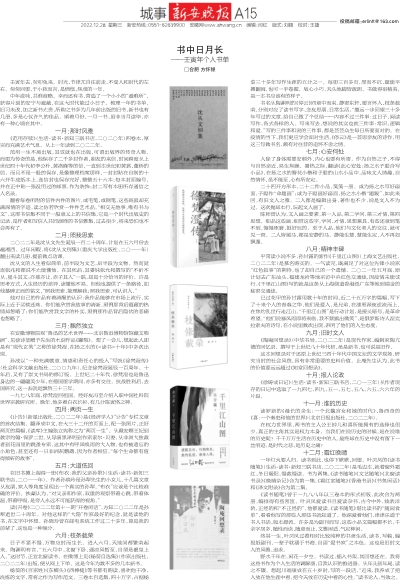发布日期:
书中日月长
□合肥方怀银
壬寅年去,癸卯兔来。时光、节律兀自往前走,不受人和时代的左右。匆匆回望,于小我而言,是恓惶、焦虑的一年。
中年滋味,共谁商略。幸而还有书,营造了一个小小的“避难所”,获得片刻的安宁与遮蔽,在这大时代能过小日子。梳理一年的书单,旧习未改,加之新书太贵,所购之书多为几年前出版的旧书,新书也有几册,多是心仪许久的佳品。顺着月份,一月一书,虽非当月读毕,亦有一种心境在其中。
一月:那时风雅
《范用存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〇年)四卷本,厚实而充满艺术气息。从上一年读到二〇二二年。
范用一生不离出版,其成就也在出版,可谓出版界的传奇人物。而更为传奇的是,他保存了二千多封作者、朋友的来信,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李公朴、黄洛峰等的信,一直到本世纪初黄裳、董桥的信。而且不是一般的保存,是像整理档案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的十六开牛皮纸本上,连信封也保存完好,整整五十六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张没用过的邮票,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
翻看每卷所附的信件内件的图片,或毛笔、或钢笔,这些斑驳却充满深情的字迹,读之仿若欣赏一件件艺术品。“相交无他事,唯有书与文”,这部书信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集,它是一个时代出版史的记录,是作者和写信人共同演绎的书信雅集,过去很少,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二月:照我思索
二〇二二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计划在五六月份去趟湘西。过年闲暇,将《沈从文别集》(重庆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翻出来读几册,提前做点功课。
沈从文的人生看似简单,前半段为文艺,后半段为文物。然而就连张兆和都说不太能懂他。在其死后,其妻妹张允和撰写的“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一联,却是十分恰当的评价。许是思考方式、人生经历的差异,读懂他不易。但他也提供了一条路径,如他墓碑正面的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三月:飘然独立
在安徽博物院观“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见徐诗荃赠予先生的木刻作品《罐梨》。想了一会儿,想起此人即是有“现代玄奘”之称的徐梵澄,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多次出现。
孙波以“一种充满敬意、情感和责任心的投入”写就《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纪念徐梵澄诞辰一百周年。十年后,又有了崇文书局的修订版。上世纪二十年代,徐梵澄也是鲁迅身边的一翩翩美少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亦多有交往。抗战胜利后,去国研究,这一去就是飘然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底,徐梵澄回祖国。经好友冯至介绍入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晚年,他多着白衣长衫,有几分陈寅恪之神。
四月:两页一生
《讣告》(新星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是《经济学人》“讣告”专栏文章的首次结集。翻译成中文,在大三十二开的页面上,配一张图片,正好两页的篇幅,《读库》主编张立宪称之为“两页一生”。从戴安娜王妃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从导演黑泽明到作家索尔·贝娄,从非洲大独裁者到花园里的跳蚤专家,这其中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也有被遗忘的小角色,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鹉,因为作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值得倾听的故事”。
五月:大道低回
在旧书摊上淘得一册《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作者孙晓玲是孙犁先生的小女儿,十几篇文章从友朋、家人等角度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孙犁,“布衣”应该是个比较准确的评价。铁凝认为,“对父亲和作家,双重的观察带着心跳、带着体温、带着呼吸,是旁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的视角。”
读《开卷》二〇二二年第十一期“开卷闲话”,方知二〇二二年是孙犁逝世二十周年。对他这样的“大隐”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在文字中怀想。孙晓玲曾在邮电系统工作过二十多年,算是我的前辈了,这也是一种缘分。
六月:枝条载荣
日子不紧不慢,万物应时而生长。进入六月,天地间都繁荣起来。陶渊明有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时节,正宜北窗读书。在微博上见《杨葵自选集》(作家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出版,便从网上下单。这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几本新书。
杨葵的《百家姓》《东榔头》《西棒槌》等书都有购读,喜欢他干净、洗练的文字,常将之作为写作范文。三卷本自选集,四十万字,占据杨葵三十多年写作生涯的五分之一。每册三百多页,厚而不沉,既能平摊翻阅,也可一手卷握。版心小巧,天头地脚皆疏朗。书做得很精美,是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
书名从陶渊明的《停云》四章中而来,静寄东轩、愿言怀人、枝条载荣,分别对应了读书写字、念友思朋、日常生活。“撤远一步回望三十多年写过的文章,给自己做了个总结——内容不过三件事: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来写去,想说的其实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写的三件事和说的三件事,都是芸芸众生每日所要面对的。在疫情的当下,我们更应学会面对生活。《停云》是一首思亲友的诗作,用这三句做书名,颇有对往昔的追怀不舍之情。
七月:心安何处
人除了身体需要安顿外,内心也要有所寄。作为自然之子,不得与自然亲近,易生焦躁。暑热之际,翻读《此心安处:扬之水子聪合写小品》,在扬之水的簪花小楷和子聪的山水小品中,品味文人情趣、自然情怀,虽不能至,心有所安定。
二十四开方形本,二十二件小品,笺笺一册。或为扬之水写好扇面,子聪作“命题画”;或为子聪画好扇面,扬之水小楷“题跋”,如此来回,有旧文人之雅。二人都是编辑出身,著作也不少,说是文人不为过。这次抛却本行,玩起文人画了。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细品这些画,细赏这些字,学问、才情、思想兼具,有些还意到笔不到,慢慢琢磨,挺好玩的。至于人品,他们与文化老人的交往,就可见一斑。二人皆属马,都是安静的马。静能生慧,慧能生定,人不再如飘蓬。
八月:精神丰碑
平常读小说不多,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是慕名购买的。一气读完,既满足了对这位先锋小说家“红色叙事”的期待,也了却自己的一个遗憾。二〇二一年五月底,原计划去广东汕头、福建龙岩等地采访中央红色交通线,因疫情未能成行。《千里江山图》写的就是这条从上海绕道香港经广东等地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已过花甲的孙甘露用数十年的时间、近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写下了十来个人的青春之华,他们是爱人,是兄弟,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乱世行走江山。“千里江山图”是行动计划,是接头暗号,是革命希望。“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是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小说里数次出现,表明了他们的人生态度。
九月:旧时文人
《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二〇二二年)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是新书,也可说是旧作。
这本回想录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止庵先生认为,此书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知堂回想录》。
十月:报人论政
《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从作者现存的日记中选取了一九四七、四九、五一、五七、五八、六五、六六年的片段。
十一月:谁的历史
读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二二年)。
在权力世界里,两书的主人公王钟儿和喜所能拥有的选择也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当我们在说历史的时候,是在说谁的历史呢?千千万万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最终却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是时代之悲、是历史之痛?
十二月:霜红晚晴
一年灯火要人归。读书到此,也停下歇歇、回望。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二年)是毛边本,就着窗外霜红、冬日暖阳,慢裁慢读。书为两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合为第一集,《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和《译文附录》合为第二集。
《读书随笔》曾于一九八八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初版,此次合为两册,编排得有些密匝。叶灵凤爱读书且爱读杂书,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他都爱读。《读书随笔》堪比读书的“随园食单”,看看他写的那些人那些书就知道了。他深爱着他们,津津乐道于书人书话、版本源流。许多是为副刊而写,这些小品文篇幅都不长,千余字居多,随性而谈,随意而止,文雅闲适,气定神闲。
终其一生,叶灵凤过着相对比较纯粹的书斋生活,读书,写稿,编报纸副刊,一辈子耽溺于书海,自诩“爱书家”之本色。这也是旧时文人的风雅、追求。
野水千年在,闲花一夕空。书读过,插入书架,其回想还在。我将这些书作为个人生活的调解器、自我认识的推进器。从年头到年尾,读之不辍。想起川端康成在五十岁时,写的一段话,“近来,我养成了把人放在他生涯中看,把今天放在历史中看的心性。”读书论人,当效之。
壬寅年去,癸卯兔来。时光、节律兀自往前走,不受人和时代的左右。匆匆回望,于小我而言,是恓惶、焦虑的一年。
中年滋味,共谁商略。幸而还有书,营造了一个小小的“避难所”,获得片刻的安宁与遮蔽,在这大时代能过小日子。梳理一年的书单,旧习未改,加之新书太贵,所购之书多为几年前出版的旧书,新书也有几册,多是心仪许久的佳品。顺着月份,一月一书,虽非当月读毕,亦有一种心境在其中。
一月:那时风雅
《范用存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〇年)四卷本,厚实而充满艺术气息。从上一年读到二〇二二年。
范用一生不离出版,其成就也在出版,可谓出版界的传奇人物。而更为传奇的是,他保存了二千多封作者、朋友的来信,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李公朴、黄洛峰等的信,一直到本世纪初黄裳、董桥的信。而且不是一般的保存,是像整理档案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的十六开牛皮纸本上,连信封也保存完好,整整五十六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张没用过的邮票,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
翻看每卷所附的信件内件的图片,或毛笔、或钢笔,这些斑驳却充满深情的字迹,读之仿若欣赏一件件艺术品。“相交无他事,唯有书与文”,这部书信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集,它是一个时代出版史的记录,是作者和写信人共同演绎的书信雅集,过去很少,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二月:照我思索
二〇二二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计划在五六月份去趟湘西。过年闲暇,将《沈从文别集》(重庆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翻出来读几册,提前做点功课。
沈从文的人生看似简单,前半段为文艺,后半段为文物。然而就连张兆和都说不太能懂他。在其死后,其妻妹张允和撰写的“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一联,却是十分恰当的评价。许是思考方式、人生经历的差异,读懂他不易。但他也提供了一条路径,如他墓碑正面的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三月:飘然独立
在安徽博物院观“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见徐诗荃赠予先生的木刻作品《罐梨》。想了一会儿,想起此人即是有“现代玄奘”之称的徐梵澄,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多次出现。
孙波以“一种充满敬意、情感和责任心的投入”写就《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纪念徐梵澄诞辰一百周年。十年后,又有了崇文书局的修订版。上世纪二十年代,徐梵澄也是鲁迅身边的一翩翩美少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亦多有交往。抗战胜利后,去国研究,这一去就是飘然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底,徐梵澄回祖国。经好友冯至介绍入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晚年,他多着白衣长衫,有几分陈寅恪之神。
四月:两页一生
《讣告》(新星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是《经济学人》“讣告”专栏文章的首次结集。翻译成中文,在大三十二开的页面上,配一张图片,正好两页的篇幅,《读库》主编张立宪称之为“两页一生”。从戴安娜王妃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从导演黑泽明到作家索尔·贝娄,从非洲大独裁者到花园里的跳蚤专家,这其中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也有被遗忘的小角色,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鹉,因为作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值得倾听的故事”。
五月:大道低回
在旧书摊上淘得一册《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作者孙晓玲是孙犁先生的小女儿,十几篇文章从友朋、家人等角度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孙犁,“布衣”应该是个比较准确的评价。铁凝认为,“对父亲和作家,双重的观察带着心跳、带着体温、带着呼吸,是旁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的视角。”
读《开卷》二〇二二年第十一期“开卷闲话”,方知二〇二二年是孙犁逝世二十周年。对他这样的“大隐”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在文字中怀想。孙晓玲曾在邮电系统工作过二十多年,算是我的前辈了,这也是一种缘分。
六月:枝条载荣
日子不紧不慢,万物应时而生长。进入六月,天地间都繁荣起来。陶渊明有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时节,正宜北窗读书。在微博上见《杨葵自选集》(作家出版社,二〇二二年)出版,便从网上下单。这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几本新书。
杨葵的《百家姓》《东榔头》《西棒槌》等书都有购读,喜欢他干净、洗练的文字,常将之作为写作范文。三卷本自选集,四十万字,占据杨葵三十多年写作生涯的五分之一。每册三百多页,厚而不沉,既能平摊翻阅,也可一手卷握。版心小巧,天头地脚皆疏朗。书做得很精美,是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
书名从陶渊明的《停云》四章中而来,静寄东轩、愿言怀人、枝条载荣,分别对应了读书写字、念友思朋、日常生活。“撤远一步回望三十多年写过的文章,给自己做了个总结——内容不过三件事: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来写去,想说的其实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写的三件事和说的三件事,都是芸芸众生每日所要面对的。在疫情的当下,我们更应学会面对生活。《停云》是一首思亲友的诗作,用这三句做书名,颇有对往昔的追怀不舍之情。
七月:心安何处
人除了身体需要安顿外,内心也要有所寄。作为自然之子,不得与自然亲近,易生焦躁。暑热之际,翻读《此心安处:扬之水子聪合写小品》,在扬之水的簪花小楷和子聪的山水小品中,品味文人情趣、自然情怀,虽不能至,心有所安定。
二十四开方形本,二十二件小品,笺笺一册。或为扬之水写好扇面,子聪作“命题画”;或为子聪画好扇面,扬之水小楷“题跋”,如此来回,有旧文人之雅。二人都是编辑出身,著作也不少,说是文人不为过。这次抛却本行,玩起文人画了。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细品这些画,细赏这些字,学问、才情、思想兼具,有些还意到笔不到,慢慢琢磨,挺好玩的。至于人品,他们与文化老人的交往,就可见一斑。二人皆属马,都是安静的马。静能生慧,慧能生定,人不再如飘蓬。
八月:精神丰碑
平常读小说不多,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二年)是慕名购买的。一气读完,既满足了对这位先锋小说家“红色叙事”的期待,也了却自己的一个遗憾。二〇二一年五月底,原计划去广东汕头、福建龙岩等地采访中央红色交通线,因疫情未能成行。《千里江山图》写的就是这条从上海绕道香港经广东等地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已过花甲的孙甘露用数十年的时间、近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写下了十来个人的青春之华,他们是爱人,是兄弟,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乱世行走江山。“千里江山图”是行动计划,是接头暗号,是革命希望。“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是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小说里数次出现,表明了他们的人生态度。
九月:旧时文人
《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二〇二二年)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是新书,也可说是旧作。
这本回想录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止庵先生认为,此书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知堂回想录》。
十月:报人论政
《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从作者现存的日记中选取了一九四七、四九、五一、五七、五八、六五、六六年的片段。
十一月:谁的历史
读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二〇二二年)。
在权力世界里,两书的主人公王钟儿和喜所能拥有的选择也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当我们在说历史的时候,是在说谁的历史呢?千千万万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最终却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是时代之悲、是历史之痛?
十二月:霜红晚晴
一年灯火要人归。读书到此,也停下歇歇、回望。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二年)是毛边本,就着窗外霜红、冬日暖阳,慢裁慢读。书为两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合为第一集,《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和《译文附录》合为第二集。
《读书随笔》曾于一九八八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初版,此次合为两册,编排得有些密匝。叶灵凤爱读书且爱读杂书,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他都爱读。《读书随笔》堪比读书的“随园食单”,看看他写的那些人那些书就知道了。他深爱着他们,津津乐道于书人书话、版本源流。许多是为副刊而写,这些小品文篇幅都不长,千余字居多,随性而谈,随意而止,文雅闲适,气定神闲。
终其一生,叶灵凤过着相对比较纯粹的书斋生活,读书,写稿,编报纸副刊,一辈子耽溺于书海,自诩“爱书家”之本色。这也是旧时文人的风雅、追求。
野水千年在,闲花一夕空。书读过,插入书架,其回想还在。我将这些书作为个人生活的调解器、自我认识的推进器。从年头到年尾,读之不辍。想起川端康成在五十岁时,写的一段话,“近来,我养成了把人放在他生涯中看,把今天放在历史中看的心性。”读书论人,当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