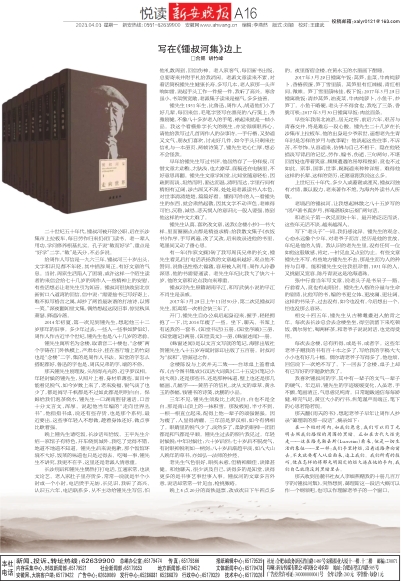发布日期:
写在《锺叔河集》边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锺叔河被开除公职,后在长沙集市上拉板车,每日劳作归来仍闭门读书。老一辈人用功,学问修养根基扎实。孔子说“敏而好学”,重点是“好学”二字,“敏”是天分,不必多说。
给周作人写信是一九六三年,锺叔河三十岁出头,文字和识见都不年轻,其中措辞周正,有好文章的气息。当时,周家生活陷入了困境,或许这样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会给七十几岁的周作人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有些话想必让老先生引为知音。锺叔河很快收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的回信,信中说:“需要拙书已写好寄上,唯不拟写格言之属,却抄了两首最诙谐的打油诗,以博一笑。”深夜翻知堂文集,偶然想起这段旧事,惊觉秋风萧瑟,驿道冷落。
2014年初夏,第一次见到锺先生,想起他三十二岁那年的旧事。多少年过去,一些人一些事如梦似幻,周作人作古近半个世纪,锺先生也是八十几岁的老翁。
锺先生寓所名为念楼,取谐音二十楼也。“念楼”两个字铸在门外铁模上,严肃本分,挂在客厅墙上的竹刻也是“念楼”二字,集的是周作人书法。知堂的字怎么搭配都好,鲁迅的字也是,周氏兄弟的字,端的不俗。
那天锺先生刚理发,头刮得光光的,近乎罗汉相。年轻时候的锺先生,从照片上看,身材单薄些,面目中能看见锐气,如今岁数上来了,老来发福,锐气淡了也少了,都是阅尽千帆都是不过如此都是明明白白。保姆给我们泡茶烧水,锺先生一口湖南腔普通话,口音十分文言文,浑厚。说起他当年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指指书桌,说还有些存货,也是那个系列,最近要出,这些事年轻人不想做,趁着身体还好,做点事比歇着强。
晚上锺先生请吃饭,长沙话叫恰饭。王平先生介绍一家馆子有特色,开车绕到城外,我吃了觉得不错,地道不地道不知道。锺先生后来说抱歉,那个饭馆环境不大好,饭菜的味道也只是过得去。吃喝一事,锺先生不讲究,我更不在乎,这里还是老派人情意重。
长沙别后和锺先生偶然打打电话,互通家常,也谈文论艺。老人家肚子里存货多,常常一说就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电话烫手无妨,长见识,我听了高兴。认识五六年,电话联系多,从不主动给锺先生写信,怕他礼数周到,回信伤神。老人家客气,每回新书出版,总要寄来并附手札给我消闲。老派文章读来不累,对着话筒祝锺先生健康长寿,多写几本,老人家那一头声响如雷,说起手头工作一件接一件,我听了高兴。寒舍虽小,书架倒宽敞,老派集子读来是福气,多多益善。
锺先生1931年生,比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小了好几辈,每回来信,毛笔字竖写在漂亮的八行笺上,秀雅刚健,不像八十多岁老人的手笔,裱起来就是一帧小品。我这个看横排字长大的晚生,亦觉得顺眼养心。请他给我写过几首周作人的杂事诗,一手行楷,又劲道又文气,朋友们喜欢,讨走好几件,如今手头只剩来往信札与一本册页、两帧诗笺了,锺先生宅心仁厚,想必不会怪我。
早年给锺先生写过书评,他居然存了一份样报,可惜文章太幼稚、太肤浅,也太潦草,底稿还在电脑里,不好意思再翻。锺先生文章学知堂,比知堂随意轻松,因疏朗而淡、坦然而明、豁达而温、清明而达,字里行间有精细有辽阔,涉古深又不深,处处是老派读书人本色,对世事清清楚楚,篇篇好看。懂得写作的人一看锺先生的东西,就会肃然起敬,因其文字不动声色,老辣得可怕、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的意识比一般人要强,练到他这样的中文太难了。
锺先生认真,喜欢改文章,送我《念楼小抄》一书大样,里面圈圈点点都是精益求精;给我散文集子《衣饭书》作序,手写两遍,改了又改,后来收录进他的书里,笔墨间又动了番心思。
有一年《作家文摘》转了我写周氏兄弟的长文,锺先生看见后打电话表扬我的文章越来越好,观点他不赞同,说鲁迅性格太偏激,容易被人利用;周作人冷静深思,他的书需要通读。老先生年纪比我大了快六十岁,他的文章和论点我向来尊重。
锺叔河先生原籍湖南平江,和写武侠小说的平江不肖生是亲戚。
2017年3月29日上午11时50分,第二次见锺叔河先生,距离第一次相会快三年了。
开门,锺先生自办公桌后起身迎来,握手,轻轻拥抱了一下,比2014年瘦了一些。坐下,聊天。书案上有送我的一套书,《知堂书话》五册,《知堂序跋》三册,《知堂题记》两册,《知堂美文》一册,《蛛窗述闻》一册。
《蛛窗述闻》是以文言文写就的笔记,海豚出版社贺锺先生八十五岁寿诞时影印出版了五百册。时叔河为“叔和”,皆弱冠之作。
念楼陈设与上次并无二致——台球桌上盖着桌布,《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大词典》《二十五史》《笔记小说大观》,还是那些书,还是那种味道,壁上也还是那几幅画、几幅字——黄苗子的信札,沈从文的章草,黄永玉的条幅,钱锺书的诗笺,沈鹏的小品。
三年不见,锺先生须发比上次见白,白也不是全白,那是南山顶上的一抹积雪。那发极短,半寸不到,一根一根直立起来,配得上他一辈子的顽强倔强。因为瘦了,人显得清癯。三年前是罗汉相,如今有佛相了。眼睛里的锐气少了、淡然多了,柔软的眼神一团团都是和气都是平顺。锺先生过去的照片我见过。年轻时候锐;中年时候壮;六十岁后烈;七十岁后不脱虎气,有时眼神锐利如一柄剑;八十岁后渐趋平淡,如八大山人晚年的草书,亦如弘一法师的抄经。
老先生气色很好,眼疾未愈,但精神颇佳,谈锋甚健。和他聊天,很少谈及自己,谈得多的是知堂,谈得更多的是书事艺事世事人事。锺叔河的文章多言外意,说话却常常一针见血,枪挑脓疮。
晚上6点20分的高铁退票,改成次日下午四点多的。夜里留宿念楼,在黄永玉的水墨画下酣睡。
2017年3月29日锺寓午饭:莴笋,韭菜,牛肉炖萝卜,香椿煎蛋,笋丁雪里蕻。莴笋里有红辣椒,青红相间,微辣。笋丁雪里蕻味佳,极下饭;2017年3月29日锺寓晚饭:清炒莴笋,油麦菜,牛肉炖萝卜,小鱼干,炒笋丁。小鱼干略硬,老头子不得食也,我吃了三条,香脆可啖;2017年3月30日锺寓早饭:肉丝面条。
早些年我南北流浪,居无定所,前后六年,艰苦与青春交并,终是难忘一段心酸。锺先生二十几岁在长沙集市上拉板车,他的出身是少爷家世,遥想老先生青年时是怎样的岁月与故事呢?他谈起这些往事,不诉苦、不夸饰,从容道来,仿佛与自己不相干。隐在他轻描淡写背后的记忆、劳作、编书、伤逝,三句两句,不堪回首处也带着笑意,频频遭遇的屈辱和挫折,竟也不过如此。家事、国事、世事,娓娓道来种种详细。难得他这样的长辈、这样的资历,还愿意跟我说这么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多少人或萎谢或湮灭,锺叔河独有才情,兼以毅力,老来著作不绝,为海内外读书人所敬。
老境后的锺叔河,让我想起林散之八十五岁写的“闭户著书真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两句话。
和老头子第一次见面快十年。最开始泛泛而谈,这些年无话不谈,越来越深入。
写下“老头子”一词,我仍感诧异。锺先生的观念、心态永远像个少年,对老爷子而言,经历是他的世故,年纪是他的人情。我认识的老先生里,没有任何一位如他这般敏感、肯定,一针见血又点到为止。有些文章锺先生不写,有些地方锺先生不去,那是生而为人的矜持与自尊。能和锺先生交往我很珍惜,1931年的人,又挑剔又宽容,陈丹青说这是沧海遗珠。
张中行翁当年写文章,说老头子是书呆子一路。行翁看人,竟也有走眼时。锺先生人格的分量与生命的剧情,比他写的书、编的书更立体、更波澜、更壮阔。这样的书呆子,过去没有,如今也没有,今后想出一个,怕也没那么容易。
相交十四五年,锺先生从古稀耄耋进入鲐背之年。每次去长沙总会去念楼坐坐,得空就留下来吃顿饭,偶尔匆忙,喝两杯茶,和老爷子说说闲话,也觉得受用。
每次去念楼,总有所得,或是书,或者字。这些年老爷子赠我的书有百十本之多了,写给我的字稿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十幅。偶尔请老爷子写得多了,他也烦,回信说下一次绝不写了。下一回去了念楼,桌子上却有已写好的字题款给我了。
我喜欢锺叔河的字,其中有一辈子的文气一辈子的硬气。年迈后,锺先生的字迹缓缓变化,人虽老,手不颤,笔画清正,气息愈见纯青。日常题跋通信每每矫健,神完气足,黄豆大小的行书,纵笔谨严而端正,笔下的心思若隐若现。
那天翻《雨天的书》,想起老爷子早年让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那一段话”,摘录如下: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Lue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那天收到岳麓书社友人李缅燕赠我的十册几百万字的《锺叔河集》,突然想到,蔼理斯这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一个纲领吧,也可以作理解老爷子的一个窗口。
给周作人写信是一九六三年,锺叔河三十岁出头,文字和识见都不年轻,其中措辞周正,有好文章的气息。当时,周家生活陷入了困境,或许这样一个陌生读者的来信会给七十几岁的周作人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有些话想必让老先生引为知音。锺叔河很快收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的回信,信中说:“需要拙书已写好寄上,唯不拟写格言之属,却抄了两首最诙谐的打油诗,以博一笑。”深夜翻知堂文集,偶然想起这段旧事,惊觉秋风萧瑟,驿道冷落。
2014年初夏,第一次见到锺先生,想起他三十二岁那年的旧事。多少年过去,一些人一些事如梦似幻,周作人作古近半个世纪,锺先生也是八十几岁的老翁。
锺先生寓所名为念楼,取谐音二十楼也。“念楼”两个字铸在门外铁模上,严肃本分,挂在客厅墙上的竹刻也是“念楼”二字,集的是周作人书法。知堂的字怎么搭配都好,鲁迅的字也是,周氏兄弟的字,端的不俗。
那天锺先生刚理发,头刮得光光的,近乎罗汉相。年轻时候的锺先生,从照片上看,身材单薄些,面目中能看见锐气,如今岁数上来了,老来发福,锐气淡了也少了,都是阅尽千帆都是不过如此都是明明白白。保姆给我们泡茶烧水,锺先生一口湖南腔普通话,口音十分文言文,浑厚。说起他当年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他指指书桌,说还有些存货,也是那个系列,最近要出,这些事年轻人不想做,趁着身体还好,做点事比歇着强。
晚上锺先生请吃饭,长沙话叫恰饭。王平先生介绍一家馆子有特色,开车绕到城外,我吃了觉得不错,地道不地道不知道。锺先生后来说抱歉,那个饭馆环境不大好,饭菜的味道也只是过得去。吃喝一事,锺先生不讲究,我更不在乎,这里还是老派人情意重。
长沙别后和锺先生偶然打打电话,互通家常,也谈文论艺。老人家肚子里存货多,常常一说就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电话烫手无妨,长见识,我听了高兴。认识五六年,电话联系多,从不主动给锺先生写信,怕他礼数周到,回信伤神。老人家客气,每回新书出版,总要寄来并附手札给我消闲。老派文章读来不累,对着话筒祝锺先生健康长寿,多写几本,老人家那一头声响如雷,说起手头工作一件接一件,我听了高兴。寒舍虽小,书架倒宽敞,老派集子读来是福气,多多益善。
锺先生1931年生,比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小了好几辈,每回来信,毛笔字竖写在漂亮的八行笺上,秀雅刚健,不像八十多岁老人的手笔,裱起来就是一帧小品。我这个看横排字长大的晚生,亦觉得顺眼养心。请他给我写过几首周作人的杂事诗,一手行楷,又劲道又文气,朋友们喜欢,讨走好几件,如今手头只剩来往信札与一本册页、两帧诗笺了,锺先生宅心仁厚,想必不会怪我。
早年给锺先生写过书评,他居然存了一份样报,可惜文章太幼稚、太肤浅,也太潦草,底稿还在电脑里,不好意思再翻。锺先生文章学知堂,比知堂随意轻松,因疏朗而淡、坦然而明、豁达而温、清明而达,字里行间有精细有辽阔,涉古深又不深,处处是老派读书人本色,对世事清清楚楚,篇篇好看。懂得写作的人一看锺先生的东西,就会肃然起敬,因其文字不动声色,老辣得可怕、沉稳、诚恳,悲天悯人的意识比一般人要强,练到他这样的中文太难了。
锺先生认真,喜欢改文章,送我《念楼小抄》一书大样,里面圈圈点点都是精益求精;给我散文集子《衣饭书》作序,手写两遍,改了又改,后来收录进他的书里,笔墨间又动了番心思。
有一年《作家文摘》转了我写周氏兄弟的长文,锺先生看见后打电话表扬我的文章越来越好,观点他不赞同,说鲁迅性格太偏激,容易被人利用;周作人冷静深思,他的书需要通读。老先生年纪比我大了快六十岁,他的文章和论点我向来尊重。
锺叔河先生原籍湖南平江,和写武侠小说的平江不肖生是亲戚。
2017年3月29日上午11时50分,第二次见锺叔河先生,距离第一次相会快三年了。
开门,锺先生自办公桌后起身迎来,握手,轻轻拥抱了一下,比2014年瘦了一些。坐下,聊天。书案上有送我的一套书,《知堂书话》五册,《知堂序跋》三册,《知堂题记》两册,《知堂美文》一册,《蛛窗述闻》一册。
《蛛窗述闻》是以文言文写就的笔记,海豚出版社贺锺先生八十五岁寿诞时影印出版了五百册。时叔河为“叔和”,皆弱冠之作。
念楼陈设与上次并无二致——台球桌上盖着桌布,《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大词典》《二十五史》《笔记小说大观》,还是那些书,还是那种味道,壁上也还是那几幅画、几幅字——黄苗子的信札,沈从文的章草,黄永玉的条幅,钱锺书的诗笺,沈鹏的小品。
三年不见,锺先生须发比上次见白,白也不是全白,那是南山顶上的一抹积雪。那发极短,半寸不到,一根一根直立起来,配得上他一辈子的顽强倔强。因为瘦了,人显得清癯。三年前是罗汉相,如今有佛相了。眼睛里的锐气少了、淡然多了,柔软的眼神一团团都是和气都是平顺。锺先生过去的照片我见过。年轻时候锐;中年时候壮;六十岁后烈;七十岁后不脱虎气,有时眼神锐利如一柄剑;八十岁后渐趋平淡,如八大山人晚年的草书,亦如弘一法师的抄经。
老先生气色很好,眼疾未愈,但精神颇佳,谈锋甚健。和他聊天,很少谈及自己,谈得多的是知堂,谈得更多的是书事艺事世事人事。锺叔河的文章多言外意,说话却常常一针见血,枪挑脓疮。
晚上6点20分的高铁退票,改成次日下午四点多的。夜里留宿念楼,在黄永玉的水墨画下酣睡。
2017年3月29日锺寓午饭:莴笋,韭菜,牛肉炖萝卜,香椿煎蛋,笋丁雪里蕻。莴笋里有红辣椒,青红相间,微辣。笋丁雪里蕻味佳,极下饭;2017年3月29日锺寓晚饭:清炒莴笋,油麦菜,牛肉炖萝卜,小鱼干,炒笋丁。小鱼干略硬,老头子不得食也,我吃了三条,香脆可啖;2017年3月30日锺寓早饭:肉丝面条。
早些年我南北流浪,居无定所,前后六年,艰苦与青春交并,终是难忘一段心酸。锺先生二十几岁在长沙集市上拉板车,他的出身是少爷家世,遥想老先生青年时是怎样的岁月与故事呢?他谈起这些往事,不诉苦、不夸饰,从容道来,仿佛与自己不相干。隐在他轻描淡写背后的记忆、劳作、编书、伤逝,三句两句,不堪回首处也带着笑意,频频遭遇的屈辱和挫折,竟也不过如此。家事、国事、世事,娓娓道来种种详细。难得他这样的长辈、这样的资历,还愿意跟我说这么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多少人或萎谢或湮灭,锺叔河独有才情,兼以毅力,老来著作不绝,为海内外读书人所敬。
老境后的锺叔河,让我想起林散之八十五岁写的“闭户著书真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两句话。
和老头子第一次见面快十年。最开始泛泛而谈,这些年无话不谈,越来越深入。
写下“老头子”一词,我仍感诧异。锺先生的观念、心态永远像个少年,对老爷子而言,经历是他的世故,年纪是他的人情。我认识的老先生里,没有任何一位如他这般敏感、肯定,一针见血又点到为止。有些文章锺先生不写,有些地方锺先生不去,那是生而为人的矜持与自尊。能和锺先生交往我很珍惜,1931年的人,又挑剔又宽容,陈丹青说这是沧海遗珠。
张中行翁当年写文章,说老头子是书呆子一路。行翁看人,竟也有走眼时。锺先生人格的分量与生命的剧情,比他写的书、编的书更立体、更波澜、更壮阔。这样的书呆子,过去没有,如今也没有,今后想出一个,怕也没那么容易。
相交十四五年,锺先生从古稀耄耋进入鲐背之年。每次去长沙总会去念楼坐坐,得空就留下来吃顿饭,偶尔匆忙,喝两杯茶,和老爷子说说闲话,也觉得受用。
每次去念楼,总有所得,或是书,或者字。这些年老爷子赠我的书有百十本之多了,写给我的字稿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十幅。偶尔请老爷子写得多了,他也烦,回信说下一次绝不写了。下一回去了念楼,桌子上却有已写好的字题款给我了。
我喜欢锺叔河的字,其中有一辈子的文气一辈子的硬气。年迈后,锺先生的字迹缓缓变化,人虽老,手不颤,笔画清正,气息愈见纯青。日常题跋通信每每矫健,神完气足,黄豆大小的行书,纵笔谨严而端正,笔下的心思若隐若现。
那天翻《雨天的书》,想起老爷子早年让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那一段话”,摘录如下: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Lue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那天收到岳麓书社友人李缅燕赠我的十册几百万字的《锺叔河集》,突然想到,蔼理斯这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一个纲领吧,也可以作理解老爷子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