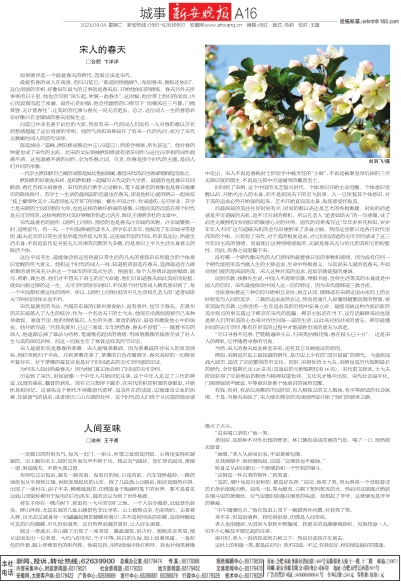发布日期:
宋人的春天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爱春天的朝代,答案应该是宋代。
最爱伤春的词人在南唐,名叫冯延巳。“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这位南唐的宰相,好像每年最大的正事就是春来后,开始他依旧的惆怅。春天另外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也会写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时候,他会带上怨妇的面具,内心因寂寞而起了波澜。最伤心的时候,他会用幽怨的口吻写下“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让美好的红颜与春光一同无奈逝去。总之,这位词人一生的喜怒哀乐好像只在金陵城的春天里发生过。
冯延巳并非名著于后世的大家,然而有宋一代的词人们没有一人对春的难以言状的愁绪超越了这位南唐的宰相。他的气质和风神却开了有宋一代的先河,成为了宋代无数婉约词人的前代导师。
陈延焯说:“晏殊、欧阳修词雅近中正(冯延巳),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他对春的钟爱也成了宋代的主流。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有诸多词作与这位冯宰相的词作混淆不清。这些混淆不清的词作,全为伤春之词。可见,伤春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是词人们共同的形象。
一代宗主欧阳修自己做的词都是如此艳丽深婉,难怪宋代的后生晚辈要群起而效之。
欧阳修的好朋友宋祁,是和欧阳修一起编写五代史的大学者。最爱的也是春日花间醉酒,看红杏枝头闹春意。宋代的流行歌手之冠柳永,笔下最著名的意象也是春日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苏学士一生谈的最深刻的恋爱也在春天,那是他和心爱的朝云一起咏叹“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时候。柳永平民之作,作词感伤,无可厚非。苏学士是宋朝的士民仰望的大师,也是这样的秾纤娇弱的感慨,只能说美的泛滥在那个时代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纯粹的对美好事物的伤逝之语言,鲜见于唐朝李杜的文章中。
宋代最著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也是春天汴京城的风物。汴京城繁极一时,冠绝前代。有一天,一个叫张择端的读书人,游学东京多年,他发现了东京城寻常巷陌、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里所蕴含的惊人的美,这座城市里的市民,有审美品位,热爱生活本身,不再是前代史书里无人问津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意识上平凡生活本身意义的鲜活个体。
这位平民书生,最能体会到这些热爱日常生活的凡夫的喜怒哀乐所蕴含的个体意识觉醒的伟大意义。他和这个时代的词人一样,知道把背景选在春天,选择最适合人群相聚的清明来充分表达一个城市的审美式生活。图画里,每个人热情洋溢地喝酒、骑马、唱歌、做生意,他们才不管天下君王的宏大命题,他们只知道春天如此美好而短暂,就如白驹过隙的这一生。无可奈何的时间意识,不仅那个时代的词人精英意识到了,每一个平民都有着这样的情怀。所以,《清明上河图》里的平凡生活和孔圣人的“逝者如斯夫”的咏叹同样永垂不朽。
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当属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没有意外,也写于春天。在黄州的苏东坡落入了人生的低谷,作为一个名动天下的士大夫,他现在沦落到需要自己来种菜做饭。寒食节里,他的情绪低沉,人生的失意,寒食的清冷,最容易激发他心中的块垒。他开始写道:“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随着书写的深入,他逐渐忘掉了章法与结构,笔端唯有起伏的情绪,用深情雅致的线条完成了对人生与美的深切哀悼。而这一切发生在了寒食这样美的节日里。
宋人最爱的花是暮春的荼蘼。宋人爱喝荼蘼酒。因为荼蘼最符合宋人的审美情味,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的白色花瓣落尽,春天美好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对于荼蘼的爱其实也是对于时间逝去的无可奈何感的印证。
为何宋人如此热爱春天?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了时间的无可奈何。
历史到了宋代,时间就像一个中年人开始回忆往事,这个中年人见过了三代的神迹,汉唐的盛况,魏晋的衰乱。现在它只想停下脚步,在宋代的积贫积弱的身躯里,开始休息和回忆。这意味这个朝代不再像唐代那样,追求外在的成就,边塞建功立业的执着,任侠使气的快乐,或者游历三山五湖的壮怀。这个时代的人们终于从沉重的使命感中走出。宋人不再是春秋时士阶层手中被烹饪的“小鲜”,不再是被秦皇帝坑掉的三百无辨识度的儒生,不再是压抑中穷途痛哭的魏晋名士。
时间到了宋朝,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个体意识开始主动觉醒。个体意识觉醒以后,开始关注人的本身,而不是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人一旦恢复其个体意识,对于美的追求必然开始强烈起来。艺术开始直面美本身,发现感受抒发美。
而最深刻的美往往同时间有关,时间的难以表达是艺术的终极难题。时间的消逝感是不可道破的天机,是不可言说的禅机。所以孔圣人“逝者如斯夫”的一句感慨,成了后世无数拥有时间意识的敏感心灵的共鸣。唐代的刘希夷写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句道破天机的金句后便招来了杀身之祸。然而这些都只是各自时代里孤单的个体。只有到了宋代,对于美的极度追求,才让时间消逝的无可奈何感成了这三百年间主流的情绪。而最能让这种情绪感发的,无疑是春天无与伦比的美和它的短暂性。因此,伤春之词滥觞于宋。
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的人们那样热爱着春日里的事物和感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把审美当做人生的主要追求、生命中终极意义。与其说宋人爱的是春天,不如说他们爱的是深刻的美。宋人这种对美的追求,直如宗教徒般的虔诚。
说到宗教,钱穆先生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琴棋书画,世俗生活等美的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宋代最能体现中国人这一信仰特征。因为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
合流意味着这三种信仰开始相互妥协、相互认同,儒释道在宋朝这里由形而上的玄妙转变为人间的美学。三教的追求虽然玄远,然而普通凡人却懂得删繁就简的智慧,将审美取代宗教,让俗世的一生在追求美的历程中安身立命。最能反映这种合流后新的美学观点的事实莫过于禅宗在宋代的滥觞。禅宗主张活在当下,这句话解释来说也就是要人们用审美的心态来对待世间每一刻的生活,以此来对抗时间的虚无。禅宗最懂时间的无可奈何,唯有在审美的过程中才能战胜世间的虚无与消逝。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是宋人的禅机,它伴随着寻春的启发。
当然,宋人的春天如此神圣多彩,还有其它耳熟能详的原因。
例如,宋朝是历史上最民富的朝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国穷民富”的朝代。大量流民涌入城市,造成了空前繁荣的市文化。同时,宋朝优待士大夫,宋朝也是历代假期最长的朝代,全年假期长达120多天(其身后的元朝假期仅有16天)。宋代重文轻武,士大夫阶层获得了空前绝后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优待。文化天才集中出现。宋代社会扁平化,门阀彻底销声匿迹,平等意识助推个体意识的强烈觉醒。
有钱,有闲,有品位高雅的市民阶层,有人格独立的文人集体,有平等舒适的社会氛围。于是,当春天来临了,宋人便在禅宗的天地境界里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路。
最爱伤春的词人在南唐,名叫冯延巳。“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这位南唐的宰相,好像每年最大的正事就是春来后,开始他依旧的惆怅。春天另外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也会写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时候,他会带上怨妇的面具,内心因寂寞而起了波澜。最伤心的时候,他会用幽怨的口吻写下“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让美好的红颜与春光一同无奈逝去。总之,这位词人一生的喜怒哀乐好像只在金陵城的春天里发生过。
冯延巳并非名著于后世的大家,然而有宋一代的词人们没有一人对春的难以言状的愁绪超越了这位南唐的宰相。他的气质和风神却开了有宋一代的先河,成为了宋代无数婉约词人的前代导师。
陈延焯说:“晏殊、欧阳修词雅近中正(冯延巳),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他对春的钟爱也成了宋代的主流。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有诸多词作与这位冯宰相的词作混淆不清。这些混淆不清的词作,全为伤春之词。可见,伤春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是词人们共同的形象。
一代宗主欧阳修自己做的词都是如此艳丽深婉,难怪宋代的后生晚辈要群起而效之。
欧阳修的好朋友宋祁,是和欧阳修一起编写五代史的大学者。最爱的也是春日花间醉酒,看红杏枝头闹春意。宋代的流行歌手之冠柳永,笔下最著名的意象也是春日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苏学士一生谈的最深刻的恋爱也在春天,那是他和心爱的朝云一起咏叹“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时候。柳永平民之作,作词感伤,无可厚非。苏学士是宋朝的士民仰望的大师,也是这样的秾纤娇弱的感慨,只能说美的泛滥在那个时代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纯粹的对美好事物的伤逝之语言,鲜见于唐朝李杜的文章中。
宋代最著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也是春天汴京城的风物。汴京城繁极一时,冠绝前代。有一天,一个叫张择端的读书人,游学东京多年,他发现了东京城寻常巷陌、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里所蕴含的惊人的美,这座城市里的市民,有审美品位,热爱生活本身,不再是前代史书里无人问津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意识上平凡生活本身意义的鲜活个体。
这位平民书生,最能体会到这些热爱日常生活的凡夫的喜怒哀乐所蕴含的个体意识觉醒的伟大意义。他和这个时代的词人一样,知道把背景选在春天,选择最适合人群相聚的清明来充分表达一个城市的审美式生活。图画里,每个人热情洋溢地喝酒、骑马、唱歌、做生意,他们才不管天下君王的宏大命题,他们只知道春天如此美好而短暂,就如白驹过隙的这一生。无可奈何的时间意识,不仅那个时代的词人精英意识到了,每一个平民都有着这样的情怀。所以,《清明上河图》里的平凡生活和孔圣人的“逝者如斯夫”的咏叹同样永垂不朽。
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当属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没有意外,也写于春天。在黄州的苏东坡落入了人生的低谷,作为一个名动天下的士大夫,他现在沦落到需要自己来种菜做饭。寒食节里,他的情绪低沉,人生的失意,寒食的清冷,最容易激发他心中的块垒。他开始写道:“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随着书写的深入,他逐渐忘掉了章法与结构,笔端唯有起伏的情绪,用深情雅致的线条完成了对人生与美的深切哀悼。而这一切发生在了寒食这样美的节日里。
宋人最爱的花是暮春的荼蘼。宋人爱喝荼蘼酒。因为荼蘼最符合宋人的审美情味,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的白色花瓣落尽,春天美好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对于荼蘼的爱其实也是对于时间逝去的无可奈何感的印证。
为何宋人如此热爱春天?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了时间的无可奈何。
历史到了宋代,时间就像一个中年人开始回忆往事,这个中年人见过了三代的神迹,汉唐的盛况,魏晋的衰乱。现在它只想停下脚步,在宋代的积贫积弱的身躯里,开始休息和回忆。这意味这个朝代不再像唐代那样,追求外在的成就,边塞建功立业的执着,任侠使气的快乐,或者游历三山五湖的壮怀。这个时代的人们终于从沉重的使命感中走出。宋人不再是春秋时士阶层手中被烹饪的“小鲜”,不再是被秦皇帝坑掉的三百无辨识度的儒生,不再是压抑中穷途痛哭的魏晋名士。
时间到了宋朝,这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个体意识开始主动觉醒。个体意识觉醒以后,开始关注人的本身,而不是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人一旦恢复其个体意识,对于美的追求必然开始强烈起来。艺术开始直面美本身,发现感受抒发美。
而最深刻的美往往同时间有关,时间的难以表达是艺术的终极难题。时间的消逝感是不可道破的天机,是不可言说的禅机。所以孔圣人“逝者如斯夫”的一句感慨,成了后世无数拥有时间意识的敏感心灵的共鸣。唐代的刘希夷写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句道破天机的金句后便招来了杀身之祸。然而这些都只是各自时代里孤单的个体。只有到了宋代,对于美的极度追求,才让时间消逝的无可奈何感成了这三百年间主流的情绪。而最能让这种情绪感发的,无疑是春天无与伦比的美和它的短暂性。因此,伤春之词滥觞于宋。
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的人们那样热爱着春日里的事物和感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把审美当做人生的主要追求、生命中终极意义。与其说宋人爱的是春天,不如说他们爱的是深刻的美。宋人这种对美的追求,直如宗教徒般的虔诚。
说到宗教,钱穆先生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琴棋书画,世俗生活等美的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宋代最能体现中国人这一信仰特征。因为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
合流意味着这三种信仰开始相互妥协、相互认同,儒释道在宋朝这里由形而上的玄妙转变为人间的美学。三教的追求虽然玄远,然而普通凡人却懂得删繁就简的智慧,将审美取代宗教,让俗世的一生在追求美的历程中安身立命。最能反映这种合流后新的美学观点的事实莫过于禅宗在宋代的滥觞。禅宗主张活在当下,这句话解释来说也就是要人们用审美的心态来对待世间每一刻的生活,以此来对抗时间的虚无。禅宗最懂时间的无可奈何,唯有在审美的过程中才能战胜世间的虚无与消逝。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是宋人的禅机,它伴随着寻春的启发。
当然,宋人的春天如此神圣多彩,还有其它耳熟能详的原因。
例如,宋朝是历史上最民富的朝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国穷民富”的朝代。大量流民涌入城市,造成了空前繁荣的市文化。同时,宋朝优待士大夫,宋朝也是历代假期最长的朝代,全年假期长达120多天(其身后的元朝假期仅有16天)。宋代重文轻武,士大夫阶层获得了空前绝后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优待。文化天才集中出现。宋代社会扁平化,门阀彻底销声匿迹,平等意识助推个体意识的强烈觉醒。
有钱,有闲,有品位高雅的市民阶层,有人格独立的文人集体,有平等舒适的社会氛围。于是,当春天来临了,宋人便在禅宗的天地境界里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