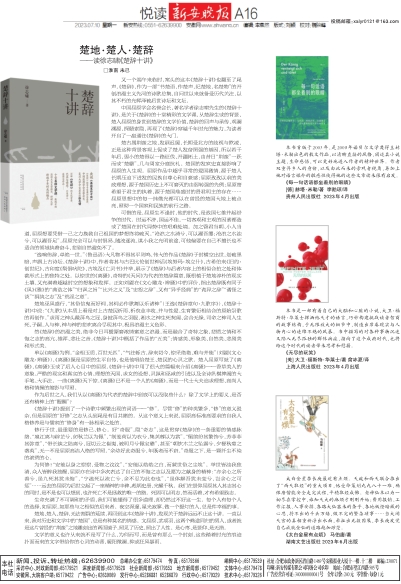发布日期:
楚地·楚人·楚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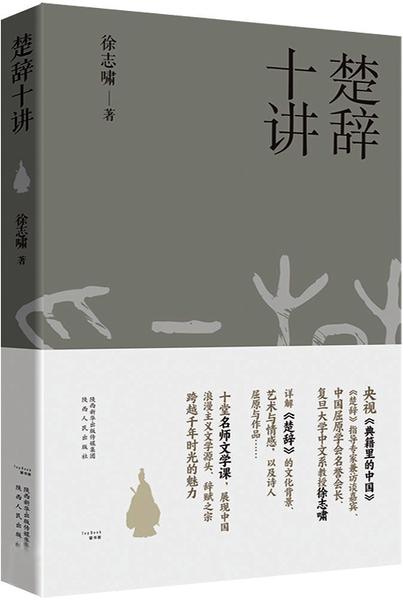
□淮南未已
又一个端午来临时,案头的这本《楚辞十讲》也翻至了尾声。《楚辞》,作为一部“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开创浪漫主义先河的诗歌总集,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历代关注,以其不朽的光辉泽被后世诗坛和文坛。
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学者徐志啸先生的《楚辞十讲》,是关于《楚辞》的十堂精彩的文学课,从楚辞生成的背景、楚人屈原的身世到楚辞的文学价值、楚辞的回声与承传,观澜溯源、探赜索隐,再现了《楚辞》穿越千年时光的魅力,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往《楚辞》的大门。
楚古属荆蛮之地,发展迟缓,长期受北方的歧视与欺凌,正是这种背景客观上促成了楚人发奋图强的基因,所以若干年后,弱小的楚得以一路征伐、开疆拓土,由昔日“荆蛮”一跃而成“楚霸”,几与周室分庭抗礼。楚国的发家史直接影响了屈原的人生观。屈原作品中超乎寻常的爱国激情,源于楚人长期压迫下迸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屈原孜孜以求的美政理想,源于楚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由弱转强的先例;屈原寄希望于君主的执着,源于楚国鼎盛时的贤君明主的存在……屈原思想中的每一抹微光都可以在曾经的楚国大地上被点亮,照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行之路。
可惜的是,屈原生不逢时,他的时代,是战国七雄并起纷争的时代。时运不济,国运不佳,一切客观和主观的因素都造成了楚国在时代局势中的艰难处境。加之昏君当朝、小人当道,屈原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挽救自己祖国的梦想终将破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完全可以与时俱易、随波逐流,谋小我之光明前途,可他偏要在自己不擅长也不适合的领域执着奋斗,悲剧自然避免不了。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伟大的作品《楚辞》于时横空出世,划破黑暗,声震上古诗坛。《楚辞十讲》中,作者将其与古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古希伯来《旧约·创世纪》、古印度《梨俱吠陀》、古埃及《亡灵书》并举,展示了《楚辞》与后者内容上的相似合拍之处和体裁形式上的独特之处。以惊世的《离骚》、奇特的《天问》为代表的楚辞篇章,既根植于楚地淳朴的现实土壤,又充满着超越时空的想象和发挥。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的评价,指出楚辞既有同于《风》《雅》的“典诰之体”“归讽之旨”“比兴之义”及“忠怨之辞”,又有“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
楚地巫风盛行,“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楚辞十讲》中说:“《九歌》从本质上看是对上古楚民祈雨、祈农业丰收,并与性爱、生育繁衍相结合的原始祭歌的再创作。”求雨之神头戴蓱鸟之冠、身披蓱鸟之羽服,湘水之神生死契阔、会合无缘,司命之神司人生死、子嗣,人与神、神与神的悲欢离合尽现其中,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然《楚辞》的浪漫之美,绝非今日耳鬓厮磨浓情蜜意之浪漫,而是融合了奇特之象、悲愤之情和不悔之志的高亢、雄浑、悲壮之音。《楚辞十讲》中概括了作品的“五美”;情感美、形象美、自然美、悲剧美和形式美。
单以《离骚》为例。“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离骚》既是屈原的生平自传,也是他唱给楚王、楚民的心灵之歌。楚人屈原写就了《离骚》,《离骚》玉成了后人心目中的屈原。《楚辞十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离骚》——香草美人的意象、严酷的现实和真实的心情、理想的天国、求女的设想、灵氛和巫咸的引进以及全诗纵横捭阖的大手笔、大手法。一曲《离骚》天下惊。《离骚》已不是一个人的《离骚》,而是一代士大夫追求理想、高尚人格和情操的缩影与写照。
作为后世之人,我们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中到底可以汲取些什么?除了文学上的要义,是否还有精神上的“醍醐”?
《楚辞十讲》提到了一个诗歌中频繁出现的词语——“修”。尽管“修”的种类繁多,“修”的意义驳杂,但是屈原的“好修”之志从头到尾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屈原高标准高要求的自我人格修养是与儒家的“修身”有一脉相承之处的。
修行于世,最重要的是修己、修心。好“奇服”,隐“奇志”,这是贯穿《楚辞》的一条重要的情感脉络。“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甚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无一不是屈原高洁人格的写照。“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奇服之下,是一颗纤尘不染的滚烫的心。
为何修?“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亦在诗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悔之志以及愿为之献身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远去的屈原为后世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彪炳史册,光耀千秋。我们在景仰屈原其人其志其心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想到,也许死亡不是拯救的唯一的路。死固可以明志,然而活着,才有希望践志。
生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可能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如屈原,如那些与之相似的后来者。夜空深邃,星光寂寥,做一个提灯的人,总是件幸福的事。
楚地、楚人、楚辞,无法割裂的延续,再回到这本《楚辞十讲》,发现关于楚辞远远不止这十讲。一直以来,我对历史和文学中的“楚国”,总是有种莫名的情感。文屈原、武项羽,这两个殊途同归的男人,或者就是这片曾经的“荆蛮”之地雕刻出的两面镜子,照见了历史,照出了人性。是心疼、是景仰、是无措。
文学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写了什么,为何而写,而是曾有那么一个时刻,这些踏着时光的痕迹扑面而来的文字带给你的心灵的动荡,暖阳微澜,抑或狂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