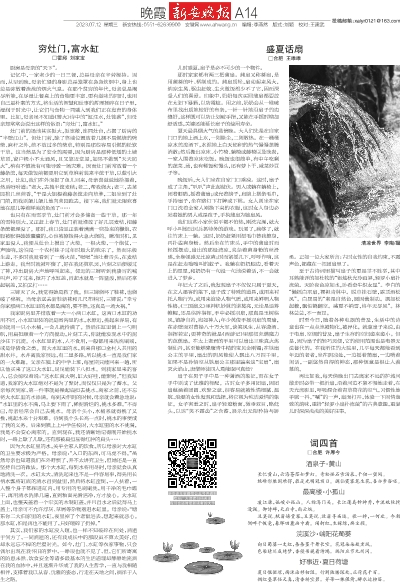发布日期:
穷灶门,富水缸
厨房是母亲的“天下”。
记忆中,一家老少的一日三餐,总是母亲在辛劳操持。因而,从早到晚,母亲忙碌的身影总是笼罩在袅袅炊烟中,身上也总是弥散着淡淡的烟火气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在尽量让餐桌上的食物更丰富、更有滋味的同时,也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将生活的智慧和世事的哲理揉碎在日子里,浸润于时光中,让它们与食物一同融入到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里。比如,母亲虽不知道《警火》诗中的“缸注水,灶徙薪”,但母亲却常常会说出这样的俗语:“穷灶门,富水缸。”
灶门前的场地其实挺大,挺宽敞,连同灶台,占据了厨房的“半壁江山”。但灶门前,除了靠墙位置放着几捆不易燃烧的劈柴、麻秆之外,绝不放过多的柴草,特别是那些容易引燃的松软干草。这当然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因为厨房是那种低矮的土墙草顶,窗户极小不太通风,且又靠近堂屋,如果不做到“天天防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一场灾难。因而灶门前常放着一个藤条筐,每天做饭前都要用它到草堆前装来半筐干草,以做引火之用。比如,我们在外面捉了鱼儿回来,母亲喜滋滋地拾掇着,然后吩咐道:“老大,去拽半筐麦秸;老二,帮我烧火;老三,去菜园掐几丝茴香。”于是大姐提着藤条筐走向草堆,二姐坐到了灶门前,而我则颠儿颠儿地向菜园跑去。接下来,我们就无限欢喜地在那儿等着鲜美的鱼汤了……
也只有在雨雪季节,灶门前才会多储备一些干草。那一年的雪特别大,又正赶上春节,灶门前就堆放了好几层麦秸,把藤条筐都埋没了。那时,我口袋里正装着满满一兜捡来的鞭炮,衣服被胀得鼓鼓囊囊的,心也被撩拨得火急火烧的。瞅准时机,见家里没人,我便从灶台上摸出了火柴。一根火柴,一个炮仗,一声脆响,这怕是一个农村娃子过年时最大的欢乐了。然而乐极生悲,不多时我就看到了一绺火苗,“咝咝”地吐着舌头,在麦秸上游走。我当时就被吓傻了,好在我还算机灵,片刻之后便缓过了神,冲出厨房大声地呼叫起来。邻近的三婶听到我凄厉的喊叫声,冲了过来,掀开了水缸盖,舀起水就是一阵猛泼,然后还拿起锅盖,又拍又打……
三婶灭了火,我觉得她是救了我。但三婶烧坏了鞋袜,也烧破了棉裤。当母亲送去新鞋新袜和几尺布料时,三婶说:“幸亏你家那两口水缸里的水都是满的,要不然,还真是一场大祸。”
我家厨房里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口水缸。这两口水缸的功用不同,小水缸里装的就是围沟里的水,水源近,挑起来容易,有时就用一只小木桶,一会儿就拎满了。然后往缸里倒上一勺明矾,用扁担顺着一个方向搅动,片刻工夫,你就能发现水中的泥沙往下沉淀。小水缸里的水,人不食用,一般都用来洗洗刷刷,或是烀猪食之类。而大水缸里的水,则来自那口全村人共用的甜水井。水井离我家很远,有二里多路,所以挑水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大难题。父亲在镇上的中学上班,每星期只能回来一趟,所以他买来了这口大水缸,足足能装下八担水。到我家里来的客人,总会惊叹着说:“这水缸真大啊,缸大好哇,能聚财。”但我知道,我家的大水缸绝对不是为了聚财,而仅仅只是为了蓄水。父亲每次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操起扁担去挑水,离家之前,还不忘将大水缸里的水添满。每到天作阴的时候,母亲就会着急地说:“水缸里的水不满,马上要下雨了,稀泥滑烂的,挑水多难。”不得已,母亲经常会自己去挑水。母亲个头小,水桶系就得挽了又挽,挑起水来十分艰难。待到我个头长高一点时,挑水的事便成了我的义务。后来到镇上上中学住校时,大水缸里的水不挑满,我是不会安心离家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刚开始挑水时,一路上歇了几歇,还有那被扁担压得红肿的肩头……
因为大水缸里的水,关乎全家人的饮食,所以母亲对大水缸的卫生要求极为严格。母亲说:“入口的东西,可马虎不得。”虽然母亲也知道我们在外野惯了,并不太讲究卫生,但她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个大水缸,每到水将用尽时,母亲就会认真地清洗一次。水缸太大,清洗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得先用长柄水瓢将缸底的清水舀到盆里,然后将水缸歪倒,一人扶着,一人整个身子都探进缸内,用专用的毛刷刷洗,用干净的毛巾醮干,再用清水洗涤几遍,直到釉面光滑洁净,方才放心。大水缸上面,也整天盖着一个牢实的木制缸盖,并且舀水之后就得马上盖上,母亲可不允许浮灰、草屑等杂物落进水缸里。母亲说:“塘东你二大伯家里的水缸,夜里掉了个老鼠进去,想起来就恶心。那水缸,怕是再也不能用了,只好砸碎了扔掉。”
其实,我们家的水缸没人砸,也一样不知破碎在何处,消逝于何方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我成长中的那段虽不算太美好,但却永远忘不掉的烂漫时光。如今,灶门、水缸等农家事物,只会偶尔出现在我怀旧的梦中,一睁眼也就不见了,但,它们所寄寓的防患未然、饮食安全等诸多最基本的生活道理却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并且逐渐升华成了我的人生哲学,一直与我相随相伴,支撑着我以从容、优雅的姿态,行走在天地之间,徜徉于人生之路。
记忆中,一家老少的一日三餐,总是母亲在辛劳操持。因而,从早到晚,母亲忙碌的身影总是笼罩在袅袅炊烟中,身上也总是弥散着淡淡的烟火气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在尽量让餐桌上的食物更丰富、更有滋味的同时,也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将生活的智慧和世事的哲理揉碎在日子里,浸润于时光中,让它们与食物一同融入到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里。比如,母亲虽不知道《警火》诗中的“缸注水,灶徙薪”,但母亲却常常会说出这样的俗语:“穷灶门,富水缸。”
灶门前的场地其实挺大,挺宽敞,连同灶台,占据了厨房的“半壁江山”。但灶门前,除了靠墙位置放着几捆不易燃烧的劈柴、麻秆之外,绝不放过多的柴草,特别是那些容易引燃的松软干草。这当然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因为厨房是那种低矮的土墙草顶,窗户极小不太通风,且又靠近堂屋,如果不做到“天天防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一场灾难。因而灶门前常放着一个藤条筐,每天做饭前都要用它到草堆前装来半筐干草,以做引火之用。比如,我们在外面捉了鱼儿回来,母亲喜滋滋地拾掇着,然后吩咐道:“老大,去拽半筐麦秸;老二,帮我烧火;老三,去菜园掐几丝茴香。”于是大姐提着藤条筐走向草堆,二姐坐到了灶门前,而我则颠儿颠儿地向菜园跑去。接下来,我们就无限欢喜地在那儿等着鲜美的鱼汤了……
也只有在雨雪季节,灶门前才会多储备一些干草。那一年的雪特别大,又正赶上春节,灶门前就堆放了好几层麦秸,把藤条筐都埋没了。那时,我口袋里正装着满满一兜捡来的鞭炮,衣服被胀得鼓鼓囊囊的,心也被撩拨得火急火烧的。瞅准时机,见家里没人,我便从灶台上摸出了火柴。一根火柴,一个炮仗,一声脆响,这怕是一个农村娃子过年时最大的欢乐了。然而乐极生悲,不多时我就看到了一绺火苗,“咝咝”地吐着舌头,在麦秸上游走。我当时就被吓傻了,好在我还算机灵,片刻之后便缓过了神,冲出厨房大声地呼叫起来。邻近的三婶听到我凄厉的喊叫声,冲了过来,掀开了水缸盖,舀起水就是一阵猛泼,然后还拿起锅盖,又拍又打……
三婶灭了火,我觉得她是救了我。但三婶烧坏了鞋袜,也烧破了棉裤。当母亲送去新鞋新袜和几尺布料时,三婶说:“幸亏你家那两口水缸里的水都是满的,要不然,还真是一场大祸。”
我家厨房里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口水缸。这两口水缸的功用不同,小水缸里装的就是围沟里的水,水源近,挑起来容易,有时就用一只小木桶,一会儿就拎满了。然后往缸里倒上一勺明矾,用扁担顺着一个方向搅动,片刻工夫,你就能发现水中的泥沙往下沉淀。小水缸里的水,人不食用,一般都用来洗洗刷刷,或是烀猪食之类。而大水缸里的水,则来自那口全村人共用的甜水井。水井离我家很远,有二里多路,所以挑水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大难题。父亲在镇上的中学上班,每星期只能回来一趟,所以他买来了这口大水缸,足足能装下八担水。到我家里来的客人,总会惊叹着说:“这水缸真大啊,缸大好哇,能聚财。”但我知道,我家的大水缸绝对不是为了聚财,而仅仅只是为了蓄水。父亲每次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操起扁担去挑水,离家之前,还不忘将大水缸里的水添满。每到天作阴的时候,母亲就会着急地说:“水缸里的水不满,马上要下雨了,稀泥滑烂的,挑水多难。”不得已,母亲经常会自己去挑水。母亲个头小,水桶系就得挽了又挽,挑起水来十分艰难。待到我个头长高一点时,挑水的事便成了我的义务。后来到镇上上中学住校时,大水缸里的水不挑满,我是不会安心离家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刚开始挑水时,一路上歇了几歇,还有那被扁担压得红肿的肩头……
因为大水缸里的水,关乎全家人的饮食,所以母亲对大水缸的卫生要求极为严格。母亲说:“入口的东西,可马虎不得。”虽然母亲也知道我们在外野惯了,并不太讲究卫生,但她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个大水缸,每到水将用尽时,母亲就会认真地清洗一次。水缸太大,清洗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得先用长柄水瓢将缸底的清水舀到盆里,然后将水缸歪倒,一人扶着,一人整个身子都探进缸内,用专用的毛刷刷洗,用干净的毛巾醮干,再用清水洗涤几遍,直到釉面光滑洁净,方才放心。大水缸上面,也整天盖着一个牢实的木制缸盖,并且舀水之后就得马上盖上,母亲可不允许浮灰、草屑等杂物落进水缸里。母亲说:“塘东你二大伯家里的水缸,夜里掉了个老鼠进去,想起来就恶心。那水缸,怕是再也不能用了,只好砸碎了扔掉。”
其实,我们家的水缸没人砸,也一样不知破碎在何处,消逝于何方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我成长中的那段虽不算太美好,但却永远忘不掉的烂漫时光。如今,灶门、水缸等农家事物,只会偶尔出现在我怀旧的梦中,一睁眼也就不见了,但,它们所寄寓的防患未然、饮食安全等诸多最基本的生活道理却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并且逐渐升华成了我的人生哲学,一直与我相随相伴,支撑着我以从容、优雅的姿态,行走在天地之间,徜徉于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