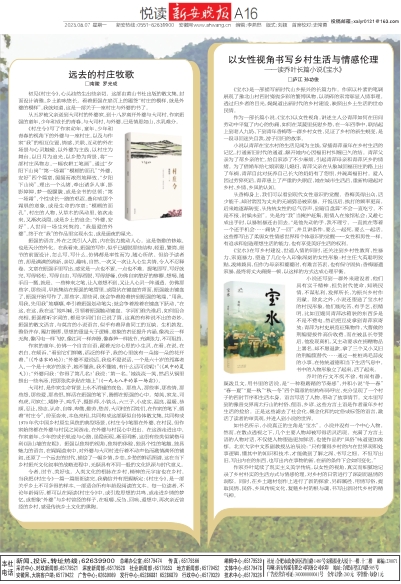发布日期:
以女性视角书写乡村生活与情感伦理
《宝水》是一部描写新时代山乡振兴的长篇力作。作家以朴素的笔调展现了豫北山村四时旖旎多彩的繁博风物,以琐碎的家常彰显人情事理,透过归乡者的目光,娓娓道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映照出乡土生活的世态民情。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宝水》以女性视角,讲述主人公青萍如何在田间劳动中平复了内心的伤痛,如何在菜蔬里抚慰乡愁,在一年四季中,联结起上到老人九奶、下到青年香梅等一群乡村女性,见证了乡村的新生蜕变,是一段寻回迷失自我、游子回归的故事。
小说以青萍在宝水村的生活见闻为主线,穿插青萍童年在乡村生活的记忆,打通新旧时代的通道,解开她内心因福田村纠缠已久的结。青萍父亲为了帮乡亲的忙,给自家添了不少麻烦,引起青萍母亲和青萍厌乡的情绪。为了借婚车给七娘家娶儿媳妇,青萍父亲在从象城回福田庄的路上出了车祸,青萍自此对抚养自己长大的奶奶有了怨恨,并疏离福田村。爱人因过劳猝死后,青萍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她在城市生活后,重新构建起对乡村、乡情、乡风的认知。
从香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香梅美得出众,话少能干,却时常因为丈夫的无端猜忌被家暴。开饭店后,挨打的频率更高,后来她逐渐转变,从传统女性的忍气吞声,到暗自盘算“不会一直吃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先是约“我”当掩护赶集,跟情人在旅馆私会;又趁七成出手时,以暴制暴还击回去。“是他先动的手,我不理亏。一直就在等着一个还手机会……痛快了一回”,并且讲条件,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活。这些都写出了柔弱女性情感世界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追求和创造理想生活的能力,也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宝水》在写乡村建设、世道人情的同时,还关注到乡村性教育、性暴力、家庭暴力,塑造了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村主任大英聪明狡黠、泼辣兼具,但作为母亲和婆婆时,有难言苦衷,也有保守固执;香梅屡遭家暴,最终将丈夫痛揍一顿,以这样的方式达成心理平衡。
小说还写到一群外来建设者,他们具有实干精神,担负时代使命,知晓民情,不谋私利,发挥所长,为振兴乡村作贡献。除此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宝水村的村民形象,他们能吃苦、有手艺、很精明,比如豆嫂问青萍冰箱装的东西多是不是不费电,然后把豆皮拿到青萍家寄放;青萍为村史展览征集物件,大曹做的荆编要按件高价收费,而在被县长夸赞后,他发现商机,又主动要求在捐赠物品上署名,却不愿退款,拿了三个又小又旧的荆编筐替代……通过一桩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传统道德和当下生活气息中,书中的人物形象立了起来,活了起来。
乔叶的行文不疾不徐,有闹有静,既泼且文,用书里的话说,是“一种稳踏踏的节奏感”,并和小说“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篇章的结构布局呼应,充分呈现了一个村子的四时节序和生活本身。语言写活了人物,带动了故事情节。文本里写到的豫晋交界南太行山的村俗、俚语、乡谚,这些方言土语是作者童年乡村生活的捡拾。正是这些滤去了社会化、概念化和约定俗成标签的语言,激活了读者的审美观,并进入到小说的世界。
如书名所示,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小说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然而,在散点透视之下,几个主要人物却被写得活灵活现。充满了方言土语的人物对话,不仅使人物塑造更加鲜活,也使作品的“风俗”味道更加浓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只有懂得乡村的内在世界观和处事逻辑,懂其中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做到了解之深、书写之细。不但写出旧,写出内在的东西,也写出内在事物的新,在新的条件下会如何变化。”
作家乔叶延续了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以女性的视角,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乡村朴实的生活方式与情感伦理,对乡村的日常进行了深刻而温情的洞察。同时,在乡土题材创作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另辟蹊径,用情写俗,提取民情、民俗、乡风传统文化,复魅乡村的根与魂,书写出新时代乡村的精气神。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宝水》以女性视角,讲述主人公青萍如何在田间劳动中平复了内心的伤痛,如何在菜蔬里抚慰乡愁,在一年四季中,联结起上到老人九奶、下到青年香梅等一群乡村女性,见证了乡村的新生蜕变,是一段寻回迷失自我、游子回归的故事。
小说以青萍在宝水村的生活见闻为主线,穿插青萍童年在乡村生活的记忆,打通新旧时代的通道,解开她内心因福田村纠缠已久的结。青萍父亲为了帮乡亲的忙,给自家添了不少麻烦,引起青萍母亲和青萍厌乡的情绪。为了借婚车给七娘家娶儿媳妇,青萍父亲在从象城回福田庄的路上出了车祸,青萍自此对抚养自己长大的奶奶有了怨恨,并疏离福田村。爱人因过劳猝死后,青萍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她在城市生活后,重新构建起对乡村、乡情、乡风的认知。
从香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香梅美得出众,话少能干,却时常因为丈夫的无端猜忌被家暴。开饭店后,挨打的频率更高,后来她逐渐转变,从传统女性的忍气吞声,到暗自盘算“不会一直吃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先是约“我”当掩护赶集,跟情人在旅馆私会;又趁七成出手时,以暴制暴还击回去。“是他先动的手,我不理亏。一直就在等着一个还手机会……痛快了一回”,并且讲条件,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活。这些都写出了柔弱女性情感世界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追求和创造理想生活的能力,也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宝水》在写乡村建设、世道人情的同时,还关注到乡村性教育、性暴力、家庭暴力,塑造了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村主任大英聪明狡黠、泼辣兼具,但作为母亲和婆婆时,有难言苦衷,也有保守固执;香梅屡遭家暴,最终将丈夫痛揍一顿,以这样的方式达成心理平衡。
小说还写到一群外来建设者,他们具有实干精神,担负时代使命,知晓民情,不谋私利,发挥所长,为振兴乡村作贡献。除此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宝水村的村民形象,他们能吃苦、有手艺、很精明,比如豆嫂问青萍冰箱装的东西多是不是不费电,然后把豆皮拿到青萍家寄放;青萍为村史展览征集物件,大曹做的荆编要按件高价收费,而在被县长夸赞后,他发现商机,又主动要求在捐赠物品上署名,却不愿退款,拿了三个又小又旧的荆编筐替代……通过一桩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传统道德和当下生活气息中,书中的人物形象立了起来,活了起来。
乔叶的行文不疾不徐,有闹有静,既泼且文,用书里的话说,是“一种稳踏踏的节奏感”,并和小说“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篇章的结构布局呼应,充分呈现了一个村子的四时节序和生活本身。语言写活了人物,带动了故事情节。文本里写到的豫晋交界南太行山的村俗、俚语、乡谚,这些方言土语是作者童年乡村生活的捡拾。正是这些滤去了社会化、概念化和约定俗成标签的语言,激活了读者的审美观,并进入到小说的世界。
如书名所示,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小说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然而,在散点透视之下,几个主要人物却被写得活灵活现。充满了方言土语的人物对话,不仅使人物塑造更加鲜活,也使作品的“风俗”味道更加浓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只有懂得乡村的内在世界观和处事逻辑,懂其中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做到了解之深、书写之细。不但写出旧,写出内在的东西,也写出内在事物的新,在新的条件下会如何变化。”
作家乔叶延续了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以女性的视角,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乡村朴实的生活方式与情感伦理,对乡村的日常进行了深刻而温情的洞察。同时,在乡土题材创作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另辟蹊径,用情写俗,提取民情、民俗、乡风传统文化,复魅乡村的根与魂,书写出新时代乡村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