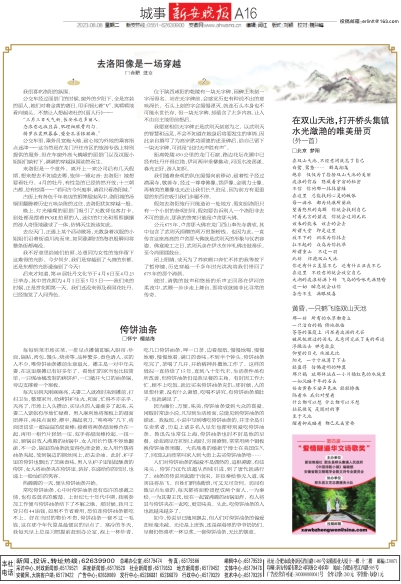发布日期:
侉饼油条
每每到菜市场买菜,一排早点摊铺即映入眼帘:炒面、锅贴、肉包、馒头、烧卖等,品种繁多,香色诱人,买的人不少,唯侉饼油条摊前生意最火。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在这里摆摊已有好多年了。看他们的家当也比较简单,一只煤油桶改制的烤饼炉,一口敞开大口的油条锅,旁边支撑着一个案板。
每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夫妻二人就准时来到摊前,打扫卫生,整理家当,给烤饼炉生火,和面,忙得不亦乐乎。天亮了,市场上人头攒动,买早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夫妻二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男人麻利地将案板上的湿面团抻开,再抹点面粉,擀平,操起菜刀,“咚咚咚”几下,将面团切成一溜扁扁的湿面棒;接着将两条湿面棒合在一起,再用一根竹片轻轻一压,双手将湿面棒拎起,一扭一拉,顺锅沿放入沸腾的油锅中,女人用长竹筷不停地翻滚,不一会,锅里的油条就变得色泽金黄,女人用竹筷将油条夹起,放到锅边的钢丝网上,沥去余油。此时,炉子里的侉饼也飘出了芝麻香味,男人从炉子里钳起酥黄的侉饼,女人将油条夹在侉饼里,装好,在递给你的同时,也递上一脸灿烂的笑容。
热腾腾的一天,便从侉饼油条开始。
常吃侉饼油条,心中对侉饼油条竟有些许的感激之情,也有些莫名的酸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便与侉饼油条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月工资只有44块钱,如果不节省着用,恐怕连侉饼油条都吃不上。好在当时的物价不贵,侉饼油条一套不过一毛钱,这在那个年代算是最便宜的早点了。寒冷的冬天,我每天早上总是习惯提前赶到办公室,泡上一杯炒青,吃几口侉饼油条,呷一口茶,边看报纸,慢慢地喝,慢慢地嚼,慢慢地看,满口的香味;不到半个钟头,侉饼油条吃完了,茶喝了几开,开始精神抖擞地工作了。这样的境况一直持续了15年,直到八十年代末,生活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侉饼油条仍是我早餐的主角。有时因工作太忙,顾不上吃饭,就近买来侉饼油条充饥;那时候,人的思想朴素,没有什么奢望,吃喝不讲究,有侉饼油条填肚子,也就满足了。
因为廉价、方便、味美,侉饼油条受到大众的喜爱。闲暇时常读小说,凡写到生活场面,总能见到侉饼油条的描述。我发现,小说中写到嗜吃侉饼油条的,并非全是引车卖浆者,历史上诸多名人早年也都特别爱吃侉饼油条。鲁迅先生常住上海,侉饼油条也时不时是他的早餐。徐悲鸿早年初到上海时,穷困潦倒,常常用两个铜板换侉饼油条果腹。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博士在美国住久了,回国以后经常叫家人到大街上去买侉饼油条啃……
人们对侉饼油条的偏爱不是偶然的,追根溯源,有些来头。侉饼乃汉代班超从西域引进,到了唐代就盛行了。油条的传说则起源于南宋。奸臣秦桧惨无人道,谋害良将岳飞。百姓们群情激愤,可又无可奈何。坊间有做早点生意的,每天都将面粉团捏成两个面人,一为秦桧,一为其妻王氏,绞在一起置沸腾的油锅里炸。有人将其与侉饼夹在一起吃,更觉味美。从此,吃侉饼油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如今,传说早已随风飘去,但人们对侉饼油条的偏爱却丝毫未减。无论是上班族,还是深巷里的爷爷奶奶们,早餐仍然喜欢一杯豆浆、一套侉饼油条,无比的惬意。
每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夫妻二人就准时来到摊前,打扫卫生,整理家当,给烤饼炉生火,和面,忙得不亦乐乎。天亮了,市场上人头攒动,买早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夫妻二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男人麻利地将案板上的湿面团抻开,再抹点面粉,擀平,操起菜刀,“咚咚咚”几下,将面团切成一溜扁扁的湿面棒;接着将两条湿面棒合在一起,再用一根竹片轻轻一压,双手将湿面棒拎起,一扭一拉,顺锅沿放入沸腾的油锅中,女人用长竹筷不停地翻滚,不一会,锅里的油条就变得色泽金黄,女人用竹筷将油条夹起,放到锅边的钢丝网上,沥去余油。此时,炉子里的侉饼也飘出了芝麻香味,男人从炉子里钳起酥黄的侉饼,女人将油条夹在侉饼里,装好,在递给你的同时,也递上一脸灿烂的笑容。
热腾腾的一天,便从侉饼油条开始。
常吃侉饼油条,心中对侉饼油条竟有些许的感激之情,也有些莫名的酸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便与侉饼油条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月工资只有44块钱,如果不节省着用,恐怕连侉饼油条都吃不上。好在当时的物价不贵,侉饼油条一套不过一毛钱,这在那个年代算是最便宜的早点了。寒冷的冬天,我每天早上总是习惯提前赶到办公室,泡上一杯炒青,吃几口侉饼油条,呷一口茶,边看报纸,慢慢地喝,慢慢地嚼,慢慢地看,满口的香味;不到半个钟头,侉饼油条吃完了,茶喝了几开,开始精神抖擞地工作了。这样的境况一直持续了15年,直到八十年代末,生活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侉饼油条仍是我早餐的主角。有时因工作太忙,顾不上吃饭,就近买来侉饼油条充饥;那时候,人的思想朴素,没有什么奢望,吃喝不讲究,有侉饼油条填肚子,也就满足了。
因为廉价、方便、味美,侉饼油条受到大众的喜爱。闲暇时常读小说,凡写到生活场面,总能见到侉饼油条的描述。我发现,小说中写到嗜吃侉饼油条的,并非全是引车卖浆者,历史上诸多名人早年也都特别爱吃侉饼油条。鲁迅先生常住上海,侉饼油条也时不时是他的早餐。徐悲鸿早年初到上海时,穷困潦倒,常常用两个铜板换侉饼油条果腹。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博士在美国住久了,回国以后经常叫家人到大街上去买侉饼油条啃……
人们对侉饼油条的偏爱不是偶然的,追根溯源,有些来头。侉饼乃汉代班超从西域引进,到了唐代就盛行了。油条的传说则起源于南宋。奸臣秦桧惨无人道,谋害良将岳飞。百姓们群情激愤,可又无可奈何。坊间有做早点生意的,每天都将面粉团捏成两个面人,一为秦桧,一为其妻王氏,绞在一起置沸腾的油锅里炸。有人将其与侉饼夹在一起吃,更觉味美。从此,吃侉饼油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如今,传说早已随风飘去,但人们对侉饼油条的偏爱却丝毫未减。无论是上班族,还是深巷里的爷爷奶奶们,早餐仍然喜欢一杯豆浆、一套侉饼油条,无比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