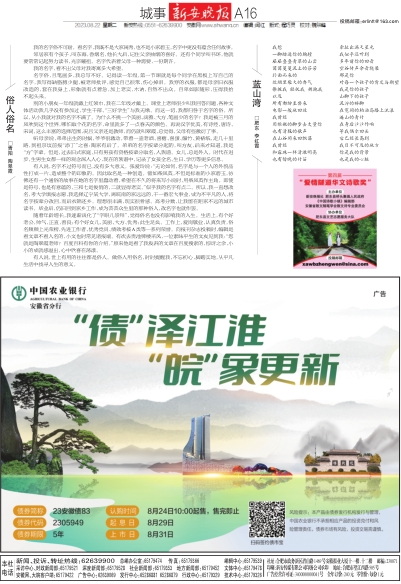发布日期:
俗人俗名
我的名字俗不可耐。看名字,我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名字中更没有蕴含任何故事。
邻居家有个孩子,叫东海,香烟名,他长大后,记住父亲抽烟的喜好。还有个同学叫书环,他就要常常记起努力读书,光宗耀祖。名字代表着父母一种需要,一份期许。
我的名字,看不出父母对我寄寓多大希望。
名字俗,且笔画多,我总写不好。记得读一年级,第一节课就是每个同学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我写得缺胳膊少腿,被老师批评,感觉自己很笨,伤心掉泪。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旧衣服改造的,套在我身上,形象就有点着急,加上老实,木讷,自然不出众。自卑如影随形,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别的小朋友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我在二年级才戴上。课堂上老师很少叫我回答问题,各种文体活动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与我无缘。而这一切,我都归咎于名字的俗。所以,从小我就对我的名字不满了。为什么不挑一个美丽、淡雅、大方,笔画少的名字?我是被三月的风吹到这个世界,哪怕取个花的名字,命里就多了一点春天的颜色。再说汉字优美,有诗经、唐诗、宋词,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况且父亲还是教师,而仍就叫翠霞,总觉得,父母有些敷衍了事。
听母亲说,弟弟出生的时候,爷爷很激动,带着一壶老酒、喜糖、喜蛋、爆竹、黄裱纸,走几十里路,到祖宗坟前报“添丁”之喜:陶家有后了。弟弟的名字按辈分起的,叫方友,后来才知道,我是“方”字辈。但是,过去旧式家庭,只有男孩有资格按辈分取名,入族谱。女儿,总是外人。时代在进步,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的族谱中,记录了女孩全名、生日、学历等更多信息。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张爱玲说:“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譬如柴风英,不但是标准的小家碧玉,彷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写小说时,用柴风英作主角。即使是符号,也是有意蕴的,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似乎我的名字有点二。所以,我一直想改名,考大学填报志愿,我选择辽宁某大学,离皖南的家远远的,干一番宏大事业,成为不平凡的人,将名字按辈分改回,而后衣锦还乡。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考分数,让我留在距家不远的城市读书。毕业后,仍旧回到家乡工作,成为芸芸众生里的那种俗人,改名字也就作罢。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淡化了“字眼儿崇拜”,觉得俗名也没有影响我的人生。生活上,有个好老公,帅气,正直,善良;有个好女儿,美丽、大方、优秀;此生足矣。工作上,爱岗敬业,认真负责,俗名频频上光荣榜,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绩效考核A类等一系列荣誉。向报刊杂志投稿时,编辑是看文章不看人名的,小文也时常见诸报端。有次去贵池牌楼采风,一位素昧平生的文友见到我:“您就是陶翠霞老师?百度百科有你的介绍。”原来他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在百度搜索的,惊讶之余,小小的成就感溢出,心中欣喜在荡漾。
有人说,世上有用的往往都是俗人。做俗人用俗名,时时提醒我,不忘初心,脚踏实地,从平凡生活中找寻人生的意义。
邻居家有个孩子,叫东海,香烟名,他长大后,记住父亲抽烟的喜好。还有个同学叫书环,他就要常常记起努力读书,光宗耀祖。名字代表着父母一种需要,一份期许。
我的名字,看不出父母对我寄寓多大希望。
名字俗,且笔画多,我总写不好。记得读一年级,第一节课就是每个同学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我写得缺胳膊少腿,被老师批评,感觉自己很笨,伤心掉泪。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旧衣服改造的,套在我身上,形象就有点着急,加上老实,木讷,自然不出众。自卑如影随形,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别的小朋友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我在二年级才戴上。课堂上老师很少叫我回答问题,各种文体活动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与我无缘。而这一切,我都归咎于名字的俗。所以,从小我就对我的名字不满了。为什么不挑一个美丽、淡雅、大方,笔画少的名字?我是被三月的风吹到这个世界,哪怕取个花的名字,命里就多了一点春天的颜色。再说汉字优美,有诗经、唐诗、宋词,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况且父亲还是教师,而仍就叫翠霞,总觉得,父母有些敷衍了事。
听母亲说,弟弟出生的时候,爷爷很激动,带着一壶老酒、喜糖、喜蛋、爆竹、黄裱纸,走几十里路,到祖宗坟前报“添丁”之喜:陶家有后了。弟弟的名字按辈分起的,叫方友,后来才知道,我是“方”字辈。但是,过去旧式家庭,只有男孩有资格按辈分取名,入族谱。女儿,总是外人。时代在进步,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的族谱中,记录了女孩全名、生日、学历等更多信息。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张爱玲说:“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譬如柴风英,不但是标准的小家碧玉,彷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写小说时,用柴风英作主角。即使是符号,也是有意蕴的,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似乎我的名字有点二。所以,我一直想改名,考大学填报志愿,我选择辽宁某大学,离皖南的家远远的,干一番宏大事业,成为不平凡的人,将名字按辈分改回,而后衣锦还乡。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考分数,让我留在距家不远的城市读书。毕业后,仍旧回到家乡工作,成为芸芸众生里的那种俗人,改名字也就作罢。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淡化了“字眼儿崇拜”,觉得俗名也没有影响我的人生。生活上,有个好老公,帅气,正直,善良;有个好女儿,美丽、大方、优秀;此生足矣。工作上,爱岗敬业,认真负责,俗名频频上光荣榜,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绩效考核A类等一系列荣誉。向报刊杂志投稿时,编辑是看文章不看人名的,小文也时常见诸报端。有次去贵池牌楼采风,一位素昧平生的文友见到我:“您就是陶翠霞老师?百度百科有你的介绍。”原来他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在百度搜索的,惊讶之余,小小的成就感溢出,心中欣喜在荡漾。
有人说,世上有用的往往都是俗人。做俗人用俗名,时时提醒我,不忘初心,脚踏实地,从平凡生活中找寻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