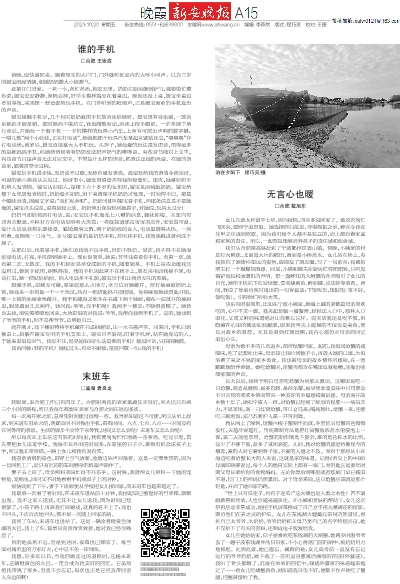发布日期:
无言心也暖
女儿在意大利留学七年,因为疫情,四年多没回家了。她这次匆忙飞回来,想回宁波祭祖。她选择回归故里,寻根探祖之举,着实令我在花甲之年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肩上都有着家庭和家族的责任。所以,一起祭祖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从合肥乘高铁赶到了宁波鄞州区姜山镇。傍晚,小姨家的村庄灯火稀疏,北面是大片的稻田,南面是小桥流水。女儿站在桥上,央我抓拍了她倚栏望远的姿势,旋即发了朋友圈,写了一句前言:我爸拍照主打一个模糊氛围感。回屋,小姨和姨夫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只听见锅铲划拉和油烟机的声响。那一盘鲜红的大闸蟹的外壳吸引了女儿的目光,她用手机拍下红膏炝蟹、雪菜烧黄鱼、醉泥螺、皮皮虾等菜肴。席间,我说了母亲待客时甩出的一句客套话:下饭呒告,饭缺饱(菜不好,饭吃饱)。引得他们哈哈大笑。
快乐有时很简单,比如在宁波小姨家,她端上桌的菜都是母亲喜欢吃的,心中不觉一震。我夹起炝蟹一撮蟹膏,轻轻送入口中,那种入口即化、又咸又鲜的味道绝对让你难以忘怀。说实话我还是吃不惯,但隐藏在心里的激动如浪翻滚,原来我舌尖上碰撞的不仅仅是美食,而是对故乡的眷恋。尤其是看到红膏炝蟹,我内心那份对母亲的回忆溢出心头。
母亲为数不多的几次返乡,都带炝蟹回家。起初,我怕闻炝蟹的咸腥味,吃了就想吐出来,母亲却让我吐到她手心,再放入她的口里,生怕浪费了来之不易的家乡美食。我也被母亲的故乡情怀所感染,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她。她吃炝蟹时,连蟹壳都含在嘴里反复咀嚼,还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
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母亲吃炝蟹为何那么激动。这哪里是吃一只炝蟹,简直是激情、是多巴胺、是荷尔蒙,是尽情享受美味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浓浓乡情而带来一种美好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母亲离开故乡数十年了,她和宁波人一样,对炝蟹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病后乏力,不思茶饭,剁一只红膏炝蟹,胃口立马来;喝高想吐,炝蟹一来,还能吃三碗泡饭,实乃苏浙沪人第一开胃利器。
我从网上了解到,炝蟹由梭子蟹制作而成,冬至前后母蟹膏色慢慢发红,天越冷膏越红。传统腌制方法是把红膏蟹放浓盐水里浸泡上一夜,第二天就能享用。炝蟹的制作倒是不复杂,难的是盐和水的比例,盐少了不够下饭,盐多了咸死骆驼。儿时,我对炝蟹的感觉特像现今的榴莲,爱的人对它爱到骨子里,不爱的人避之不及。而对于那些从小在海边吃着炝蟹长大的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记得《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说过,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哪里或者那扇门早已破旧不堪,但门上的密码仍然紧闭。对于母亲来说,这只炝蟹应该就是那个钥匙,开启了她回家的路。
“世上只有瓜连子,何有子连瓜?”这大概也是人类之本性?若不紧跟教育和传承,人性会越来越淡化。在小姨和堂妹的帮助下,女儿这次祭祖活动非常成功,她把手机屏幕换成了自己立于祖先墓碑前的留影,期待他们在天之灵的护佑。女儿在东钱湖大堰戴氏宗祠的族谱里,看到自己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和父母乃至自己的名字特别兴奋,她不仅拍下了有关的资料,还制成电子版发给我。
女儿在她姑姑家,似乎更喜欢吃东钱湖的大闸蟹,她两岁时跟爷爷去了一趟宁波东钱湖仲品伯伯家,不小心滑落门前的湖中,被奶奶用力地抓起。此情此景,她已遗忘。蹊跷的是,女儿高考前一直没有忘记远行的爷爷奶奶,她下载了一首用吴语慈溪话演唱的民谣《外婆谣》,我听了骨头都酥了,沉浸在浓浓的回忆中,顿感外婆家的味道越来越近了……看女儿吃螃蟹真香,她知道我牙齿不好,便默不作声地吃了蟹腿,把蟹黄留给了我。
我们从合肥乘高铁赶到了宁波鄞州区姜山镇。傍晚,小姨家的村庄灯火稀疏,北面是大片的稻田,南面是小桥流水。女儿站在桥上,央我抓拍了她倚栏望远的姿势,旋即发了朋友圈,写了一句前言:我爸拍照主打一个模糊氛围感。回屋,小姨和姨夫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只听见锅铲划拉和油烟机的声响。那一盘鲜红的大闸蟹的外壳吸引了女儿的目光,她用手机拍下红膏炝蟹、雪菜烧黄鱼、醉泥螺、皮皮虾等菜肴。席间,我说了母亲待客时甩出的一句客套话:下饭呒告,饭缺饱(菜不好,饭吃饱)。引得他们哈哈大笑。
快乐有时很简单,比如在宁波小姨家,她端上桌的菜都是母亲喜欢吃的,心中不觉一震。我夹起炝蟹一撮蟹膏,轻轻送入口中,那种入口即化、又咸又鲜的味道绝对让你难以忘怀。说实话我还是吃不惯,但隐藏在心里的激动如浪翻滚,原来我舌尖上碰撞的不仅仅是美食,而是对故乡的眷恋。尤其是看到红膏炝蟹,我内心那份对母亲的回忆溢出心头。
母亲为数不多的几次返乡,都带炝蟹回家。起初,我怕闻炝蟹的咸腥味,吃了就想吐出来,母亲却让我吐到她手心,再放入她的口里,生怕浪费了来之不易的家乡美食。我也被母亲的故乡情怀所感染,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她。她吃炝蟹时,连蟹壳都含在嘴里反复咀嚼,还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
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母亲吃炝蟹为何那么激动。这哪里是吃一只炝蟹,简直是激情、是多巴胺、是荷尔蒙,是尽情享受美味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浓浓乡情而带来一种美好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母亲离开故乡数十年了,她和宁波人一样,对炝蟹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病后乏力,不思茶饭,剁一只红膏炝蟹,胃口立马来;喝高想吐,炝蟹一来,还能吃三碗泡饭,实乃苏浙沪人第一开胃利器。
我从网上了解到,炝蟹由梭子蟹制作而成,冬至前后母蟹膏色慢慢发红,天越冷膏越红。传统腌制方法是把红膏蟹放浓盐水里浸泡上一夜,第二天就能享用。炝蟹的制作倒是不复杂,难的是盐和水的比例,盐少了不够下饭,盐多了咸死骆驼。儿时,我对炝蟹的感觉特像现今的榴莲,爱的人对它爱到骨子里,不爱的人避之不及。而对于那些从小在海边吃着炝蟹长大的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记得《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说过,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哪里或者那扇门早已破旧不堪,但门上的密码仍然紧闭。对于母亲来说,这只炝蟹应该就是那个钥匙,开启了她回家的路。
“世上只有瓜连子,何有子连瓜?”这大概也是人类之本性?若不紧跟教育和传承,人性会越来越淡化。在小姨和堂妹的帮助下,女儿这次祭祖活动非常成功,她把手机屏幕换成了自己立于祖先墓碑前的留影,期待他们在天之灵的护佑。女儿在东钱湖大堰戴氏宗祠的族谱里,看到自己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和父母乃至自己的名字特别兴奋,她不仅拍下了有关的资料,还制成电子版发给我。
女儿在她姑姑家,似乎更喜欢吃东钱湖的大闸蟹,她两岁时跟爷爷去了一趟宁波东钱湖仲品伯伯家,不小心滑落门前的湖中,被奶奶用力地抓起。此情此景,她已遗忘。蹊跷的是,女儿高考前一直没有忘记远行的爷爷奶奶,她下载了一首用吴语慈溪话演唱的民谣《外婆谣》,我听了骨头都酥了,沉浸在浓浓的回忆中,顿感外婆家的味道越来越近了……看女儿吃螃蟹真香,她知道我牙齿不好,便默不作声地吃了蟹腿,把蟹黄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