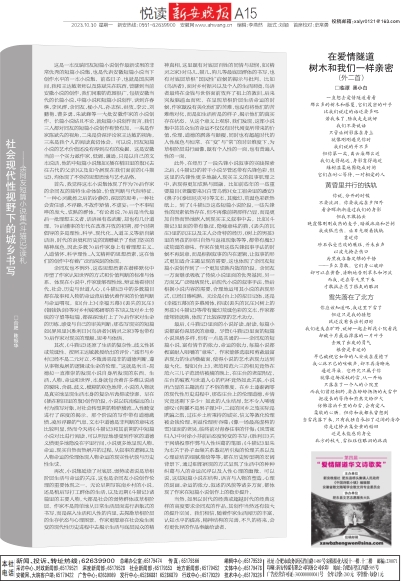发布日期:
社会现代性视野下的城乡书写
这是一本反映同友短篇小说创作最新成果的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代表安徽短篇小说当下创作水平的一本小说集。前些日子,也就是国庆期间,我和王达敏老师以及陈斌先在皖西,曾聊到当前安徽小说的创作,我们闲聊的范围很广,包括安徽当代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谈到许春樵、李凤群、余同友、杨小凡、孙志保、洪放、李云、刘鹏艳、曹多勇、朱斌峰等一大批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姑且不论,就短篇小说创作而言,我们三人都对同友的短篇小说创作称赞有加。一来是作家陈斌先的视角,二来是资深评论家王达敏的视角,三来是我个人的阅读真切体会。可以说,同友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这是安徽当前一个实力派作家,低调、谦逊,只是以自己的文本说话,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如《插在稻田里的旗》《去往古代的父亲》以及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斗猫记》,均体现了不俗的思想质地与艺术品格。
首先,我觉得这本小说集体现了作为70后作家的余同友的独特生命体验、价值判断与代际特征。“一种心灵激扬之后的冷静的、深层的思考;一种社会责任感,不浮躁,不故作矫情,不虚妄;一个不事喧哗的庞大、成熟的群体。”有论者说,70后是当代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话语虽有些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70后懂事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时期倡导的多是理性、科学、现代化、人道主义等新启蒙话语,时代的语境和历史的馈赠赋予了他们坚实的精神底色,因此多数70后作家身上有着理想主义、人道情怀、科学理性、人文精神的思想质素,这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体现。
余同友也不例外,这些思想质素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作家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与体系。体现在小说中,作家能够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时代、社会、历史与世道人心,《斗猫记》中的多数篇目都在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背后蛰伏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与命运喟叹。如《台上》《幸福五幕》《丢失的瓦庄》《铜钱铁剑》等对乡村破败凋零的书写以及对乡土传统的守望等短篇,都深深地打上了70后作家对生命的历练、感受与自己的审美判断;那些写现实的短篇如《屏风里》《胜利日》《鸟语者》《精灵之家》等也带有70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思考与体悟。
其次,《斗猫记》还原了生活的复杂性、歧义性甚或荒诞性。按照王达敏教授给出的评价:“城市与乡村已经不是二元对立,不做善恶是非的道德判断,遵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或生命的伦理。”这就是米兰·昆德拉一直推崇的发现小说自身所发现的东西。生活、人物、命运和世界,本身就包含着许多难以说清的暧昧、含混、歧义、模糊的灰色地带,小说的人物就是真实地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吊诡抑或悖谬。早在《插在稻田里的旗》创作阶段,小说以皖南偏远的山村为描写对象,对社会转型期的物欲横流、人性畸变进行了深度的揭示。那个阶段的写作带有道德激愤、凌厉浮躁的气息,文本中道德是非判断的意味还比较明显,然而今天将《斗猫记》和其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对比进行阅读,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的道德义愤更多地隐没在字里行间,小说更多地呈现人物、命运、现实自然而然展开的过程,从叙事的逻辑以及人物命运的伦理体现人物命运的现实性状貌与历史性生成。
再次,小说集延续了对底层、弱势或者说是草根阶层生活与命运的关注,这也是余同友小说创作伦理的重要体现之一。无论早期写皖南乡村的小说,还是稍后写打工群体的生活,以及近期《斗猫记》诸篇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草根阶层。作家不是简单地从日常生活层面进行表象式的书写,而是深入生活和人性的内里,去探勘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图景。作家更愿意在社会发生剧变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去揭示生活与底层民众的精神真相,这里既有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悲悯,如《精灵之家》对马儿、猫儿、狗儿等最底层群体的书写,也有对底层草根“国民性”症候的揭示与批判。比如《鸟语者》,面对乡村振兴以及个人的生活困境,鸟语者最终在金钱与世俗面前放弃了祖上的教训,后来突发脑溢血而死。在呈现草根阶层生活命运的时候,作家既没有美化他们的苦难,也没有将他们的苦难绝对化,而是如生活所是的样子,揭示他们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我们发现,这部小说集中芸芸众生的命运不仅仅有时代剧变所带来的价值、伦理、道德的震荡与颠覆,同时也有超越时代的人性底色与恒常。在“变”与“常”的时空维度下,为草根阶层进行画像,既有个人性的一面,也有普遍人性的一面。
此外,在经历了一段先锋小说叙事的实践探索之后,《斗猫记》的若干小说尽管还带有先锋色彩,但这里的先锋性更多地融入现实主义的叙事肌理之中,表现得更加成熟与圆融。比如前些年的一些重要篇目《老魏要来》《白雪乌鸦》《女工宿舍里的潘安》《鼻子》《泰坦尼克号》等文本,其魔幻、荒诞色彩跃然纸上。到了《斗猫记》这些短篇小说阶段,一些先锋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像前期那样凸显,而是更加自然而然地嵌入到现实主义叙事中去。比如《斗猫记》里面的带有象征、隐喻意味的猫,《丢失的瓦庄》里的瓦庄以及主人公奇特的经历,《树上的男孩》里的男孩的回归自然与返祖现象等等,都带有魔幻或荒诞的意味。作家在使用这些先锋叙事手法的时候不再刻意,而是根据叙事的内在逻辑,让叙事的形式更加适合主题呈现的需要,这也体现了余同友短篇小说创作到了一个更加成熟内敛的阶段。余同友一方面继承吸收了传统小说里面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又广泛吸纳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法,然后根据小说内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其小说的表现形式,已经日臻纯熟。无论是《台上》的拟日记体,还是《幸福五幕》的多幕剧体,抑或《丢失的瓦庄》《树上的男孩》《斗猫记》等带有魔幻荒诞色彩的文本,作家都能驾轻就熟,体现了比较深厚的艺术功力。
最后,《斗猫记》里面的小说好读、耐读,每篇小说都富有深层次的意蕴。尽管《斗猫记》里面的短篇小说风格多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余同友的短篇小说,富有情节的张力、命运的张力,每篇小说都极富耐人咀嚼的“意味”。作家能够选取和剪裁最富表现力的生活横截面,使得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达到最大化。譬如《台上》,老范和范六三的相见竟然在范六三儿子范团结被捕的晚上,在庄台的老屋附近,庄台的破败与世道人心的朽坏竟然如此关联,小说所凸显的主题就有了不俗的维度。在乡土逐渐凋零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那些庄台上的伦理道德、乡情究竟还剩下多少?如此的人生结局,怎不令人唏嘘感叹?《狗獾不是果子狸》中,二叔的回乡之旅实际是欺骗之旅,过往乡土所秉持的诚实、信义等教化伦理被金钱伦理、利益伦理所吞噬;《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里面的老吴,临终前对青春往事的忏悔;《风雪夜归人》中对徐小芬前后态度转变的书写;《胜利日》关于网络投票作弊与人性纠葛的笔墨;《斗猫记》里朱为本关于孙子血缘关系鉴定所引发的伦理关系以及心理症结的细腻描绘等等,都在历史转型期的宏阔背景下,通过细部展现的方式呈现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与人的命运沉浮以及人性心理的幽微。可以说,这些短篇小说在结构、语言与人物的塑造、心理的刻画、命运的张力、叙述的风貌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稳步提升。
当然,如果以时代的经典或超越时代的经典这样的高度要求余同友的作品,其创作当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相信,随着作家生活阅历的丰富,认知水平的提高,精神结构的完善,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优异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首先,我觉得这本小说集体现了作为70后作家的余同友的独特生命体验、价值判断与代际特征。“一种心灵激扬之后的冷静的、深层的思考;一种社会责任感,不浮躁,不故作矫情,不虚妄;一个不事喧哗的庞大、成熟的群体。”有论者说,70后是当代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话语虽有些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70后懂事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时期倡导的多是理性、科学、现代化、人道主义等新启蒙话语,时代的语境和历史的馈赠赋予了他们坚实的精神底色,因此多数70后作家身上有着理想主义、人道情怀、科学理性、人文精神的思想质素,这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体现。
余同友也不例外,这些思想质素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作家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与体系。体现在小说中,作家能够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时代、社会、历史与世道人心,《斗猫记》中的多数篇目都在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背后蛰伏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与命运喟叹。如《台上》《幸福五幕》《丢失的瓦庄》《铜钱铁剑》等对乡村破败凋零的书写以及对乡土传统的守望等短篇,都深深地打上了70后作家对生命的历练、感受与自己的审美判断;那些写现实的短篇如《屏风里》《胜利日》《鸟语者》《精灵之家》等也带有70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思考与体悟。
其次,《斗猫记》还原了生活的复杂性、歧义性甚或荒诞性。按照王达敏教授给出的评价:“城市与乡村已经不是二元对立,不做善恶是非的道德判断,遵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或生命的伦理。”这就是米兰·昆德拉一直推崇的发现小说自身所发现的东西。生活、人物、命运和世界,本身就包含着许多难以说清的暧昧、含混、歧义、模糊的灰色地带,小说的人物就是真实地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吊诡抑或悖谬。早在《插在稻田里的旗》创作阶段,小说以皖南偏远的山村为描写对象,对社会转型期的物欲横流、人性畸变进行了深度的揭示。那个阶段的写作带有道德激愤、凌厉浮躁的气息,文本中道德是非判断的意味还比较明显,然而今天将《斗猫记》和其前期的中短篇小说对比进行阅读,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的道德义愤更多地隐没在字里行间,小说更多地呈现人物、命运、现实自然而然展开的过程,从叙事的逻辑以及人物命运的伦理体现人物命运的现实性状貌与历史性生成。
再次,小说集延续了对底层、弱势或者说是草根阶层生活与命运的关注,这也是余同友小说创作伦理的重要体现之一。无论早期写皖南乡村的小说,还是稍后写打工群体的生活,以及近期《斗猫记》诸篇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草根阶层。作家不是简单地从日常生活层面进行表象式的书写,而是深入生活和人性的内里,去探勘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图景。作家更愿意在社会发生剧变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去揭示生活与底层民众的精神真相,这里既有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与悲悯,如《精灵之家》对马儿、猫儿、狗儿等最底层群体的书写,也有对底层草根“国民性”症候的揭示与批判。比如《鸟语者》,面对乡村振兴以及个人的生活困境,鸟语者最终在金钱与世俗面前放弃了祖上的教训,后来突发脑溢血而死。在呈现草根阶层生活命运的时候,作家既没有美化他们的苦难,也没有将他们的苦难绝对化,而是如生活所是的样子,揭示他们的真实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我们发现,这部小说集中芸芸众生的命运不仅仅有时代剧变所带来的价值、伦理、道德的震荡与颠覆,同时也有超越时代的人性底色与恒常。在“变”与“常”的时空维度下,为草根阶层进行画像,既有个人性的一面,也有普遍人性的一面。
此外,在经历了一段先锋小说叙事的实践探索之后,《斗猫记》的若干小说尽管还带有先锋色彩,但这里的先锋性更多地融入现实主义的叙事肌理之中,表现得更加成熟与圆融。比如前些年的一些重要篇目《老魏要来》《白雪乌鸦》《女工宿舍里的潘安》《鼻子》《泰坦尼克号》等文本,其魔幻、荒诞色彩跃然纸上。到了《斗猫记》这些短篇小说阶段,一些先锋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像前期那样凸显,而是更加自然而然地嵌入到现实主义叙事中去。比如《斗猫记》里面的带有象征、隐喻意味的猫,《丢失的瓦庄》里的瓦庄以及主人公奇特的经历,《树上的男孩》里的男孩的回归自然与返祖现象等等,都带有魔幻或荒诞的意味。作家在使用这些先锋叙事手法的时候不再刻意,而是根据叙事的内在逻辑,让叙事的形式更加适合主题呈现的需要,这也体现了余同友短篇小说创作到了一个更加成熟内敛的阶段。余同友一方面继承吸收了传统小说里面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又广泛吸纳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法,然后根据小说内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其小说的表现形式,已经日臻纯熟。无论是《台上》的拟日记体,还是《幸福五幕》的多幕剧体,抑或《丢失的瓦庄》《树上的男孩》《斗猫记》等带有魔幻荒诞色彩的文本,作家都能驾轻就熟,体现了比较深厚的艺术功力。
最后,《斗猫记》里面的小说好读、耐读,每篇小说都富有深层次的意蕴。尽管《斗猫记》里面的短篇小说风格多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余同友的短篇小说,富有情节的张力、命运的张力,每篇小说都极富耐人咀嚼的“意味”。作家能够选取和剪裁最富表现力的生活横截面,使得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达到最大化。譬如《台上》,老范和范六三的相见竟然在范六三儿子范团结被捕的晚上,在庄台的老屋附近,庄台的破败与世道人心的朽坏竟然如此关联,小说所凸显的主题就有了不俗的维度。在乡土逐渐凋零的现代性历史进程中,那些庄台上的伦理道德、乡情究竟还剩下多少?如此的人生结局,怎不令人唏嘘感叹?《狗獾不是果子狸》中,二叔的回乡之旅实际是欺骗之旅,过往乡土所秉持的诚实、信义等教化伦理被金钱伦理、利益伦理所吞噬;《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里面的老吴,临终前对青春往事的忏悔;《风雪夜归人》中对徐小芬前后态度转变的书写;《胜利日》关于网络投票作弊与人性纠葛的笔墨;《斗猫记》里朱为本关于孙子血缘关系鉴定所引发的伦理关系以及心理症结的细腻描绘等等,都在历史转型期的宏阔背景下,通过细部展现的方式呈现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与人的命运沉浮以及人性心理的幽微。可以说,这些短篇小说在结构、语言与人物的塑造、心理的刻画、命运的张力、叙述的风貌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稳步提升。
当然,如果以时代的经典或超越时代的经典这样的高度要求余同友的作品,其创作当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相信,随着作家生活阅历的丰富,认知水平的提高,精神结构的完善,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优异的作品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