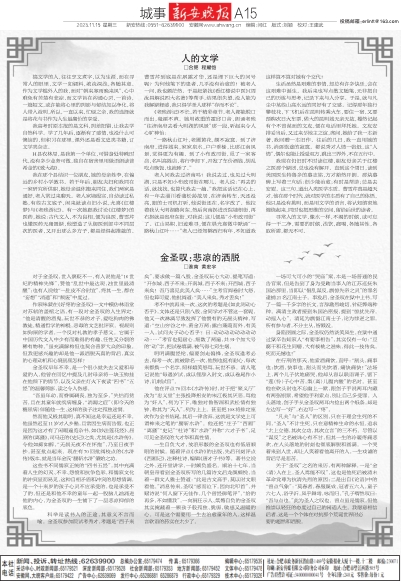发布日期:
金圣叹:悲凉的洒脱
对于金圣叹,世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16世纪的精神先锋”,赞他“乱世中最达观,浊世里最清醒”;也有人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终其一生,都在“妄想”“消遣”和“颓废”中度过。
作家咪蒙在《好疼的金圣叹》一文中模仿林语堂对苏轼的盖棺之语,有一段对金圣叹的人生界定:“他是清醒的酒鬼,玩世不恭的才子,爱吃狗肉的佛教徒,精通哲学的神棍,恶毒的文艺批评家。视规则如狗屎的学者,一个反对礼教的孝子慈父。它属于中国历代文人中少有而难得的有趣、任性又分裂的稀有物种。”虽充满解构但也契合普罗大众的印象,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他一派洒脱天真的背后,真实的心理动机和心境到底怎样?
金圣叹早年不幸,是一个很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的人,他曾在回忆中提及儿时母亲将一块玉钩挂在他颈下的情节,以及父亲在灯火下夜读“四书”“五经”的温馨剪影,读之令人伤感。
“吾虽年幼,而眷属凋丧,独为至多。”失怙而贫苦,且在其童年就疾病缠身,“消渴之症”(即今天的糖尿病)伴随他一生,这样的孩子注定孤独迷惘。
然而他又极其聪明,真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他虽然迟至11岁才入乡塾,且常因生病而告假,也正是因为这才有了闲暇遍览杂书,如《妙法莲花经》、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之类,尤其是《水浒传》,令他如痴如醉,“无晨无夜不在怀抱”,乃至日夜手抄,甚至批点起来。现在有70回批阅校点的《水浒传》版本,就是当年金氏“腰斩水浒”肇始之功。
这些书不同儒家正统的“四书五经”,其中充满着人生的幻灭、不幸、怨愤和抗争色彩,和儒家文化的冲突显而易见,这种自相矛盾和冲突的思想情调,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心灵不应承受的,也是承受不了的,但还是和他不幸的童年一起一股脑儿汹涌进他的内心,为金圣叹的一生铺下了一层悲凉抑郁的底色。
科举是读书人的正途,其意义不言而喻。金圣叹参加院试考秀才,考题是“西子来矣”,要求做一篇八股,金圣叹玩心大动,提笔写道:“开东城,西子不来;开南城,西子不来;开西城,西子来矣!吾乃喜见此美人矣……”主考官阅卷时大怒,但也算可爱,他批阅道:“美人来矣,秀才丢矣!”
考不中就再来一次,这次的考题是《如此则动心否乎》,文体还是只限八股,金同学才不管这一套呢,他又一次淋漓尽致发挥了他惯有的无厘头精神,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蒹葭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考官也挺耐心,细数了两遍,共39个加大号的“动”字,把试卷填满,被气得七窍生烟。
明明满腹经纶,偏要剑走偏锋,金圣叹逢考必去,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挺有耐心,每次来都换一个名字,照样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以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
他在评点70回本《水浒传》时,对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主张投降招安的宋江极其厌恶,骂他为“奸人”,列为下下,唯独对鲁智深和武松情有独钟,称其为“天人”,列为上上。甚至把108将排定座次作为全书结尾,其后一律舍弃,这就是文学史上可谓神来之笔的“腰斩水浒”。他还把“庄子”“西厢”“离骚”“史记”“杜诗”和“水浒”并称“六才子书”,足可见金圣叹的大才华和真性情。
一生自负大才,放浪形骸的金圣叹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随着评点《水浒》的出版,先后刊刻评点《西厢记》,注释杜诗,编辑《唐才子书》等。著书立说之外,还开堂讲学,一时颇负盛名。顺治十七年,当朝皇帝看到金圣叹所写的几篇诗文后龙颜颇悦,当着一群文人雅士赞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消息传来,圣叹“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并赋诗说“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给的再多,不如懂我”,一向狷狂示人、桀骜自负的金圣叹其实掩藏着一颗孩子般孤独、脆弱、敏感又温暖的心。可是这个需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人,这样温言软语的药实在太少了。
一场可大可小的“哭庙”案,本是一场普通的民告官案,但是告到了身为受贿当事人的江苏巡抚朱国治那里,当即以“倡乱谋反,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逮捕21名江南士子。事发后,金圣叹在狱中上书,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长文,言辞激烈峻切,针砭弊端种种。满清主政者接到朱国治密报,提到“惊扰先帝,动摇人心”。清廷为震慑江南士子,论为悖逆之罪,所有参与者,不分主从,皆戮没。
身陷囹圄之际,金圣叹仍然谈笑风生,在狱中通过狱卒告知家人“有要事相告”,其实仅有一句:“豆腐干和花生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在行刑的那天,他索酒痛饮,直呼:“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法场上,两个儿子伏地痛哭,他却从容以联语课子,留下“莲(怜)子心中苦,梨(离)儿腹内酸”的名对。甚至他在砍头时也不忘幽上一默,跟刽子手说两耳内藏有两张银票,希望他手利索点,别让自己多受罪。人头落地,刽子手从金圣叹两耳内捻出两个纸条,却是左边写一“好”,右边写一“疼”。
“凡夫”与“圣人”的区别,只在于理会生死的不同,“圣人”不计生死,只在意精神生命的永恒,追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尽管以“谋反”之名被诛心有不甘,但其一生的冷暖疼痛悲欢,在人头落地的时刻也彻底解脱和圆满。一个哭着来到人世,却让人笑着看他离开的人,一生戏谑的背后尽是悲苦。
关于“圣叹”之名的来历,有两种解释,一是“金(清)人在上,圣人焉能不叹”,这也是他死后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的原因;二是出自《论语》中的“曾点气象”:“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此为圣人之叹也。曾点虽是儒家,但他推崇以轻狂的态度过自己的闲适人生。我愿意相信后者,这是一个个体在对抗那个荒诞世界时必要的超然和洒脱。
作家咪蒙在《好疼的金圣叹》一文中模仿林语堂对苏轼的盖棺之语,有一段对金圣叹的人生界定:“他是清醒的酒鬼,玩世不恭的才子,爱吃狗肉的佛教徒,精通哲学的神棍,恶毒的文艺批评家。视规则如狗屎的学者,一个反对礼教的孝子慈父。它属于中国历代文人中少有而难得的有趣、任性又分裂的稀有物种。”虽充满解构但也契合普罗大众的印象,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他一派洒脱天真的背后,真实的心理动机和心境到底怎样?
金圣叹早年不幸,是一个很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的人,他曾在回忆中提及儿时母亲将一块玉钩挂在他颈下的情节,以及父亲在灯火下夜读“四书”“五经”的温馨剪影,读之令人伤感。
“吾虽年幼,而眷属凋丧,独为至多。”失怙而贫苦,且在其童年就疾病缠身,“消渴之症”(即今天的糖尿病)伴随他一生,这样的孩子注定孤独迷惘。
然而他又极其聪明,真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他虽然迟至11岁才入乡塾,且常因生病而告假,也正是因为这才有了闲暇遍览杂书,如《妙法莲花经》、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之类,尤其是《水浒传》,令他如痴如醉,“无晨无夜不在怀抱”,乃至日夜手抄,甚至批点起来。现在有70回批阅校点的《水浒传》版本,就是当年金氏“腰斩水浒”肇始之功。
这些书不同儒家正统的“四书五经”,其中充满着人生的幻灭、不幸、怨愤和抗争色彩,和儒家文化的冲突显而易见,这种自相矛盾和冲突的思想情调,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心灵不应承受的,也是承受不了的,但还是和他不幸的童年一起一股脑儿汹涌进他的内心,为金圣叹的一生铺下了一层悲凉抑郁的底色。
科举是读书人的正途,其意义不言而喻。金圣叹参加院试考秀才,考题是“西子来矣”,要求做一篇八股,金圣叹玩心大动,提笔写道:“开东城,西子不来;开南城,西子不来;开西城,西子来矣!吾乃喜见此美人矣……”主考官阅卷时大怒,但也算可爱,他批阅道:“美人来矣,秀才丢矣!”
考不中就再来一次,这次的考题是《如此则动心否乎》,文体还是只限八股,金同学才不管这一套呢,他又一次淋漓尽致发挥了他惯有的无厘头精神,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蒹葭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考官也挺耐心,细数了两遍,共39个加大号的“动”字,把试卷填满,被气得七窍生烟。
明明满腹经纶,偏要剑走偏锋,金圣叹逢考必去,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挺有耐心,每次来都换一个名字,照样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以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
他在评点70回本《水浒传》时,对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主张投降招安的宋江极其厌恶,骂他为“奸人”,列为下下,唯独对鲁智深和武松情有独钟,称其为“天人”,列为上上。甚至把108将排定座次作为全书结尾,其后一律舍弃,这就是文学史上可谓神来之笔的“腰斩水浒”。他还把“庄子”“西厢”“离骚”“史记”“杜诗”和“水浒”并称“六才子书”,足可见金圣叹的大才华和真性情。
一生自负大才,放浪形骸的金圣叹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随着评点《水浒》的出版,先后刊刻评点《西厢记》,注释杜诗,编辑《唐才子书》等。著书立说之外,还开堂讲学,一时颇负盛名。顺治十七年,当朝皇帝看到金圣叹所写的几篇诗文后龙颜颇悦,当着一群文人雅士赞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消息传来,圣叹“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并赋诗说“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给的再多,不如懂我”,一向狷狂示人、桀骜自负的金圣叹其实掩藏着一颗孩子般孤独、脆弱、敏感又温暖的心。可是这个需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人,这样温言软语的药实在太少了。
一场可大可小的“哭庙”案,本是一场普通的民告官案,但是告到了身为受贿当事人的江苏巡抚朱国治那里,当即以“倡乱谋反,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逮捕21名江南士子。事发后,金圣叹在狱中上书,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长文,言辞激烈峻切,针砭弊端种种。满清主政者接到朱国治密报,提到“惊扰先帝,动摇人心”。清廷为震慑江南士子,论为悖逆之罪,所有参与者,不分主从,皆戮没。
身陷囹圄之际,金圣叹仍然谈笑风生,在狱中通过狱卒告知家人“有要事相告”,其实仅有一句:“豆腐干和花生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在行刑的那天,他索酒痛饮,直呼:“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法场上,两个儿子伏地痛哭,他却从容以联语课子,留下“莲(怜)子心中苦,梨(离)儿腹内酸”的名对。甚至他在砍头时也不忘幽上一默,跟刽子手说两耳内藏有两张银票,希望他手利索点,别让自己多受罪。人头落地,刽子手从金圣叹两耳内捻出两个纸条,却是左边写一“好”,右边写一“疼”。
“凡夫”与“圣人”的区别,只在于理会生死的不同,“圣人”不计生死,只在意精神生命的永恒,追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尽管以“谋反”之名被诛心有不甘,但其一生的冷暖疼痛悲欢,在人头落地的时刻也彻底解脱和圆满。一个哭着来到人世,却让人笑着看他离开的人,一生戏谑的背后尽是悲苦。
关于“圣叹”之名的来历,有两种解释,一是“金(清)人在上,圣人焉能不叹”,这也是他死后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的原因;二是出自《论语》中的“曾点气象”:“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此为圣人之叹也。曾点虽是儒家,但他推崇以轻狂的态度过自己的闲适人生。我愿意相信后者,这是一个个体在对抗那个荒诞世界时必要的超然和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