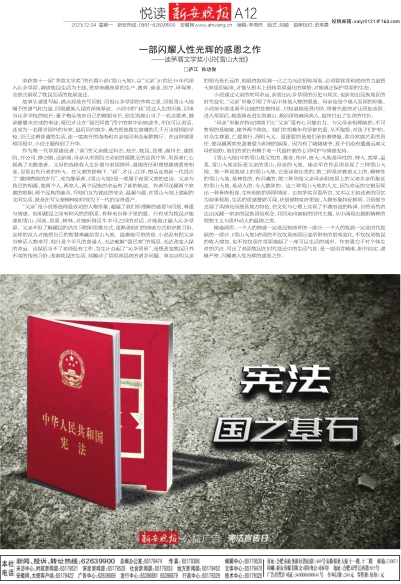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一部闪耀人性光辉的感恩之作
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父亲”20世纪50年代深入沁多草原、调查牧民生活为主线,贯穿青藏高原的生产、教育、商业、医疗、环保等,全景式展现了牧民生活的发展变迁。
故事从感恩写起,落点却是在写回报:回报沁多草原的养育之恩,回报雪山大地赐予的勇气和力量,回报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小说中的“我”经过人生的历练,回来当沁多学校的校长;妻子梅朵放弃自己的舞蹈专长,到生别离山当了一名志愿者,继承婆婆未完成的事业;哑巴才让在“强巴阿爸”西宁的家中治病读书,不仅可以说话,还成为一名留学国外的专家,最后回归家乡;桑杰把他做生意赚的几千万全部捐给学校,自己过着普通的生活,连一度离开的洛洛和央金也回来办起歌舞厅。在这种感恩和回报中,小说主题得到了升华。
作为第一代草原建设者,“我”的父亲做过科长、校长、牧民、经理、副州长,建医院、开公司、修公路、迁新城;母亲从市医院主动到资源匮乏的县医疗所,用医者仁心拯救了无数患者。父母的选择将人生价值与家国情怀、道德责任和理想激情紧密相连,呈现出先行者的伟大。在父辈的影响下,“我”、才让、江洋、梅朵这些新一代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继承者。《雪山大地》是一部属于高原父辈的史诗。父亲与角巴的相遇,使两个人、两家人、两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轨迹。作者写汉藏两个家庭的联姻,两个民族的融合,写他们互为彼此的成全、温暖与爱,在雪山大地上建起的文明生活,就是在写父辈精神如何成为下一代的宝贵遗产。
“父亲”是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感恩与回报、尊重与情感。他和藏民之间有种天然的联系,有种来自骨子里的爱。只有成为牧民才能感知雪山、河流、草原、树林,才能听得见牛羊马之间的对话,才能真正融入沁多草原。父亲不但了解藏民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更熟悉他们的情感方式和宗教习俗,这样的汉人才能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雪山大地。最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没有把父亲当神话人物来写,他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无法破解“强巴案”的冤屈,无法改变入狱的命运。出狱后当不了老师没有工作,为生计办起了“沁多贸易”,是想改变牧民只养不卖的传统习俗,改善牧民的生活,却触动了草原深层次的诸多问题。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是长远的,他最终发现靠一己之力无法扭转局面,必须要靠党和政府的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草原退化的颓势,才能真正保护草原的生态。
小说通过父亲的坎坷命运,折射出沁多草原的历史与现实,也折射出民族地区的时代变化,“父亲”形象引领了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塑造。母亲也是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小说前半部还看不出她的性格特征,只知道她是贤内助,带着失聪的才让四处求医。进入草原后,她选择走进生别离山,救治那些麻风病人,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母亲”形象在特定情境下比“父亲”更有心灵撞击力。与父母亲相辉映的、不可忽视的是姥姥、姥爷两个角色。他们在艰难年代坚韧负重,从不抱怨,对孩子们护佑,对众生尊重,仁爱善行,深明大义。更重要的是他们承担着修复、弥合家庭关系的责任,使汉藏两家充盈着爱与和谐的氛围。因为有了姥姥姥爷,孩子们没有遭遇远离父母的创伤,他们的成长有赖于老一代最朴素的心灵呵护与情感支持。
《雪山大地》中的雪山是父性的,雄奇、伟岸、高大;大地是母性的,博大、宽厚、温柔,雪山大地实际是父亲的雪山、母亲的大地。杨志军在作品里呈现了三种雪山大地。第一种是地域上的雪山大地,它是诗意壮美的;第二种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性的雪山大地,是神性的,有灵魂的;第三种则是父亲母亲和高原上的父老乡亲所象征的雪山大地,是动人的、令人敬仰的。这三种雪山大地的人文,因为命运的交错呈现出一种骨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正如茅奖评委所言,文本以主叙述者的回忆为叙事视角,生活的质感謦欬可闻,状景描物如在眼前,人物形象特征鲜明,习俗细节去除了风情化而独具地方特色,在文化与心理上实现了不落痕迹的转译,自然而然表达出汉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观念,共同走向富裕的时代主题,从中涌现出提振精神的理想主义与质朴动人的温情之美。
掩卷深思,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雪山大地》表现的不仅仅是高原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牧民的收入增加,也不仅仅是在草原建起了一座可以生活的城市。作家致力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写出了高原牧民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气息,是一部语言精准、细节结实、逻辑严密,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感恩之作。
故事从感恩写起,落点却是在写回报:回报沁多草原的养育之恩,回报雪山大地赐予的勇气和力量,回报藏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小说中的“我”经过人生的历练,回来当沁多学校的校长;妻子梅朵放弃自己的舞蹈专长,到生别离山当了一名志愿者,继承婆婆未完成的事业;哑巴才让在“强巴阿爸”西宁的家中治病读书,不仅可以说话,还成为一名留学国外的专家,最后回归家乡;桑杰把他做生意赚的几千万全部捐给学校,自己过着普通的生活,连一度离开的洛洛和央金也回来办起歌舞厅。在这种感恩和回报中,小说主题得到了升华。
作为第一代草原建设者,“我”的父亲做过科长、校长、牧民、经理、副州长,建医院、开公司、修公路、迁新城;母亲从市医院主动到资源匮乏的县医疗所,用医者仁心拯救了无数患者。父母的选择将人生价值与家国情怀、道德责任和理想激情紧密相连,呈现出先行者的伟大。在父辈的影响下,“我”、才让、江洋、梅朵这些新一代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继承者。《雪山大地》是一部属于高原父辈的史诗。父亲与角巴的相遇,使两个人、两家人、两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轨迹。作者写汉藏两个家庭的联姻,两个民族的融合,写他们互为彼此的成全、温暖与爱,在雪山大地上建起的文明生活,就是在写父辈精神如何成为下一代的宝贵遗产。
“父亲”是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感恩与回报、尊重与情感。他和藏民之间有种天然的联系,有种来自骨子里的爱。只有成为牧民才能感知雪山、河流、草原、树林,才能听得见牛羊马之间的对话,才能真正融入沁多草原。父亲不但了解藏民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更熟悉他们的情感方式和宗教习俗,这样的汉人才能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雪山大地。最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没有把父亲当神话人物来写,他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无法破解“强巴案”的冤屈,无法改变入狱的命运。出狱后当不了老师没有工作,为生计办起了“沁多贸易”,是想改变牧民只养不卖的传统习俗,改善牧民的生活,却触动了草原深层次的诸多问题。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是长远的,他最终发现靠一己之力无法扭转局面,必须要靠党和政府的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草原退化的颓势,才能真正保护草原的生态。
小说通过父亲的坎坷命运,折射出沁多草原的历史与现实,也折射出民族地区的时代变化,“父亲”形象引领了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塑造。母亲也是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小说前半部还看不出她的性格特征,只知道她是贤内助,带着失聪的才让四处求医。进入草原后,她选择走进生别离山,救治那些麻风病人,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母亲”形象在特定情境下比“父亲”更有心灵撞击力。与父母亲相辉映的、不可忽视的是姥姥、姥爷两个角色。他们在艰难年代坚韧负重,从不抱怨,对孩子们护佑,对众生尊重,仁爱善行,深明大义。更重要的是他们承担着修复、弥合家庭关系的责任,使汉藏两家充盈着爱与和谐的氛围。因为有了姥姥姥爷,孩子们没有遭遇远离父母的创伤,他们的成长有赖于老一代最朴素的心灵呵护与情感支持。
《雪山大地》中的雪山是父性的,雄奇、伟岸、高大;大地是母性的,博大、宽厚、温柔,雪山大地实际是父亲的雪山、母亲的大地。杨志军在作品里呈现了三种雪山大地。第一种是地域上的雪山大地,它是诗意壮美的;第二种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性的雪山大地,是神性的,有灵魂的;第三种则是父亲母亲和高原上的父老乡亲所象征的雪山大地,是动人的、令人敬仰的。这三种雪山大地的人文,因为命运的交错呈现出一种骨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正如茅奖评委所言,文本以主叙述者的回忆为叙事视角,生活的质感謦欬可闻,状景描物如在眼前,人物形象特征鲜明,习俗细节去除了风情化而独具地方特色,在文化与心理上实现了不落痕迹的转译,自然而然表达出汉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观念,共同走向富裕的时代主题,从中涌现出提振精神的理想主义与质朴动人的温情之美。
掩卷深思,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雪山大地》表现的不仅仅是高原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牧民的收入增加,也不仅仅是在草原建起了一座可以生活的城市。作家致力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写出了高原牧民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气息,是一部语言精准、细节结实、逻辑严密,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感恩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