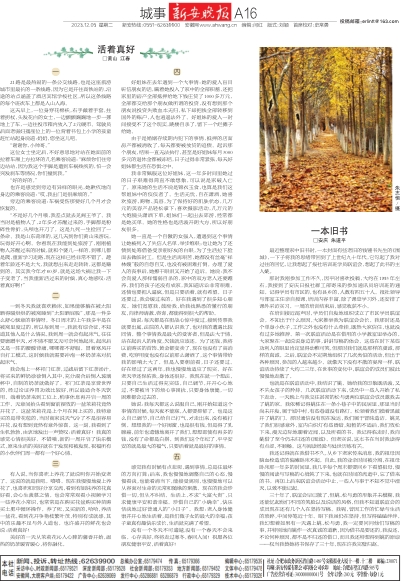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一本旧书
最近整理家中旧书时,一本封面有些老旧的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一下子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它勾起了我对过往的回忆,让我想起了报社培训班学员联谊会,想起了此书的主人姚。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因平时喜欢投稿,大约在1993年左右,我接到了安庆日报社群工部寄来的参加通讯员培训班的通知。记得学员有市区的,也有县乡的,人数有四五十人。报社领导与部室主任亲自授课,培训内容丰富,除了课堂学习外,还安排了课外采访实习。一周的培训结束后,感觉收获不小。
在培训接近尾声时,学员们自发地组织成立了市区学员联谊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推举我为联谊会会长。我那时还是个单身小伙子,工作之外也没有什么牵挂,既然大家信任,也就没有过多地推辞。第一次联谊活动是在借用的小学教室里举办的。大家聚在一起说说身边的事,讲讲写稿的体会。这些在时下某些功利人的眼里肯定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时我们就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真诚。之后,联谊会不定期地组织了几次类似的活动,但出于各种原因,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联谊活动持续了大约二三年,在世事的变化中,联谊会的成员们彼此慢慢地走散了。
也就是在联谊活动中,我结识了姚。她给我的印象既活泼,又不失女孩子的矜持。几次联谊活动下来,成员中一些人开始了私下走动。一天晚上与我交往甚密的松与勇两位联谊会成员邀我去了姚的家。我依稀记得姚住在一条小巷子中的民居里,那里当时尚未开发,属于城中村,有些巷道没有路灯。松领着我们摸着黑敲开了姚的门。那时通信没有现在发达,我们属于冒昧造访。姚见了我们很感意外,室内白炽灯有些昏暗,短暂的不适后,我们放松下来,漫无边际地聊着近闻,以及所看的书。我记得临走时,我向姚借了至今仍未归还的《围城》。但老实说,这本书在当时我读得有点涩,不顺畅。这与阅读经验与处世历练有关。
我还记得就在我借书不久,从乡下老家传来消息,我的祖母因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卧床不起。自此,我的业余时间被分割,在祖母卧床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乡下看望祖母,慢慢的阅读与写稿的心境钝了下来,也就在时间的流逝中,忘了借来的书。再加上后来联谊会活动中止,一些人与事于不知不觉中湮灭,以致不能记起。
三十年了,联谊会早已散了,但姚、松与勇的形象并未模糊,我还能忆起他们不同的笑脸以及说话的风格,但我不知道联谊会的成员现在还有几个人在坚持写稿。我呢,曾因工作的忙碌与生活的琐碎,中间停笔近十年。眼下我虽仍在坚持,但写得磕磕绊绊。我幻想着如果有一天遇上姚、松与勇,我一定要问问他们写稿的事,并特别地向姚作一次真诚的道歉,因为借书是要还的,我没还,不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不归还的借口,而且我还特想得到姚的原谅——权当我替她将书保存了三十年,现在许我完璧归赵。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因平时喜欢投稿,大约在1993年左右,我接到了安庆日报社群工部寄来的参加通讯员培训班的通知。记得学员有市区的,也有县乡的,人数有四五十人。报社领导与部室主任亲自授课,培训内容丰富,除了课堂学习外,还安排了课外采访实习。一周的培训结束后,感觉收获不小。
在培训接近尾声时,学员们自发地组织成立了市区学员联谊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推举我为联谊会会长。我那时还是个单身小伙子,工作之外也没有什么牵挂,既然大家信任,也就没有过多地推辞。第一次联谊活动是在借用的小学教室里举办的。大家聚在一起说说身边的事,讲讲写稿的体会。这些在时下某些功利人的眼里肯定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时我们就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真诚。之后,联谊会不定期地组织了几次类似的活动,但出于各种原因,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联谊活动持续了大约二三年,在世事的变化中,联谊会的成员们彼此慢慢地走散了。
也就是在联谊活动中,我结识了姚。她给我的印象既活泼,又不失女孩子的矜持。几次联谊活动下来,成员中一些人开始了私下走动。一天晚上与我交往甚密的松与勇两位联谊会成员邀我去了姚的家。我依稀记得姚住在一条小巷子中的民居里,那里当时尚未开发,属于城中村,有些巷道没有路灯。松领着我们摸着黑敲开了姚的门。那时通信没有现在发达,我们属于冒昧造访。姚见了我们很感意外,室内白炽灯有些昏暗,短暂的不适后,我们放松下来,漫无边际地聊着近闻,以及所看的书。我记得临走时,我向姚借了至今仍未归还的《围城》。但老实说,这本书在当时我读得有点涩,不顺畅。这与阅读经验与处世历练有关。
我还记得就在我借书不久,从乡下老家传来消息,我的祖母因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卧床不起。自此,我的业余时间被分割,在祖母卧床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乡下看望祖母,慢慢的阅读与写稿的心境钝了下来,也就在时间的流逝中,忘了借来的书。再加上后来联谊会活动中止,一些人与事于不知不觉中湮灭,以致不能记起。
三十年了,联谊会早已散了,但姚、松与勇的形象并未模糊,我还能忆起他们不同的笑脸以及说话的风格,但我不知道联谊会的成员现在还有几个人在坚持写稿。我呢,曾因工作的忙碌与生活的琐碎,中间停笔近十年。眼下我虽仍在坚持,但写得磕磕绊绊。我幻想着如果有一天遇上姚、松与勇,我一定要问问他们写稿的事,并特别地向姚作一次真诚的道歉,因为借书是要还的,我没还,不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不归还的借口,而且我还特想得到姚的原谅——权当我替她将书保存了三十年,现在许我完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