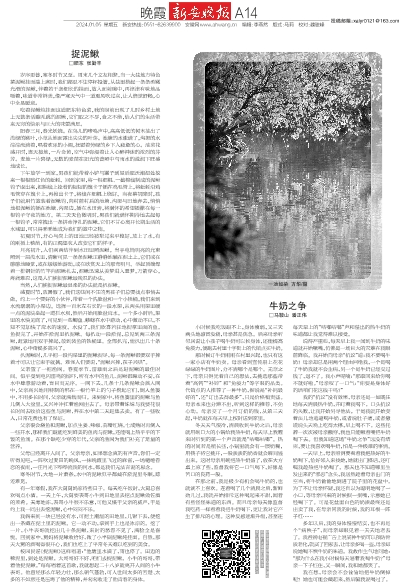发布日期:
捉泥鳅
岁序更替,寒冬时节又至。周末几个文友相聚,当一大盆地方特色菜泥鳅挂面端上席时,我们都忍不住停杯投箸,从盆里捞起一条条柔嫩光滑的泥鳅,伴着若干条细长的挂面,放入面前碗中,再津津有味地品咂着,味道非常鲜美,像严寒天气中一道熏风吹过来,让人倍觉舒畅,心中全是暖意。
吃着泥鳅炖挂面这道肥东特色菜,我的眼前出现了儿时乡村土地上无数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它们取之不尽,食之不绝,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快乐与巨大的味蕾满足。
阳春三月,春光妖娆。在鸟儿的啼鸣声中,高高低低的树木抽出了浅绿的嫩叶,小草从地面露出尖尖的叶芽。池塘的水涨满了,沟渠的水淙淙流淌着,唱着欢乐的小调,抚慰着劳碌的乡下人疲惫的心。油菜花盛开时,连天接地,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心醉神迷的浓烈的芬芳。麦地一片碧绿,无数的麦苗在阳光的普照中与雨水的滋润下旺盛地成长。
下午放学一到家,男孩们就带着小铲与罐子到屋后肥沃潮湿处挖来一根根暗红色的蚯蚓。回到家里,将一根细棍、一截棉线制成的泥鳅钓子取出来,把棉线上拴着的短短的篾卡子插在鸡毛管上,将蚯蚓沿鸡毛管穿在篾卡上,再拔出卡子,将线在细棍上绕好。当夜幕初降时,孩子们就用竹篮装着泥鳅钓,向村前村后的池塘、沟渠与田地奔去,悄悄地把泥鳅钓插在池塘、沟渠边,插在水田旁,将满怀的希望播撒在每一根钓子守夜的地方。第二天天色微明时,男孩们就满怀期待地去起每一根钓子,常常拽出一条拼命挣扎的泥鳅,它们不甘心离开长期生活的水域里,可只得乖乖地成为我们的篮中之物。
初夏时节,圩心与岗上的田地已经被犁过来平整好,放上了水,有的刚插上秧苗,有的正渴望农人改变它们的样子。
月亮初升,人们两两结伴到水田里照泥鳅。当手电筒明亮的光束照到一层浅水里,清晰可见一条条泥鳅正静静地躺在泥土上,它们或在憨憨地睡觉,或在缓缓地游动,或在欣赏天上的那弯明月。举起顶端焊着一排钢针的竹竿向泥鳅扎去,泥鳅迅速从美梦进入噩梦,万箭穿心,疼痛难忍,这是人们捕捉泥鳅最残忍的办法。
当然,人们捕捉泥鳅最温柔的办法就是扒泥鳅。
盛夏时节,放暑假了,我们这些闲不住的男孩子们总要找点事情去做。约上一个要好的小伙伴,带着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小铁桶,我们来到水流潺潺的小渠边。选择一百米左右长的一段水渠,从两头用渠里硬一点的泥块垒起一道拦水坝,然后开始用脸盆戽水。一个多小时后,渠里的水快见底了,可见到一些鲫鱼、鲹鲦在水中游动,心中激动不已,不知不觉加快了戽水的速度。水没了,我们欣喜若狂地捉拿里面的鱼。鱼捉完了,开始在淤泥里扒泥鳅。每扒动一段淤泥,总见到两三条泥鳅,赶紧地用双手捧起,放到装鱼的铁桶里。全部扒完,能扒出几十条泥鳅,心中甭提多高兴了。
扒泥鳅时,几乎把一段沟渠里的泥鳅捉尽,每一条泥鳅都要双手捧着才可以让它束手就擒。难怪人们要说,“泥鳅兴捧,孩子兴哄”。
父亲置了一把渔网。春夏季节,雷暴雨之后是赶泥鳅的最佳时间。似乎受到电闪雷鸣的惊吓,所有水中的鱼儿、泥鳅都躁动不安,在水中肆意游动着,盲目而无序。一网下去,几条十几条泥鳅会落入网中,父亲高兴地用特制的绑在一根竹竿上的勺子捞起它们,倒入鱼篓中,不用多长时间,父亲就满载而归。来到家中,将鱼篓里的泥鳅与鱼儿倒入大盆里,又兴冲冲扛着渔网出去了。母亲带着妹妹与我要花很长时间去收拾这些鱼与泥鳅,养在水中第二天赶集去卖。有了一些收入,日常花费也有了保证。
父亲很会烧鱼和泥鳅,加点生姜、辣椒、蒜瓣红烧,七成熟时再倒入一些开水,那样我们既能吃到鲜美的鱼肉与泥鳅,还能喝上热乎乎的下饭的鱼汤。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父亲的渔网为我们补充了足量的营养。
父母已经离开人间了。父亲母亲,如果想念真的有声音,你们一定听得见吧,一阵吹过麦田的晚风,一抹晚霞里飞过的麻雀,一场缱绻眷恋的夜雨,一汪月光下哗哗流淌的河水,都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思念。
寒冬时节,大地一片萧条,水中的泥鳅似乎都藏在淤泥里冬眠,踪迹难觅。
有一年寒假,我在大舅舅妈家待些日子。每天吃午饭时,大舅总喜欢喝点小酒。一天上午,大舅要表哥小牛到田地里去挖点泥鳅做佐酒的菜肴。天寒地冻,表哥小牛很不乐意,可他又慑于父亲的威严,于是约上我一同出去挖泥鳅,心中闷闷不乐。
我俩来到一块已经没有水,可泥土潮湿的田地里,几锹下去,便挖出一条藏在泥土里的泥鳅。它一动不动,拿到手上也是冰凉的。挖了一片,小牛表哥就挖出几十条泥鳅,来时的愁容不见了,满脸全是喜悦。回到家中,舅妈将泥鳅收拾好,做了小半锅泥鳅炖挂面。自然,那天大舅的酒喝得很开心,我们也吃上了平常冬天难以吃到的美食。
校园民谣《捉泥鳅》这样唱道:“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每每唱着这首歌,我就想起二十八岁就离开人间的小牛表哥。他曾经那么年轻力壮,那么朝气蓬勃,可人世间太多的苦楚、太多的不如意还是压垮了他的精神,并匆匆收走了他青春的身体。
吃着泥鳅炖挂面这道肥东特色菜,我的眼前出现了儿时乡村土地上无数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它们取之不尽,食之不绝,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穷的快乐与巨大的味蕾满足。
阳春三月,春光妖娆。在鸟儿的啼鸣声中,高高低低的树木抽出了浅绿的嫩叶,小草从地面露出尖尖的叶芽。池塘的水涨满了,沟渠的水淙淙流淌着,唱着欢乐的小调,抚慰着劳碌的乡下人疲惫的心。油菜花盛开时,连天接地,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心醉神迷的浓烈的芬芳。麦地一片碧绿,无数的麦苗在阳光的普照中与雨水的滋润下旺盛地成长。
下午放学一到家,男孩们就带着小铲与罐子到屋后肥沃潮湿处挖来一根根暗红色的蚯蚓。回到家里,将一根细棍、一截棉线制成的泥鳅钓子取出来,把棉线上拴着的短短的篾卡子插在鸡毛管上,将蚯蚓沿鸡毛管穿在篾卡上,再拔出卡子,将线在细棍上绕好。当夜幕初降时,孩子们就用竹篮装着泥鳅钓,向村前村后的池塘、沟渠与田地奔去,悄悄地把泥鳅钓插在池塘、沟渠边,插在水田旁,将满怀的希望播撒在每一根钓子守夜的地方。第二天天色微明时,男孩们就满怀期待地去起每一根钓子,常常拽出一条拼命挣扎的泥鳅,它们不甘心离开长期生活的水域里,可只得乖乖地成为我们的篮中之物。
初夏时节,圩心与岗上的田地已经被犁过来平整好,放上了水,有的刚插上秧苗,有的正渴望农人改变它们的样子。
月亮初升,人们两两结伴到水田里照泥鳅。当手电筒明亮的光束照到一层浅水里,清晰可见一条条泥鳅正静静地躺在泥土上,它们或在憨憨地睡觉,或在缓缓地游动,或在欣赏天上的那弯明月。举起顶端焊着一排钢针的竹竿向泥鳅扎去,泥鳅迅速从美梦进入噩梦,万箭穿心,疼痛难忍,这是人们捕捉泥鳅最残忍的办法。
当然,人们捕捉泥鳅最温柔的办法就是扒泥鳅。
盛夏时节,放暑假了,我们这些闲不住的男孩子们总要找点事情去做。约上一个要好的小伙伴,带着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小铁桶,我们来到水流潺潺的小渠边。选择一百米左右长的一段水渠,从两头用渠里硬一点的泥块垒起一道拦水坝,然后开始用脸盆戽水。一个多小时后,渠里的水快见底了,可见到一些鲫鱼、鲹鲦在水中游动,心中激动不已,不知不觉加快了戽水的速度。水没了,我们欣喜若狂地捉拿里面的鱼。鱼捉完了,开始在淤泥里扒泥鳅。每扒动一段淤泥,总见到两三条泥鳅,赶紧地用双手捧起,放到装鱼的铁桶里。全部扒完,能扒出几十条泥鳅,心中甭提多高兴了。
扒泥鳅时,几乎把一段沟渠里的泥鳅捉尽,每一条泥鳅都要双手捧着才可以让它束手就擒。难怪人们要说,“泥鳅兴捧,孩子兴哄”。
父亲置了一把渔网。春夏季节,雷暴雨之后是赶泥鳅的最佳时间。似乎受到电闪雷鸣的惊吓,所有水中的鱼儿、泥鳅都躁动不安,在水中肆意游动着,盲目而无序。一网下去,几条十几条泥鳅会落入网中,父亲高兴地用特制的绑在一根竹竿上的勺子捞起它们,倒入鱼篓中,不用多长时间,父亲就满载而归。来到家中,将鱼篓里的泥鳅与鱼儿倒入大盆里,又兴冲冲扛着渔网出去了。母亲带着妹妹与我要花很长时间去收拾这些鱼与泥鳅,养在水中第二天赶集去卖。有了一些收入,日常花费也有了保证。
父亲很会烧鱼和泥鳅,加点生姜、辣椒、蒜瓣红烧,七成熟时再倒入一些开水,那样我们既能吃到鲜美的鱼肉与泥鳅,还能喝上热乎乎的下饭的鱼汤。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父亲的渔网为我们补充了足量的营养。
父母已经离开人间了。父亲母亲,如果想念真的有声音,你们一定听得见吧,一阵吹过麦田的晚风,一抹晚霞里飞过的麻雀,一场缱绻眷恋的夜雨,一汪月光下哗哗流淌的河水,都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思念。
寒冬时节,大地一片萧条,水中的泥鳅似乎都藏在淤泥里冬眠,踪迹难觅。
有一年寒假,我在大舅舅妈家待些日子。每天吃午饭时,大舅总喜欢喝点小酒。一天上午,大舅要表哥小牛到田地里去挖点泥鳅做佐酒的菜肴。天寒地冻,表哥小牛很不乐意,可他又慑于父亲的威严,于是约上我一同出去挖泥鳅,心中闷闷不乐。
我俩来到一块已经没有水,可泥土潮湿的田地里,几锹下去,便挖出一条藏在泥土里的泥鳅。它一动不动,拿到手上也是冰凉的。挖了一片,小牛表哥就挖出几十条泥鳅,来时的愁容不见了,满脸全是喜悦。回到家中,舅妈将泥鳅收拾好,做了小半锅泥鳅炖挂面。自然,那天大舅的酒喝得很开心,我们也吃上了平常冬天难以吃到的美食。
校园民谣《捉泥鳅》这样唱道:“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每每唱着这首歌,我就想起二十八岁就离开人间的小牛表哥。他曾经那么年轻力壮,那么朝气蓬勃,可人世间太多的苦楚、太多的不如意还是压垮了他的精神,并匆匆收走了他青春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