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谈诺奖听水浒写家乡

作家陈家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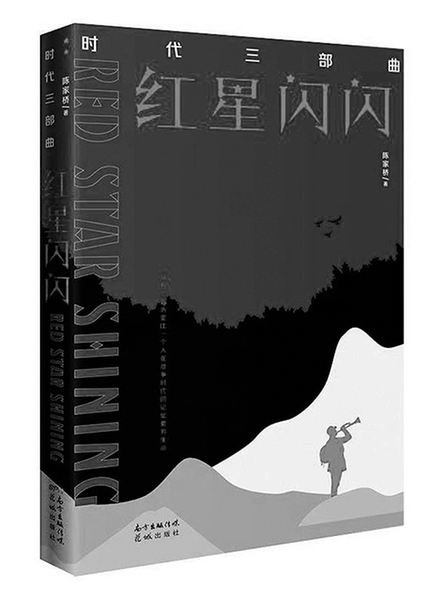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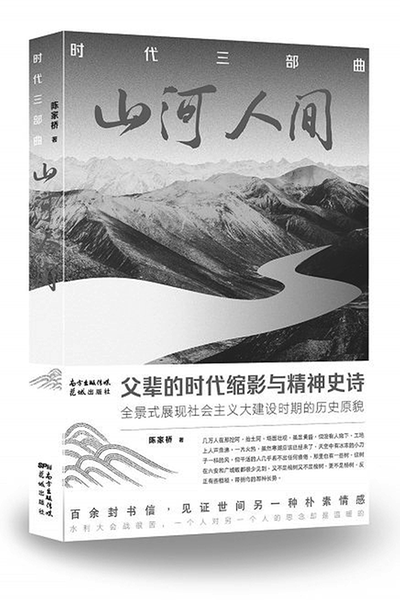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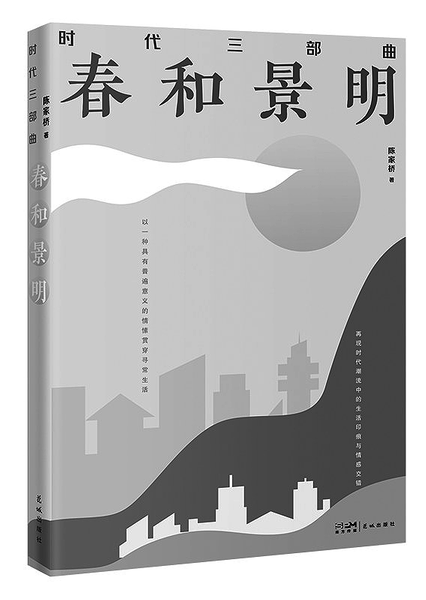
◎我想学习经典的东西,并不是别的,正是从这些已有的被检验为特别重要的经验上,你拿到了一种在世界上足以立身的技术支撑,你才能去处理你的文化,你的主题,以及你的故事。
◎我想,《活着》的流行与反复的被强调,本身也会包含有太多的文学受众的“症结”和“问题”。
◎在《山河人间》中,我甚至写到了父亲的青春,我想正是对于“个人史”的小说书写,我们才能抵达记忆中的乡土。
阅读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年底的时候,媒体记者来采访,让谈一下个人2023年的阅读印象,要我谈一本印象最深的书。这个问题很难答,我谈了2023年诺贝尔奖得主约恩·福瑟的戏剧集《有人将至》。其实我对这位作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每年对于诺贝尔奖,确实又是关注的。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媒介的发达,特别是当下自媒体的崛起,很多有关文学的议题会被放大,进而有了一种虚张声势式的文学氛围感。但是,这二十年来的诺奖,确实有几点是让人感到有些奇特的。比如诺奖颁给了唱歌的鲍伯·迪伦,又比如颁给了多位法国作家,包括克莱齐奥,埃尔诺,还有莫迪亚诺,当然英国相关的作家也不少,比如莱辛,比如石黑一雄,又比如有英国背景的古尔纳,当然欧洲作家中的帕慕克,还有赫塔·米勒,耶利内克,品特等等。相较而言,对于亚洲和拉美作家就较少了,在世纪初有几位非常重要的获奖者,比如库切、奈保尔以及上个世纪末的格拉斯。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新一代小说家的写作风向。
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是有些刻意地留心近二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坦率说,我认为除了少数几位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大师,其余的未必有深远的艰巨的影响。小说仍然处于一种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但这种不确定,并非是主观上的或是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内在的标准的缺乏,这种内在的隐形的标准始终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一直难以被完成,因而我几乎每年在记者采访时,我都会说,诺贝尔奖有时确实是一再地偏离文学应该有的那种样子。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在媒介、批评、翻译、文化等多重维度的交织中,会有人能找到一个所谓的公正尺度去评价作品,往往偏离、固执,甚至是错误,也是文学传播和批评的必然后果之一。
中国作家在走出去的问题上,始终是有一点特殊性的,我们引进了许多包括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作品在内的大量图书,但我们的书翻译推广出去的很少,在国外是很少能见到摆在显眼位置的中国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不关注中国小说或者中国文本。在日本汉学家饭冢容提供的一份日本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极其重视,做到了对每一年度具体作品及其内涵的研究和标识。在2001年的年度报告中,我发现他是把那一年中国文学的年度主题确定为“描写婚姻家庭伦理的新问题”,引用的是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夫妻记》。由此可见,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极其认真而细致的。
我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过一次报告,名叫《西方经典小说观察》,时间是2009年,那时我三十七岁,当时的听众中有许多年老的文学爱好者,反响非常热烈,对于经典作品,其实是不分国界,不分语种的。比如卡夫卡,比如乔伊斯,这些重要作家的代表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我的写作也正是从这些作品中学到了一些重要的方法,在小说创作上,如果没有这些伟大作家带来的启迪,你是很难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因此,我想学习经典的东西,并不是别的,正是从这些已有的被检验为特别重要的经验上,你拿到了一种在世界上足以立身的技术支撑,你才能去处理你的文化,你的主题,以及你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我有时在想,我到底读了多少本小说,我指的是完整地读完它每一个字的小说,我经常数这个数字,回忆这个数字。有时会很累,但我想我至少是理清楚了,比如英国有什么重要的作家,法国有谁,美国有谁,俄罗斯有谁,日本有谁,拉美有谁,东欧有谁,这样一捋下来,你会发现,世界虽然无比广大,但站在世界顶尖位置的作家仍然是有限的。
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先天没有那种陌生性
去年秋季,因为意外摔伤了脚踝,骨折,只能躺下来休息,听了一段时间的评书,尤其是《水浒传》,相当的有意思,特别是关于武松、宋江以及林冲等人物的塑造,从评书来听,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跟中国古代叙事者之间的很难言明的对话关系,我也因而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在小说上并不太强,可能也源于我们始终缺乏一种通过虚构及想象来建立一个世界的强大冲动,我们的现实性很强,我们的文化、人际、历史、环境乃至地理、民俗,都具有一种强大的托承的力量。
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先天没有那种陌生性,甚至也缺乏它该有的那种“纸上历史”的力量。我父亲特别喜欢《水浒》,但在我小时候,他就反对我看《水浒》,后来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看到那种人所挟有的某种破坏性的力量,后来我自己看《水浒》,包括听《水浒》,我也是觉得《水浒》严重类型化了人物,《红楼梦》也在草蛇灰线的同时,过于预设了人的命运,这些因素往往又是反小说的,所以写得多,读得多,有时又会迷失在某种“不可知”中。
近年,我又读了鲁迅,自然是觉得非常好,我坚定地赞同五百年来只有一个鲁迅的说法。但我在读《狂人日记》时,我又会想到卡夫卡的《判决》,同样是关于人的被挤压,被禁锢的状态,在东西方,差不多二十世纪一○年代,两位大师同时触及了相同的主题,我甚至想问一下我在北大复旦的朋友,他们了解文学翻译,不知在东西方关于同样的主题,是否有布罗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
冯唐在一次视频中谈到余华的《活着》,他说他认为那是一部不太好的小说,因为里面太多的苦难发生在同一个家庭,这缺少一种现实的真实。我听了很受震动,我觉得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跟我也提到一个关于《许三观卖血记》的问题。她的意思是,为什么写了一种人在饥饿状态下的苦,那就是好的命运书写?我想,《活着》的流行与反复的被强调,本身也会包含有太多的文学受众的“症结”和“问题”。
阅读是一个人接触广大深邃的知识世界的方式之一,但阅读不能取代生活本身,个人的历史不是由阅读完成的,甚至阅读本身是对个人历史的一个破坏,个人历史应该是由生活,是由感受以及由经验来构成的。也因此,行走变得非常的必要,但近十年来,我很少远行,世界在小说的对照下,正在历史化。我想我是在抽象这个世界,这反而是要改变的。人本身已经接近于知识了,不再是一种进取,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认识和判断,人成了时间的刻度,成了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个性化的标识,这是小说带来的,是故事带来的。同时也是值得反思的。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把视线拉回了故乡
乌尔善的电影《封神》第一部出来时,我第一时间给我早年的编剧搭档邵导演去电,他的反应非常平淡,显然不认为是一部好电影,乌尔善是我早年的合作导演之一,在故事的理解上非常偏执。我和他有过无数的讨论和争执,我们曾合作过一个未遂的电影计划,名叫《胡作非为》。尽管没有拍,但故事的内核基本上就是他后来的《刀剑笑》的那些东西。
这二十年的影像文本,尤其是电影,我想某种程度上和长篇小说一样,甚至超过了长篇小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既影响了当代人,年轻人,城市人,同时也把历史风格化了,故事化了,并进一步情境化,艺术化了,我2004年出版了《爱情三部曲》,我的导演朋友邵,一直讲他想把《北京爱情》改成一部大电影,但我缺少这样的动力,我还是认为电影和长篇小说,作为新世纪最重要的长篇幅文本,应该在不同的方式上,去完成它的作用。
最近几年,我陆续推出了《时代三部曲》,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把视线拉回了故乡,这三本书不是简单记录时代或书写人群,它们实际上是我对个人历史的一次重塑,从个人与故乡,从经验与感受,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交错中,重新发现自我,理解自我,进而认识自我。在《山河人间》中,我甚至写到了父亲的青春,我想正是对于“个人史”的小说书写,我们才能抵达记忆中的乡土。
陈家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