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聚焦乡村振兴谱写古镇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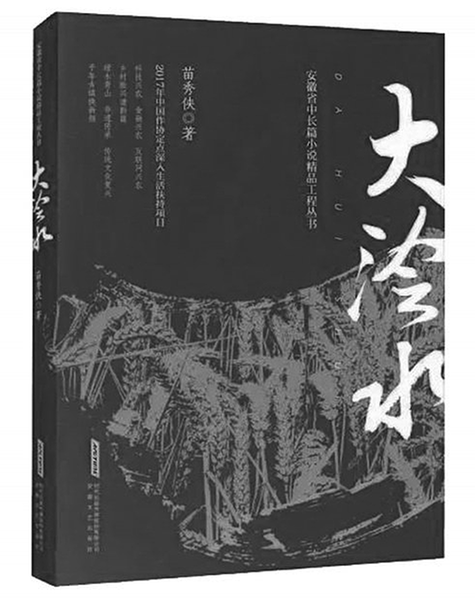
2002年苗秀侠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一篇童话,题目叫《小豌豆》,讲的是一颗小豌豆被风吹到了异乡,在知了的鼓励和帮助下忍着疼痛生长,终于又借着大风飞回了淮北平原。从小豌豆对淮北平原的依恋,我们可以见出苗秀侠对淮北平原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我想正是这份对土地的深情,使得苗秀侠的创作一直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的创作目光始终关注这片土地上的农村和农民,她的文学之根就像童话里的那颗小豌豆一样,扎根在淮北平原。
苗秀侠的很多作品都以“庄稼”为名,早年的《遍地庄稼》,开启了她书写乡村的序幕,小说借棉花、高粱、红芋、麦子四种庄稼,写出了乡野间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对上世纪70-80年代北方农村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有着非常细致的刻画。报告文学《迷惘的庄稼》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长篇小说《农民工》和《农民的眼睛》,则是从农民工在城市的迷惘和乡村的凋敝两个侧面来反映改革开放后“乡村空了”这一现象,长篇小说《皖北大地》是农民回归乡村建设家园的真实呈现。炽热的乡土情怀决定了作家的创作方向,苗秀侠对农村题材的深耕正像农民对土地的深耕一样,春种秋收,从早年的“遍地庄稼”到今天的“大浍水”,苗秀侠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家园。
如果说,苗秀侠此前的创作是发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大浍水》则是试图解决之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为我们描画了乡村生活的美好愿景。如何解决“乡村空了”这个问题,《大浍水》击中了要害,那就是为返乡创业的农民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小说中的主线是陆文昌重回浍水镇,立志振兴乡村经济,通过修复浍水古镇和建设浍湾农场,打造大浍水旅游产业链,来打通乡村振兴的任督二脉。
四年前,陆文昌贪功冒进,开发商利欲熏心,留下了浍水镇古建筑被毁损、浍水河被污染、浍山被炸掉半边的烂摊子,也害得两位发小夏小荷、嵇成煊破产还贷,背井离乡。陆文昌重回浍水镇,是想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当年给古镇带来的伤害,他用“不是为了官帽子”、决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态度,重新获得武汉文和两位发小企业家的支持,达成了修复古镇、生态发展的共识。
苗秀侠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明确提出了乡村经济振兴的发展思路,而且试图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苗秀侠曾在一场文学对谈中说道:“为什么农村的高楼留不住农民自己呢?这就是乡村文化的缺失,让受到城市文明洗礼的农民,不再适应乡村沉寂的日子。要改变农村现状,除了经济建设跟得上,乡村文化建设,同样要跟上,只有这样,农民回归家园,才是精神和心灵的完全皈依。”(《我的乡土写作——苗秀侠、常河对谈录》)
小说中的陆文昌是一个曾经犯过错的干部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更多地寄托了她对基层干部的期望——“不是为了官帽子”,而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苗秀侠并不回避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冒进贪功等问题,正是通过对陆文昌转变过程的细致刻画,让这一人物最终重新得到浍水镇群众的信任,完成了救赎。小说也通过陆文昌与村民们的关系表达了对干群关系的理解,良好干群关系的情感基础是“以心换心”。干部只有耐心地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是作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能体察到的。
在艺术形式上,作家选取浍水镇的两个文化符号——灵石和淮北大鼓,在小说中巧妙穿插,既拓展了小说的诗性空间,又使小说具有了音乐美感。灵石曾是编钟上的一颗磬石。灵璧石“黑亮如漆,石质细腻柔滑,叩之有声,音韵悦耳动听,为石中之珍品”。千年灵石千年回响,来自千年灵石的玉振金声既具有历史感,又使得叙事更加灵动跳脱。
小说每章的开头都有一段淮北大鼓,放在每一章开头的这段鼓词有点类似于大鼓书的书帽,书帽在大鼓书的演出中主要起到吸引听众注意力、调节演出气氛的作用。作家把这个形式移植到小说中,从内容上看,有的段落起到提示情节的作用,有的则是营造氛围,小说最后一章“开街”中的一段淮北大鼓是“历史纲鉴”,对自古以来的圣贤的歌颂营造了开街的喜庆气氛,同时也寓意着浍水镇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
“乡村振兴谱新篇,千年古镇焕新颜”,为了讲好故事,写活人物,苗秀侠深入基层,多次走进乡村,去倾听,去探寻,去发现,《大浍水》体现了作家务实求真的创作态度和责任担当,这部作品也是乡村振兴主题创作的成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