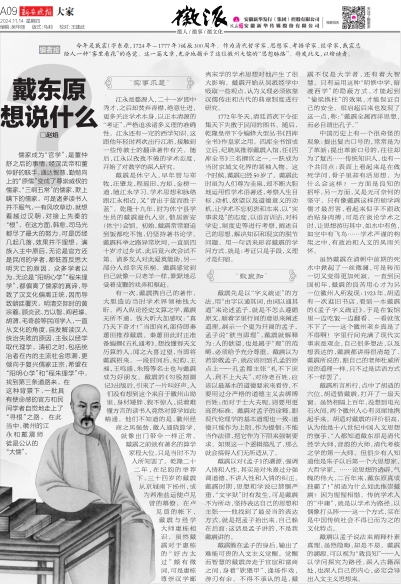发布日期:
戴东原想说什么
儒家成为“官学”,是董仲舒之后的事情,经汉武帝和董仲舒的联手,通达智慧、勤勉向上的“原儒”变成了尊崇威权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欺上瞒下的儒家。可是诸多读书人并不服气,一有风吹草动,就想着越过汉朝,对接上先秦的“根”。在这方面,韩愈、司马光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历经几起几落,效果并不理想。满族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学者,都低首反思大明灭亡的原因。众多学者以为,无论是“阳明心学”“程朱理学”,都偏离了儒家的真谛,导致了汉文化偏离正统,因而导致朝廷覆灭。明清交际时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民间学人,一直从文化的角度,自发解读汉人统治失败的原因,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清初之时,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主流社会思潮,更倾向于复兴儒家正宗,希望在“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来。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具有使命感的官方和民间学者自觉地走上了“寻根”之路。在此当中,徽州的江永和戴震师徒是公认的“大儒”。
“实事求是”
江永是婺源人,二十一岁即中秀才,之后却焚弃青襟,绝意仕进,更多关注学术本身,以正本清源的“考证”,严格追求诸多义理的准确性。江永还有一定的西学知识,这跟他年轻时两次出行江浙,接触到一些传教士的翻译著作有关。随后,江永以孜孜不倦的学术态度,开始了对数学的深入研究。
戴震是休宁人,早年曾与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一道,随江永学习,学术思想和脉络跟江永相近,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乾隆十九年,时为休宁县学生员的戴震避仇入京,借居新安(休宁)会馆。初始,戴震常常窘迫到饭都吃不饱,仍坚持著书论学。戴震科举之路异常坎坷,一直到四十岁才过乡试,此后竟六次会试不第。诸多友人对此爱莫能助,另一部分人却幸灾乐祸。戴震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老羊一样,默默地忍受着皮鞭的戏弄和驱赶。
有一次,戴震携自己的著作,大胆造访当时学术界领袖钱大昕。两人纵论经史文算之学,戴震无所不通。钱大昕大加感叹:“真乃天下奇才!”当即向礼部侍郎秦蕙田推荐戴震。秦蕙田此时正准备编撰《五礼通考》,想找懂得天文历算的人,闻之大喜过望,当即将戴震招来。一段时间后,纪昀、王昶、王鸣盛、朱筠等名士也与戴震成为好朋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出版后,引来了一片叫好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于徽州山坳里,身材矮胖、貌不惊人、说着难懂方言的读书人竟然对算学如此精通。他们不知道的是,徽州经商之风强劲,徽人通晓算学,就像出门带伞一样正常。戴震之前就有著名的算学家程大位,只是当时不为人所知罢了。乾隆二十二年,在纪昀的举荐下,三十四岁的戴震从京城南下扬州,成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僚。在卢见曾的帐下,戴震与经学大师惠栋相识。虽然戴震对于惠栋的“好古太过”颇有微词,可是惠栋尊崇汉学鄙夷宋学的学术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开始从吴派经学中吸取一些观点,认为义理必须依靠汉儒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研究。
1772年冬天,清廷首次下令征集天下失散于民间的图书。随后,乾隆皇帝下令编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作皇家之用。四库全书馆成立后,纪晓岚推荐戴震入馆,任《四库全书》三名撰官之一,一跃成为当时京城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这个时候,戴震已经50岁了。戴震此时虽为人们尊为圭臬,却不断大胆地运用哲学术语著述,考察人生目标、动机、欲望以及道德意义的动机,让学术不忘初衷和本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语言训诂,对科学史、制度史等进行考察,阐述自己的思想,解决知识和现实的脱节问题。用一句话来形容戴震的学问方式,就是:考证只是手段,义理才是归宿。
“致良知”
戴震先是以“字义疏证”的方法,用“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来论述孟子,就是不怎么遵循原文,顺着字里行间的意思来阐述道理,展示一个更为开阔的孟子。孟子说“欲当即理”,戴震就解释为:人的欲望,也是属于“理”的范畴,必须给予充分尊重。戴震以为若崇敬孟子,就应该回到孔孟的原点上——孔孟都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待老百姓,应该以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来看待,不要用过分严格的道德主义去绑缚百姓;而对于士大夫呢,则要用更高的标准。戴震对孟子的诠释,跟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道理也一致:道德只能作为上限,作为提倡;不能当作法律,把它作为下限来强制要求。如果这一个逻辑搞乱了,那么就会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了。
戴震以对《孟子》的溯源,强调人情和人性,其实是对朱熹过分强调道德、不讲人性和人情的纠正。戴震时期,思想和学说已禁锢严重,“文字狱”时有发生,可是戴震不为所动,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找到了最妥当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孟子抬出来,自己躲在后面:这话是孟子讲的,不是我戴震讲的。
戴震躲在孟子的身后,输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觉醒。觉醒而智慧的戴震奔走于官宦和富商之间,身着“软猥甲”,逢场作戏,游刃有余。不得不承认的是,戴震不仅是大学者,还有着大智慧。只有运用这种“明修中学,暗渡西学”的隐蔽方式,才能起到“偷梁换柱”的效果,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梁启超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称:“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出复古口号的,常常是为了革新;提出革新口号的,往往却为了复古……传统知识人,也有一个共同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死学问,骨子里却有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良知的招呼,另一方面,又是无可奈何的坚守。只有像戴震这样的硕学鸿儒才最厉害,看起来似乎不跟政治贴身肉搏,可是在谈论学术之时,让思想游历其中,如水中有鱼,如空中有飞鸟……学术严谨的构架之中,有政治和人文的风雨关怀。
虽然戴震在清朝中前期的死水中掀起了一丝微澜,可是转而一切又变得更加死寂。一直到民国初年,戴震的良苦用心才为另一位徽州人所发现:1923年,胡适有一次逛旧书店,看到一本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于是在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翻看。一看就放不下了——这个徽州老乡真是了不得啊!字里行间充满了现代实事求是观念,自己很多想法,以及想表达的,戴震都讲得很清楚了。戴震所说的,跟自己的老师杜威所说的道理一样,只不过是话语方式不一样罢了。
戴震所言所行,点中了胡适的穴位,胡适借戴震,打开了一扇天窗。虽然相隔上百年,没想到电光石火间,两个徽州人心有灵犀地携起手来。胡适对戴震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十八世纪中国人文思想的旗手,“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戴震?因为惺惺相惜。传统学术人的“中庸”,就是以学术为路径,以偶像打头阵——这一个方式,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特点。
戴震以孟子说法来阐释朴素真理,虽然隐晦,却是不易。戴震的溯源,可以视为“致良知”——人以学问探究为路径,深入古籍深处,也深入自己的内心,必定会导出人文主义思想来。
“实事求是”
江永是婺源人,二十一岁即中秀才,之后却焚弃青襟,绝意仕进,更多关注学术本身,以正本清源的“考证”,严格追求诸多义理的准确性。江永还有一定的西学知识,这跟他年轻时两次出行江浙,接触到一些传教士的翻译著作有关。随后,江永以孜孜不倦的学术态度,开始了对数学的深入研究。
戴震是休宁人,早年曾与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一道,随江永学习,学术思想和脉络跟江永相近,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乾隆十九年,时为休宁县学生员的戴震避仇入京,借居新安(休宁)会馆。初始,戴震常常窘迫到饭都吃不饱,仍坚持著书论学。戴震科举之路异常坎坷,一直到四十岁才过乡试,此后竟六次会试不第。诸多友人对此爱莫能助,另一部分人却幸灾乐祸。戴震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老羊一样,默默地忍受着皮鞭的戏弄和驱赶。
有一次,戴震携自己的著作,大胆造访当时学术界领袖钱大昕。两人纵论经史文算之学,戴震无所不通。钱大昕大加感叹:“真乃天下奇才!”当即向礼部侍郎秦蕙田推荐戴震。秦蕙田此时正准备编撰《五礼通考》,想找懂得天文历算的人,闻之大喜过望,当即将戴震招来。一段时间后,纪昀、王昶、王鸣盛、朱筠等名士也与戴震成为好朋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出版后,引来了一片叫好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于徽州山坳里,身材矮胖、貌不惊人、说着难懂方言的读书人竟然对算学如此精通。他们不知道的是,徽州经商之风强劲,徽人通晓算学,就像出门带伞一样正常。戴震之前就有著名的算学家程大位,只是当时不为人所知罢了。乾隆二十二年,在纪昀的举荐下,三十四岁的戴震从京城南下扬州,成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僚。在卢见曾的帐下,戴震与经学大师惠栋相识。虽然戴震对于惠栋的“好古太过”颇有微词,可是惠栋尊崇汉学鄙夷宋学的学术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开始从吴派经学中吸取一些观点,认为义理必须依靠汉儒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研究。
1772年冬天,清廷首次下令征集天下失散于民间的图书。随后,乾隆皇帝下令编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作皇家之用。四库全书馆成立后,纪晓岚推荐戴震入馆,任《四库全书》三名撰官之一,一跃成为当时京城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这个时候,戴震已经50岁了。戴震此时虽为人们尊为圭臬,却不断大胆地运用哲学术语著述,考察人生目标、动机、欲望以及道德意义的动机,让学术不忘初衷和本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语言训诂,对科学史、制度史等进行考察,阐述自己的思想,解决知识和现实的脱节问题。用一句话来形容戴震的学问方式,就是:考证只是手段,义理才是归宿。
“致良知”
戴震先是以“字义疏证”的方法,用“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来论述孟子,就是不怎么遵循原文,顺着字里行间的意思来阐述道理,展示一个更为开阔的孟子。孟子说“欲当即理”,戴震就解释为:人的欲望,也是属于“理”的范畴,必须给予充分尊重。戴震以为若崇敬孟子,就应该回到孔孟的原点上——孔孟都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待老百姓,应该以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来看待,不要用过分严格的道德主义去绑缚百姓;而对于士大夫呢,则要用更高的标准。戴震对孟子的诠释,跟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道理也一致:道德只能作为上限,作为提倡;不能当作法律,把它作为下限来强制要求。如果这一个逻辑搞乱了,那么就会搞得人们无所适从了。
戴震以对《孟子》的溯源,强调人情和人性,其实是对朱熹过分强调道德、不讲人性和人情的纠正。戴震时期,思想和学说已禁锢严重,“文字狱”时有发生,可是戴震不为所动,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找到了最妥当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孟子抬出来,自己躲在后面:这话是孟子讲的,不是我戴震讲的。
戴震躲在孟子的身后,输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觉醒。觉醒而智慧的戴震奔走于官宦和富商之间,身着“软猥甲”,逢场作戏,游刃有余。不得不承认的是,戴震不仅是大学者,还有着大智慧。只有运用这种“明修中学,暗渡西学”的隐蔽方式,才能起到“偷梁换柱”的效果,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梁启超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称:“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出复古口号的,常常是为了革新;提出革新口号的,往往却为了复古……传统知识人,也有一个共同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死学问,骨子里却有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良知的招呼,另一方面,又是无可奈何的坚守。只有像戴震这样的硕学鸿儒才最厉害,看起来似乎不跟政治贴身肉搏,可是在谈论学术之时,让思想游历其中,如水中有鱼,如空中有飞鸟……学术严谨的构架之中,有政治和人文的风雨关怀。
虽然戴震在清朝中前期的死水中掀起了一丝微澜,可是转而一切又变得更加死寂。一直到民国初年,戴震的良苦用心才为另一位徽州人所发现:1923年,胡适有一次逛旧书店,看到一本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于是在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翻看。一看就放不下了——这个徽州老乡真是了不得啊!字里行间充满了现代实事求是观念,自己很多想法,以及想表达的,戴震都讲得很清楚了。戴震所说的,跟自己的老师杜威所说的道理一样,只不过是话语方式不一样罢了。
戴震所言所行,点中了胡适的穴位,胡适借戴震,打开了一扇天窗。虽然相隔上百年,没想到电光石火间,两个徽州人心有灵犀地携起手来。胡适对戴震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十八世纪中国人文思想的旗手,“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胡适为什么如此推崇戴震?因为惺惺相惜。传统学术人的“中庸”,就是以学术为路径,以偶像打头阵——这一个方式,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特点。
戴震以孟子说法来阐释朴素真理,虽然隐晦,却是不易。戴震的溯源,可以视为“致良知”——人以学问探究为路径,深入古籍深处,也深入自己的内心,必定会导出人文主义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