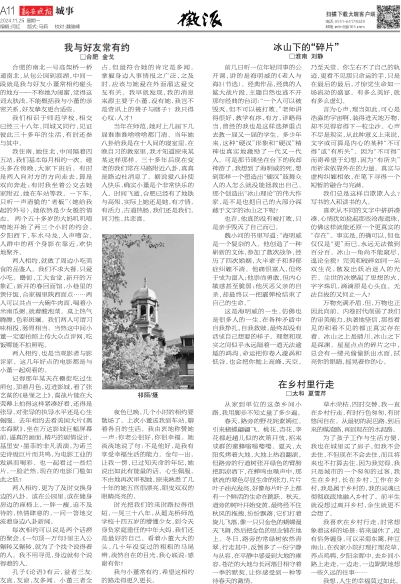发布日期:
我与好友常有约
合肥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一桥通南北,从包公园到滨湖,中间一段就是我与好友小董常相约碰头的地方——不称她为闺蜜,觉得这词太肤浅,不能概括我与小董的亲密关系,好友挚友更合适些。
我们相识于师范学校,相交已经三十八年,同城又同行,见证彼此三十多年的生活,有时还参与其中。
我住南,她住北,中间隔着四五站,我们基本每月相约一次。碰头多在傍晚,大家下班后。有时是两人向对方的方向走去,算是双向奔赴;有时我坐着公交去她家附近,她在车站等我。一下车,只听一声清脆的“老板”(她给我起的外号),她依然是少女般的情态。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叽叽喳喳地开始了两三个小时的约会。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人声嘈杂,人群中的两个身影在靠近,欢快地聚齐。
两人相约,就做了周边小吃美食的品鉴人。我们不求大餐,只爱小吃。罍街,工大食堂,新开的万象汇;新开的春回面馆,小巷里的煲仔饭,合家福里陕西面点……两人可以共点一大碗牛肉面,喝着小米南瓜粥,就着酸泡菜。桌上热气腾腾,色彩斑斓。我们两人可谓习味相投,肠胃相当。当然这中间小董一定要拍照上传大众点评网,吃饭哪能不拍照呢。
两人相约,也是当观影者与影评家。这几年好点的电影都是与小董一起观看的。
记得那年某天在罍街吃过生煎包,顶着月色,迈进影城,看了张艺谋的《悬崖之上》,谍战片能在大荧幕上拍得这样紧凑好看,还得是张导,对张导的执导水平还是心生佩服。去年相约去看美国大片《奥本海默》,坐在万达影城巨幅屏幕前,逼真的画面,精巧的剧情设计,基里安·墨菲的非凡表演,为诺兰史诗级巨片而共鸣,为电影工业的发展而喝彩。也一起看过一些烂片,一脸茫然,现在的电影门槛如此之低?
两人相约,更为了及时交换身边的八卦。或在公园里,或在健身房边的座椅上,一胖一瘦,迫不及待的,热情肆意的,一问一答地交流着身边八卦新闻。
每次相约可以说是两个话痨的聚会。《一句顶一万句》里主人公辗转又辗转,就为了个找个说得着的人。我不用寻觅,身边就有个说得着的人。
孔子《论语》有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小董三者全占,但最符合她的肯定是多闻。掌握身边人事情报之广泛、之及时,应该与她爱在外面溜达爱交友有关。我早就发现,我的消息来源主要于小董,没有她,我岂不是资讯上的聋子与瞎子?我只得心叹:人才!
当年在师范,她对上几届下几届谁谁谁啥啥啥都门清。当年她八卦给我是在十人间的寝室里,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我才知道原来某某这样那样。三十多年后现在变老的我们常在马路附近八卦,真真是路边社消息了。据说爱八卦使人快乐,确实小董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时间飞逝,合肥已经有了地铁与高架,实际上她还是她,有才情,有活力,古道热肠,我们还是我们,同习性,共悲喜。
夜色已晚,几个小时的相约要散场了。上次小董送我到车站,聊着各自的生活。我由衷地称赞她一声:你老公很好,你很幸福。她淡淡地说了句:不是他好,是我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能力。金句一出,让我一愣,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她说出如此有能量的话。心生佩服,不由地再次审视她,原来熟悉了几十年的她五官很漂亮,眼皮双双的眼睛亮亮的。
时光把我们的来时路拉得很短,一晃三十八年,从廻龙桥师范学校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女,到今天身负家庭重任的中年大妈,我们还是最好的自己。看着小董大大的头,几十年没变过的粗粗的马尾辫,淡然自在的目光,我心底说:感谢有你!
我与小董常有约,希望这相约的路走得更久更长。
我们相识于师范学校,相交已经三十八年,同城又同行,见证彼此三十多年的生活,有时还参与其中。
我住南,她住北,中间隔着四五站,我们基本每月相约一次。碰头多在傍晚,大家下班后。有时是两人向对方的方向走去,算是双向奔赴;有时我坐着公交去她家附近,她在车站等我。一下车,只听一声清脆的“老板”(她给我起的外号),她依然是少女般的情态。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叽叽喳喳地开始了两三个小时的约会。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人声嘈杂,人群中的两个身影在靠近,欢快地聚齐。
两人相约,就做了周边小吃美食的品鉴人。我们不求大餐,只爱小吃。罍街,工大食堂,新开的万象汇;新开的春回面馆,小巷里的煲仔饭,合家福里陕西面点……两人可以共点一大碗牛肉面,喝着小米南瓜粥,就着酸泡菜。桌上热气腾腾,色彩斑斓。我们两人可谓习味相投,肠胃相当。当然这中间小董一定要拍照上传大众点评网,吃饭哪能不拍照呢。
两人相约,也是当观影者与影评家。这几年好点的电影都是与小董一起观看的。
记得那年某天在罍街吃过生煎包,顶着月色,迈进影城,看了张艺谋的《悬崖之上》,谍战片能在大荧幕上拍得这样紧凑好看,还得是张导,对张导的执导水平还是心生佩服。去年相约去看美国大片《奥本海默》,坐在万达影城巨幅屏幕前,逼真的画面,精巧的剧情设计,基里安·墨菲的非凡表演,为诺兰史诗级巨片而共鸣,为电影工业的发展而喝彩。也一起看过一些烂片,一脸茫然,现在的电影门槛如此之低?
两人相约,更为了及时交换身边的八卦。或在公园里,或在健身房边的座椅上,一胖一瘦,迫不及待的,热情肆意的,一问一答地交流着身边八卦新闻。
每次相约可以说是两个话痨的聚会。《一句顶一万句》里主人公辗转又辗转,就为了个找个说得着的人。我不用寻觅,身边就有个说得着的人。
孔子《论语》有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小董三者全占,但最符合她的肯定是多闻。掌握身边人事情报之广泛、之及时,应该与她爱在外面溜达爱交友有关。我早就发现,我的消息来源主要于小董,没有她,我岂不是资讯上的聋子与瞎子?我只得心叹:人才!
当年在师范,她对上几届下几届谁谁谁啥啥啥都门清。当年她八卦给我是在十人间的寝室里,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我才知道原来某某这样那样。三十多年后现在变老的我们常在马路附近八卦,真真是路边社消息了。据说爱八卦使人快乐,确实小董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时间飞逝,合肥已经有了地铁与高架,实际上她还是她,有才情,有活力,古道热肠,我们还是我们,同习性,共悲喜。
夜色已晚,几个小时的相约要散场了。上次小董送我到车站,聊着各自的生活。我由衷地称赞她一声:你老公很好,你很幸福。她淡淡地说了句:不是他好,是我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能力。金句一出,让我一愣,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她说出如此有能量的话。心生佩服,不由地再次审视她,原来熟悉了几十年的她五官很漂亮,眼皮双双的眼睛亮亮的。
时光把我们的来时路拉得很短,一晃三十八年,从廻龙桥师范学校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女,到今天身负家庭重任的中年大妈,我们还是最好的自己。看着小董大大的头,几十年没变过的粗粗的马尾辫,淡然自在的目光,我心底说:感谢有你!
我与小董常有约,希望这相约的路走得更久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