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潘军:先锋,是一种文学探索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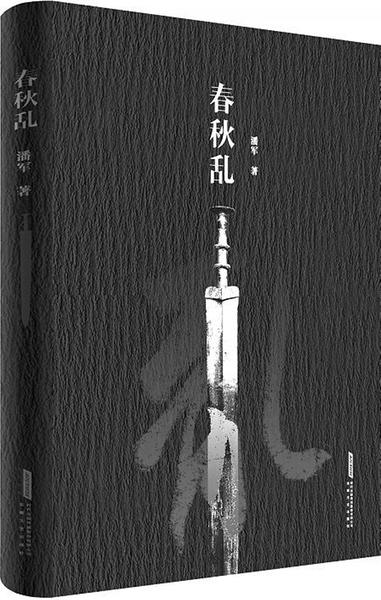

霸王别姬、赵氏孤儿和荆轲刺秦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潘军的强力阅读之后,被解构又重构,以一家之言和自圆其说的基本原则成了三个有意味的中篇。既而以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的名义集结为“失败的英雄故事”,历时24年,成为眼前的这本《春秋乱》。在《春秋乱》全国首发式上,潘军称是用自认为合适的弹性的形式重塑具有弹性空间的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做了想做的事,就像爱了想爱的人——同样在他看来,除了这两件事,人生没有第三件事了。
模糊的边界中再造叙事空间
徽派:霸王像个诗人,程婴培养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荆轲把自己变成刺入历史视野的匕首,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重构?
潘军:如果历史上对这个界定很清晰,佐证很详细,我觉得我不会去打它的主意,去触碰它。除了《春秋乱》中间的赵氏孤儿、荆轲刺秦和楚汉争霸,我还写了《断桥》,《断桥》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它已经到了神话层面了,和史实的层面永远是有一种距离感。面对所谓的历史小说,我关注的都是那些界限模糊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比如程婴、公孙杵臼甚至屠岸贾,这种人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过都不好说,可能就是某一个人最早的一次虚构,包括荆轲,他毕竟不是像曹操那样确有其人。所以在一个创作者这边,它实际上是要经过自己的过滤和细分的。这些说明了我对历史的一种基本立场就是:材料很详尽确有其事的东西,还是要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去维护它的基本史实;只有在具有一种弹性的、模糊的、缺乏边界感的史实面前,你才有可能有再造的空间。
徽派:英雄,某种程度上都被解构甚至重塑了。
潘军:有评论家说我写的是英雄,要是准确一点的话,还可以加三个字,写的都是“失败的英雄”。传统的《赵氏孤儿》中程婴没有失败,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仇已报一雪前耻,阖家团圆。但是我好像从少年开始,对那种人生的失意者就特别同情。我不太喜欢那些成功的人士,我喜欢命运蹉跎的人、命途多舛的人,所以我笔下的程婴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好像也符合我的心思,我没想到我最后把他写成了一个失败的英雄,他付出了一切,结果塑造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后他自己疯掉了。小说的最后就是程婴在漫天飞雪中大喊,我有一个儿子,他不姓赵,他姓程,但是他的儿子已经跟朝廷承认他姓赵。
徽派:三个中篇在小说叙事的形式上很有特色,也很现代。
潘军:中国小说本土的源头,应该是追溯到明清的话本小说,另外一个源头就是俄罗斯乃至苏联文学。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发出这种感慨的人就特别多。譬如在余华的创作身上,就出现了很鲜明的向卡夫卡、川端康成致敬的东西,在莫言的作品中间也出现了很多向马尔克斯致敬的东西,那在我的创作中间呢,也出现了向博尔赫斯、塞林格致敬的东西。当这些作家都成长起来,有了一定的成就,他们突然又不约而同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说的读者问题。作者要追求小说和读者之间的共鸣,所以那个时候苏童开始写《妻妾成群》,余华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而我也写《海口日记》《合同婚姻》和《死刑报告》,这也是为了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选择。不能说他是退步了,或者他是落伍了,或者他是厌倦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诉求,就像我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写《与程婴书》和《刺秦考》,不是说我现在又想去“先锋”了,我只能说,我觉得以这种方式去表达这种题材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是合适的一种方式。
AI不会懂“流动的枯笔与飞白”
徽派:我记得您对小说有过一个比较个人的分类方式。
潘军:对。第一个是有意义的小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带有一种通俗小说层面的,比如琼瑶的小说张恨水的小说,它叫有意思的小说;第三种就是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形态,就是有意味的小说。那什么叫有意味的,真是停留在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那种层面,譬如说这孩子舞跳得很有味道,这个人的字写得很有味道,这位先生的琴拉得很有味道,你具体地让他说他真说不清楚,但是他存在。
我读鲁迅,最早是读他的思想性,包括国民性的解剖,一些前瞻的东西,后来读鲁迅,读的是他汉语言文字的表达,我觉得他的文章好看,文字本身好看,什么叫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啊,他为什么不讲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啊?为什么要这样颠来倒去地写呢?包括有时候发现了鲁迅文字中间的一种,我认为叫很拗口、晦涩的一种拗涩之美,就像笔墨中间的枯笔之美、飞白之美,有些东西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表,但是这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你不能回避的。
徽派:小说叙事解构在您这里非常重要。
潘军:我觉得一个作家对形式的敏感以及对形式的把握,某种意义上也是见证了这个作家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好作家写作是富有一种弹性的,他不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有些作品你说还好吧,也还行,但是它就是显得不高级。小说,它应该有一种很高级的状态。我有个短篇《枪,或中国盒子》,我觉得这种小说构思就很高级,所以我一直就想追求这种高级的东西。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应该对于这样的东西是很敏感的。
徽派:您觉得目前先锋文学是什么样的存在?
潘军:先锋是一种文学精神。其实这个表达也还不准确,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先锋是一种文学探索精神”。我认为现代小说一个重大的分野就是确定小说的形式,换言之就是,形式的发现是现代小说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先锋它不可能随着文学运动就消亡了,因为文学的探索会永远在。
徽派:显然AI写作在您看来根本不叫事了。
潘军:我觉得在通俗写作层面,AI替代一个写作者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是如果是特别重视感觉、感受、审美的这种创作者,AI替代不了。比如说AI写不了《刺秦考》,写不了《重瞳》,也写不了《与程婴书》,因为它是创作,而且它是有独特的形式的发现和独特的作者感受,在这之前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投喂,所以AI不可能完成,所以我认为在感觉审美层面,AI永远不会超过人类。最根本的分歧,我觉得文学或者艺术之所以被称为一种创作的劳动,还是利用了人类本身的一种智慧高度。这是机器、人工智能无法代替的,它不是像自然科学中算力的那种简单模式化模型化,“感觉”这个东西它是流动的,有的时候是瞬息万变的。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实习生储畅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