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胡竹峰:所有文章都是我的灵的灵光一现

陆青剑/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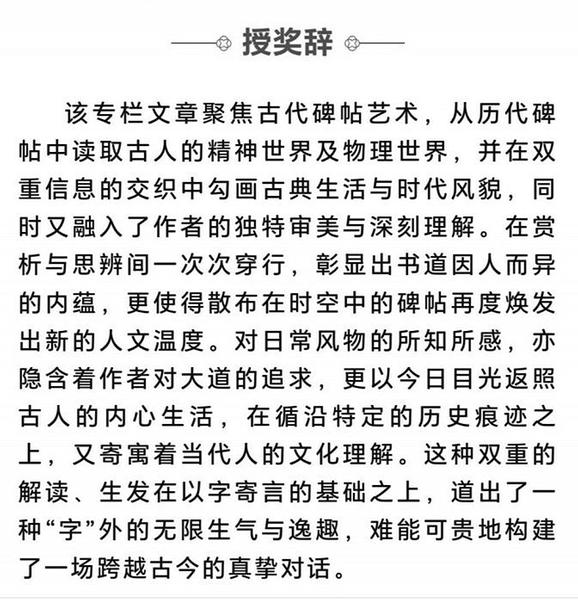
近日,第五届山花文学奖在贵州省赫章县揭晓,我省作家胡竹峰“碑帖心事”专栏获散文奖。山花文学奖旨在表彰在《山花》刊发的优秀作品,为综合性文学奖项,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文体,是国内文学界一个重要奖项。本届山花文学奖的评选范围是2022年和2023年在《山花》刊发的所有作品。
徽派:你在《山花》杂志的专栏,《兰亭序》《快雪时晴帖》《董美人碑》《上阳台帖》等中国书法史上诸多碑帖名作尽在其中,将之结集成《黑老虎集:中国碑帖之美》,勾勒二王、李白、唐寅、八大山人、金农等人的往事心神,这种写法是不是觅知音?
胡竹峰:因为读碑帖,得以进入古人的某个刹那,不敢谬托知己。但文章写出来,那些人从此就住进了我的书里,不离不弃。
徽派:这次能获奖,因为碑帖往事也是文脉传承。但碑帖往事光阴漫卷,显然你推崇烟火往事,他们的状态,乃至柴米油盐,又像是淡然从容的高手气象。你说自己没什么学问,但你却在聊“文贤”的传世神作。
胡竹峰:梁任公讲演,开场白简短,“启超没有什么学问”,接着话锋一转,轻轻点头道,“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如此自信。如此自信,可见谦逊;如此谦逊,可见自信。我差不多也是如此,有自己的信心,也有自己的谦逊。其实也是文人的一个花枪。
我写作喜欢置自己于无知,然后求知感知相知有知,这是我文章秘诀之一。写作快三十年,读书逾三十年,多少有所得。现在的见识比过去好一些,但创作力其实在下降。说来可能偏颇,文章好坏和学问关系不大。学问有无之间,下笔或许更加骀荡。学问太大了,容易堵塞才思。但做文章,要力戒不懂装懂。
徽派:古人视碑帖拓片为珍宝,金贵如虎,因用黑墨取白字,乌漆漆一团,俗称黑老虎。透过碑帖,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人风骨,更有中国古典文化沉淀下来的审美密码、生活情趣以及四时情怀。你的写碑之心和临帖之心又是什么?碑、帖两个字肯定唤起了你某种冲动。
胡竹峰:碑多一些厚重,帖多一些清逸。碑刻是古人的大事,帖则偏重日常。魏晋手帖就是朋友之间的互通讯息。十五年前的某个冬日,黄昏枯涩,看着窗外,忽有所感,从此开始读碑读帖,一读十几年,文章也陆陆续续写了十几年。
我写作主题不少,瓜果蔬菜、山川河岳、草木虫鱼、历史人物、碑帖书画,乃至民国史、饮食史,因为有些话非要通过那个载体说出来才恰当才得体才熨帖。
碑帖里有太多中国往事,将那些往事的流水流进今日的衣食住行,我能得到一种力量,文学的力量,也是艺术的力量。
徽派:你自己也写字。如今这个年纪和状态,对于笔墨和书法的理解是怎样的?
胡竹峰:笔墨落在纸上,很多心绪会落下来。读有些碑帖,能看见当年那个写字的人。我偷偷摸摸写书法,正大光明做文章。书法难寻,文章偶得。书法太难了,难在笔法,一天天一年年厮磨,迟了,懒了,时间不能倒流,我又舍不得花太多时间。
笔法贯通古人,又一笔笔是自己,谈何容易。这些年偶尔给一些报刊写过字,无非卖字营生,有朋友向我索字,从来不敢答应,因为怕唐突了一段人情。
徽派:从《兰亭序》《祭侄文稿》到《寒食帖》,你都看到了什么?心底又显影了什么?终究又能神游到什么地方?
胡竹峰:欲知详情,可以读我的《黑老虎集》。你可以买,我也可以送。
读《兰亭序》,很向往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王羲之文章也不坏,其中天道人情物理,对时间的感慨尤为惊心——“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多少人事化作了陈迹,所谓灰飞烟灭啊,岂不悲乎?
《祭侄文稿》的苍凉与正大,很有力量。我人到中年,心底开始多了苍凉,审美上追求正大。正大才能走得远。
《寒食帖》里可以看见一个逼真的苏东坡,这是烂漫到通晓天机的人物。
在我心里,这些都是天地之间一等一的人物留下来的一等一的立此存照。活在家长里短中,活在鸡毛蒜皮里,活在锅碗瓢盆之间,难免少了斯文,读文章诗词书画碑帖,和滚滚红尘隔开。人心堆满尘埃,用流水洗,用明月洗。走上大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徽派:见字如面,见字也能见史,历朝历代书法的气度也不同。同样见字也能见自己,你读字,字也读你。回头看这些碑帖往事的解读,带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它们共同表征了一个什么样的胡竹峰?
胡竹峰:我又多了一种笔法,其实一幅帖一块碑,明明白白在那里,见或者不见,写或者不写,它还是碑还是帖。我尝试用一种感觉,将碑帖转化成日常人间烟火。也有潜回,试着将笔墨凝望过去。一言以蔽之,希望写出熬更守夜、韦编三绝、费尽口舌、苦心孤诣、筚路蓝缕之后一刹那的灵光。所有文章都是我的灵光一现。
人一生很短,也很长。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都要消失,星辰也会寂灭。人生如朝露,艺术亦然。身在此岸,要栽此岸的花此岸的草,毕竟彼岸的事更云里雾里。我承认,我写了不少作品,快四十本书了。承蒙我的读者厚爱,感谢他们破费。
我希望写出更好更多的文章,这是我的痴与执。没办法,改不了了,只能将错就错,只能一往直前,只能奋不顾身。假如以后有人回望这个时代,假如我还有读者,他们会惊讶,在遥远的一百年前两百年前三百年前,那个叫胡竹峰的人居然如此丰富。其实我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将至,不管老之将至。
徽派:现在大家开口闭口就是人工智能,譬如很多工艺美术作品,面临被技术攻略的可能,也许那些笔墨中的空白和涂抹,才是人工智能最难学的灵性,哪怕是失误。
胡竹峰:桐城派姚鼐有个学生叫管同,在《禁用洋货议》中说:“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很多古人将诸多事务归于奇技淫巧,他们视人工智能或许更如此。人工智能,暂且用于艺,还是破绽太多,不足一提。未来如何,拭目以待吧。
技术革命带来太多革新,好歹不由人。就我而言,人工智能的创作取代不了我。因为写作过程自有欢喜。下棋不全是追求赢棋,钓鱼也未必只求上钩。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