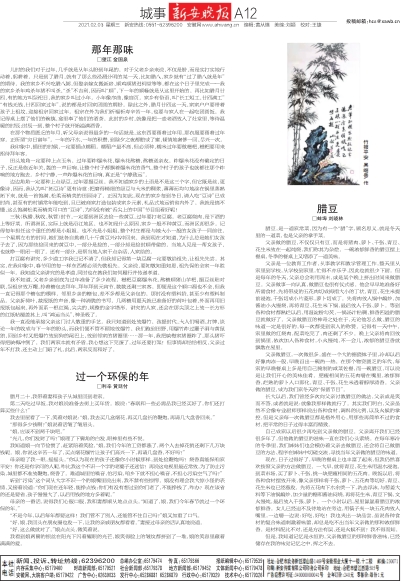发布日期:
那年那味
□望江金国泉
儿时的我们对于过年,几乎就是从年头盼到年尾的。对于父老乡亲来说,不仅是盼,而是实打实地行动着、躬耕着。只是到了腊月,就有了那么些泾渭分明的某一天,比如腊八,家乡就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期待。我的家乡不兴吃腊八粥,但娶亲嫁女搬新房、顺鸡顺猪进祠堂等等,都在这个日子里完成——我的家乡杀年鸡杀年猪不叫杀,“杀”不吉利,因而叫“顺”,下一年的顺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再比如腊月廿四,有的地方叫祭祀日,我的家乡叫过小年。小年像序曲,像扉页。家乡有俗语,叫“长工短工,廿四满工”“有钱无钱,廿四回家过年”,说的都是对回家团圆的期盼。除此之外,腊月廿四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带着孩子上祖坟,迎接祖宗回家过年。祖宗在外为我们祈福祈寿辛苦一年,也要与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我记得桌上摆了他们的碗筷,龛里奉了他们的酒茶。此时的乡村,就像是把一壶老酒放入了灶堂里,等待温暖的时辰;时辰一到,整个村子就开始溢满酒香。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听父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东西要留着过年用,那衣服要留着过年穿。正所谓“穷日富年”。一年的汗水、一年的积攒,到除夕之夜都酿成了蜜,倾情地奢侈一回、尽兴一次。
我印象中,插田的时候,一定要插点糯稻。糯稻产量不高,但必须种,糯米过年要做糍粑,糍粑要用来招待拜年客。
田头地角一定要种上点玉米。过年要炸爆米花,爆米花熬糖,熬糖送亲友。炸爆米花没有确定的日子,反正是临近年关,轰的一声巨响,让整个村子都飘着爆米花的香气,整个村子的孩子也就都往那个炸响的地方跑去。乡村宁静,一声炸爆米花的巨响,真正是“宁静致远”。
边边角角一定要种上点绿豆,过年要搨豆丝。我不知道家乡的土语是不是这三个字,但它既是丝,更像诗,因而,我认为叫“拓豆诗”更有诗意:把磨得精细的绿豆与大米的稠浆,薄薄而均匀地涂在锅里蒸熟拓下来,就是一首饱满、松柔而精美的田园诗了。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家乡每到冬日,请人吃“豆诗”已成时尚,甚至有的村镇常年能吃到,且已被商家打造包装成家乡元素,礼品式地远销省内外了。我就是搞不懂,这么饱满松柔而精美可口的“豆诗”,为何没有被“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组看好呢!
三秋(秋播、秋收、秋管)时节,一定要到洲区去捡一些黄豆,过年要打老豆腐。老豆腐烧肉,是下酒的上等好菜。所谓洲区,实际上就是沿江地区。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家乡一般不种黄豆,而洲区却很多。记得每年担任这个重任的都是小姐姐。也不光是小姐姐,整个村庄都是与她大小一般的女孩子一同前往。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她们就各自挑着几十斤黄豆兴冲冲回来。我到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总是她们女孩子去了,因为那些捡回来的黄豆中,一部分是捡的,一部分却是捡时顺带偷的。当地人见是一帮女孩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还有一部分,是帮当地人家干点杂活,人家给的。
打豆腐有讲究,多少道工序我已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第一块豆腐一定要敬给祖先,让祖先先尝。其实,在我印象中,春节用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先敬祖先。父亲说,要知敬知重知恩,祖先保佑全家一年胜似一年。我知道父亲讲究的是孝道,同时也在教我们如何履行并传递孝道。
我不知道,父老乡亲到底为过年准备了多少流程。糍粑豆腐爆米花,熬糖顺猪山芋粑,搨豆丝贴对联,祭祖宗放万鞭,拎着糖包去拜年,拜年拜到元宵节,数数还剩三家客。即便是这个顺口溜也不全,但我一直记得那个糖包的模样。邻里乡亲的糖包,差不多都是父亲包的。那时没有塑料袋,甚至少有塑料制品。父亲折荷叶、裁报纸的声音,像一种清脆的书写。几两糖用夏天就已准备好的荷叶包着,外面再用旧报纸包起来,再外面系一根红绳,尖尖的,规整的金字塔形。讲究的人家,还会在那尖顶之上放一长方形的红纸帖覆盖其上,叫“鸿运当头”,神圣极了。
我一直没能承接父亲这门讨人敬重的手艺。我只知道到处放爆竹。孩提时代,大人们喝酒、打牌、谈论一年的收成与下一年的盼头,而我们便不管不顾地放爆竹。我们跑到田野,用爆竹炸过獾子洞与黄鼠狼,回到乡村又把爆竹放到狗的尾巴上、放到邻家的猪圈里……那一年,我把映梅家猪圈炸了,那头猪吓得把映梅冲倒了。我们两家本就有矛盾,我心想这下完蛋了,过年还要打架!但事情却恰恰相反,父亲过年不打我,还主动上门赔了礼,此后,两家反而和好了。
儿时的我们对于过年,几乎就是从年头盼到年尾的。对于父老乡亲来说,不仅是盼,而是实打实地行动着、躬耕着。只是到了腊月,就有了那么些泾渭分明的某一天,比如腊八,家乡就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期待。我的家乡不兴吃腊八粥,但娶亲嫁女搬新房、顺鸡顺猪进祠堂等等,都在这个日子里完成——我的家乡杀年鸡杀年猪不叫杀,“杀”不吉利,因而叫“顺”,下一年的顺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再比如腊月廿四,有的地方叫祭祀日,我的家乡叫过小年。小年像序曲,像扉页。家乡有俗语,叫“长工短工,廿四满工”“有钱无钱,廿四回家过年”,说的都是对回家团圆的期盼。除此之外,腊月廿四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带着孩子上祖坟,迎接祖宗回家过年。祖宗在外为我们祈福祈寿辛苦一年,也要与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我记得桌上摆了他们的碗筷,龛里奉了他们的酒茶。此时的乡村,就像是把一壶老酒放入了灶堂里,等待温暖的时辰;时辰一到,整个村子就开始溢满酒香。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听父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东西要留着过年用,那衣服要留着过年穿。正所谓“穷日富年”。一年的汗水、一年的积攒,到除夕之夜都酿成了蜜,倾情地奢侈一回、尽兴一次。
我印象中,插田的时候,一定要插点糯稻。糯稻产量不高,但必须种,糯米过年要做糍粑,糍粑要用来招待拜年客。
田头地角一定要种上点玉米。过年要炸爆米花,爆米花熬糖,熬糖送亲友。炸爆米花没有确定的日子,反正是临近年关,轰的一声巨响,让整个村子都飘着爆米花的香气,整个村子的孩子也就都往那个炸响的地方跑去。乡村宁静,一声炸爆米花的巨响,真正是“宁静致远”。
边边角角一定要种上点绿豆,过年要搨豆丝。我不知道家乡的土语是不是这三个字,但它既是丝,更像诗,因而,我认为叫“拓豆诗”更有诗意:把磨得精细的绿豆与大米的稠浆,薄薄而均匀地涂在锅里蒸熟拓下来,就是一首饱满、松柔而精美的田园诗了。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家乡每到冬日,请人吃“豆诗”已成时尚,甚至有的村镇常年能吃到,且已被商家打造包装成家乡元素,礼品式地远销省内外了。我就是搞不懂,这么饱满松柔而精美可口的“豆诗”,为何没有被“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组看好呢!
三秋(秋播、秋收、秋管)时节,一定要到洲区去捡一些黄豆,过年要打老豆腐。老豆腐烧肉,是下酒的上等好菜。所谓洲区,实际上就是沿江地区。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家乡一般不种黄豆,而洲区却很多。记得每年担任这个重任的都是小姐姐。也不光是小姐姐,整个村庄都是与她大小一般的女孩子一同前往。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她们就各自挑着几十斤黄豆兴冲冲回来。我到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总是她们女孩子去了,因为那些捡回来的黄豆中,一部分是捡的,一部分却是捡时顺带偷的。当地人见是一帮女孩子,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还有一部分,是帮当地人家干点杂活,人家给的。
打豆腐有讲究,多少道工序我已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第一块豆腐一定要敬给祖先,让祖先先尝。其实,在我印象中,春节用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先敬祖先。父亲说,要知敬知重知恩,祖先保佑全家一年胜似一年。我知道父亲讲究的是孝道,同时也在教我们如何履行并传递孝道。
我不知道,父老乡亲到底为过年准备了多少流程。糍粑豆腐爆米花,熬糖顺猪山芋粑,搨豆丝贴对联,祭祖宗放万鞭,拎着糖包去拜年,拜年拜到元宵节,数数还剩三家客。即便是这个顺口溜也不全,但我一直记得那个糖包的模样。邻里乡亲的糖包,差不多都是父亲包的。那时没有塑料袋,甚至少有塑料制品。父亲折荷叶、裁报纸的声音,像一种清脆的书写。几两糖用夏天就已准备好的荷叶包着,外面再用旧报纸包起来,再外面系一根红绳,尖尖的,规整的金字塔形。讲究的人家,还会在那尖顶之上放一长方形的红纸帖覆盖其上,叫“鸿运当头”,神圣极了。
我一直没能承接父亲这门讨人敬重的手艺。我只知道到处放爆竹。孩提时代,大人们喝酒、打牌、谈论一年的收成与下一年的盼头,而我们便不管不顾地放爆竹。我们跑到田野,用爆竹炸过獾子洞与黄鼠狼,回到乡村又把爆竹放到狗的尾巴上、放到邻家的猪圈里……那一年,我把映梅家猪圈炸了,那头猪吓得把映梅冲倒了。我们两家本就有矛盾,我心想这下完蛋了,过年还要打架!但事情却恰恰相反,父亲过年不打我,还主动上门赔了礼,此后,两家反而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