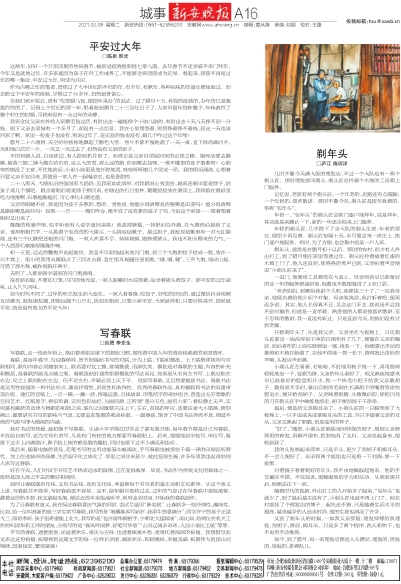发布日期:
剃年头
□庐江施训洋
儿时不像今天满大街的理发店,不过一个大队也有一两个剃头匠。那时理发就叫剃头,剃头匠总拎着个木制的工具箱上门服务。
记忆里,老家有两个剃头匠,一个年老的,走路还有点跛脚;一个年轻的,喜欢散讲。那时不像今天,剃头匠是按年收费的,俗称“包年头”。
年初一,“包年头”的剃头匠会挨门逐户地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来确认一下,新的一年还由他来上门服务。
年轻的剃头匠,几乎揽下了全大队的剃头生意;年老的那位,便很少再见着。剃头匠每隔十天、半月便会来一次庄上,挨门逐户地服务。有时,为了方便,也会集中到某一户人家。
剃年头,通常是在腊月初十以后。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外出打工,到了腊月便在家里等着过年。剃头匠拎着刷着红漆的木箱上门了,他人还没到,那咯咯的笑声已到,父亲听着声音便说“小剃头匠来了”。
一进门,他便将工具箱放在大桌上。母亲则将早已准备好的这一年的服务费递给他,他数也不数便塞进了上衣口袋。
“老表妈妈,到哪给我讲个人吧,我都快三十了。”一见我母亲,他便央着给他介绍个对象。母亲笑笑说,我打听着吧,便再没多说。其实,他人长得真不丑,又会这门手艺,按说是不会找不到对象的,但就是一直单着。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喜欢散讲,至于怎样的散讲,我一直没有听过。只是直到今天,他依旧没有讨到老婆。
开始剃年头了,先是我父亲。父亲坐在大板凳上。只见剃头匠拿出一块洗得很干净的白围布抖了几下,便铺在父亲的胸前,而后将布的上面往脖颈里一塞,再系一下。他便拿出手动的推剪和木梳开始剃了,在他不停地一捏一松下,推剪发出奇妙的声响,头发应声而落。
小剃头匠左看看、右转转,不时地用梳子挑一下,再用推剪轻轻地划一下,变剃为修,父亲的年头剃好了。他又熟练地拿来早已准备好的脸盆和开水,捏一个热毛巾把子给我父亲敷胡子。敷得差不多时,拿出自制的毛刷在长满胡子的嘴唇旁涂些肥皂水,便开始刮胡子。父亲眯着眼睛,头微微后仰,那把闪亮的刀在剃头匠手中熟练地游走,胡子便刮得干干净净。
最后,便是给父亲掏耳朵了。小剃头匠的一只脚架到了大板凳上,一只手里或夹或拿掏耳朵的工具,另只手提着父亲的耳朵,父亲又眯起了眼睛,很是受用的样子。
“好了。”随即,小剃头匠熟练地用特制的刷子,刷刷父亲脖颈里的碎发,再解开围布,狠劲地抖了又抖。父亲坐起身来,便轮到我了。
我的头发剃起来简单,只是平头,更少了刮胡子和掏耳朵,不一会儿便好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也只是剪一下刘海,修一下发髻。
对着镜子看着剃好的年头,我不由地佩服起他来。他的手艺确实不错。不仅如此,更佩服他的手力和站功。从我家离开后,他便去往下一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打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包年头”也就少了,到了最后基本没有了,小剃头匠也就不再上门了。他在村部挂了个理发店的牌子。起先还不错,只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时尚,他的生意也清淡了许多。
又到了剃年头的时候,一如我父亲那般,理发师傅给我理发、刮胡子、修面、掏耳朵。只是多了两个程序,洗头和吹干,也不再用手动推剪。
如今,到了腊月,每一家理发店都是人头攒动,理发的、烫发的、染发的,排着队儿。
儿时不像今天满大街的理发店,不过一个大队也有一两个剃头匠。那时理发就叫剃头,剃头匠总拎着个木制的工具箱上门服务。
记忆里,老家有两个剃头匠,一个年老的,走路还有点跛脚;一个年轻的,喜欢散讲。那时不像今天,剃头匠是按年收费的,俗称“包年头”。
年初一,“包年头”的剃头匠会挨门逐户地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来确认一下,新的一年还由他来上门服务。
年轻的剃头匠,几乎揽下了全大队的剃头生意;年老的那位,便很少再见着。剃头匠每隔十天、半月便会来一次庄上,挨门逐户地服务。有时,为了方便,也会集中到某一户人家。
剃年头,通常是在腊月初十以后。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外出打工,到了腊月便在家里等着过年。剃头匠拎着刷着红漆的木箱上门了,他人还没到,那咯咯的笑声已到,父亲听着声音便说“小剃头匠来了”。
一进门,他便将工具箱放在大桌上。母亲则将早已准备好的这一年的服务费递给他,他数也不数便塞进了上衣口袋。
“老表妈妈,到哪给我讲个人吧,我都快三十了。”一见我母亲,他便央着给他介绍个对象。母亲笑笑说,我打听着吧,便再没多说。其实,他人长得真不丑,又会这门手艺,按说是不会找不到对象的,但就是一直单着。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喜欢散讲,至于怎样的散讲,我一直没有听过。只是直到今天,他依旧没有讨到老婆。
开始剃年头了,先是我父亲。父亲坐在大板凳上。只见剃头匠拿出一块洗得很干净的白围布抖了几下,便铺在父亲的胸前,而后将布的上面往脖颈里一塞,再系一下。他便拿出手动的推剪和木梳开始剃了,在他不停地一捏一松下,推剪发出奇妙的声响,头发应声而落。
小剃头匠左看看、右转转,不时地用梳子挑一下,再用推剪轻轻地划一下,变剃为修,父亲的年头剃好了。他又熟练地拿来早已准备好的脸盆和开水,捏一个热毛巾把子给我父亲敷胡子。敷得差不多时,拿出自制的毛刷在长满胡子的嘴唇旁涂些肥皂水,便开始刮胡子。父亲眯着眼睛,头微微后仰,那把闪亮的刀在剃头匠手中熟练地游走,胡子便刮得干干净净。
最后,便是给父亲掏耳朵了。小剃头匠的一只脚架到了大板凳上,一只手里或夹或拿掏耳朵的工具,另只手提着父亲的耳朵,父亲又眯起了眼睛,很是受用的样子。
“好了。”随即,小剃头匠熟练地用特制的刷子,刷刷父亲脖颈里的碎发,再解开围布,狠劲地抖了又抖。父亲坐起身来,便轮到我了。
我的头发剃起来简单,只是平头,更少了刮胡子和掏耳朵,不一会儿便好了。母亲和两个姐姐也只是剪一下刘海,修一下发髻。
对着镜子看着剃好的年头,我不由地佩服起他来。他的手艺确实不错。不仅如此,更佩服他的手力和站功。从我家离开后,他便去往下一家。
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打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包年头”也就少了,到了最后基本没有了,小剃头匠也就不再上门了。他在村部挂了个理发店的牌子。起先还不错,只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时尚,他的生意也清淡了许多。
又到了剃年头的时候,一如我父亲那般,理发师傅给我理发、刮胡子、修面、掏耳朵。只是多了两个程序,洗头和吹干,也不再用手动推剪。
如今,到了腊月,每一家理发店都是人头攒动,理发的、烫发的、染发的,排着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