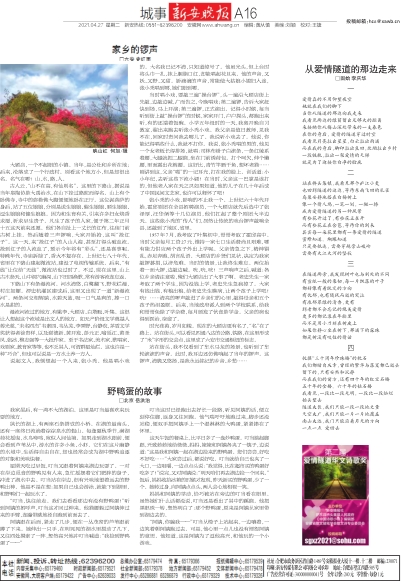发布日期:
家乡的锣声
□六安史红雨
大顾店,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当年,是公社和乡所在地;后来,沦落成了一个行政村。别看这个地方小,但是却很出名。名气在哪?山,水,路,人。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里的下骆山,据说是当年皋陶协助大禹治水,在山下拴过骆驼而得名。山上有个卧佛寺,寺中的弥勒佛大腹便便地卧在正厅。这位泥菩萨的身后,站了五位娘娘,分别是送生娘娘、催生娘娘、顺生娘娘、逗生娘娘和健生娘娘。因为和生育有关,引来许多妇女烧香求愿,祈求早生贵子。凡生了孩子的人家,便于第二年正月十五这天前来还愿。他们各自扯上一丈长的红布,往庙门前古树上挂。然后随着三声锣响,大家开始抢,这叫“抢红子”。这一天,来“抢红子”的人山人海,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抢到红子的人流血了,预示今年将有“彩头”,还是喜事呢。特殊年代,寺庙拆除了,香火不复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省里在下骆山建起微波站,建设了电视传输系统。后来,“有线”让位给“无线”,微波站也过时了。不过,现在这里,山上古木参天,山中洞穴幽深,山下田园渔歌,常有游客流连忘返。
下骆山下有条漫流河。河水清悠,白鹭翻飞,野花烂漫,村庄如螺。淠史杭灌区建成后,这里又出现了一道“新漫流河”。两条河交相辉映,水碧天蓝,吸一口气是爽的,捧一口水是甜的。
漫流河流过的地方,有姚李、大顾店、白塔畈、叶集。这很让人想起这个流域是出文人的地方。如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蒋光慈,“未名四杰”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以及谢德新、黄开发、彭元正、喻廷江、黄圣凤、张冰、穆志强等一大批作家。至于书法家、美术家、歌唱家、戏剧家、教育家等等,也不乏其人,可谓群星灿烂。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也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说起文人,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张小秃。他是唱小戏的。大名我已记不清,只知道绰号了。他虽光头,但上台时将头巾一扎,抹上胭脂口红,却能唱起花旦来。他的声音,又妖、又野、又甜。娇滴滴的声音,常能使大姑娘小媳妇入迷,张小秃唱到哪,她们跟到哪。
当时唱小戏,要敲三遍“操台锣”,头一遍沿大顾店街上先敲,边敲边喊,广而告之,今晚唱戏;第二遍锣,告诉大家赶快到场,马上开演;第三遍锣,正式演出。记得小时候,每当听到街上敲“操台锣”的时候,家家开门,户户探头,都跑出来听,有的还端着饭碗。小学五年级时的一天,我离开晚自习教室,溜出来跑去听张小秃小戏。我父亲是值日教师,见我不在,回家时责问我去哪儿了。我说听小戏去了。他说,你能记得唱些什么,我就不打你。我说,张小秃唱的男的,他见一个女老板长得排场,就唱:司林布褂子白滚条,一条红绫系着腰,大腿就把二腿跷,坐在门前绣荷包。打个呵欠,伸个懒腰,里面露出花裤腰。这好比,青竹竿晒干鱼,想坏老猫……刚讲到这,父亲“啪”的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训话道:小小年纪,去听这些下流小调!在当时,父亲这一巴掌是该打的,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儿子在几十年后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家,也许可以释怀了吧!
张小秃的小戏,影响的不止我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霍邱剧团在全县招聘演员,一个大顾店就先后选中了张泽厚、汪华炳等十几位演员,他们扛起了整个剧团大半边天。这些张小秃的“传人”们,居然让传统的戏台锣声敲响全县,还敲到了地区、省里。
1957年7月,我考取了叶集初中,哥哥考取了霍邱高中。当时父亲每月工资27元,维持一家七口生活费尚且艰难,哪有能力供应两个孩子外出上学呢。父亲情急之下,精神错乱,赤足奔跑,胡言乱语。大顾店的乡贤们见状,决定为我家敲锣募捐,以济危难。当时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两位抬着一面大锣,边敲边喊。咣,咣,咣!三声响声之后,喊道:各位乡亲请注意啦,俺们大顾店出了大事了啊。老史先生一家考取了两个学生,因为没钱上学,老史先生急疯掉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给老史先生瞧病,让两个孩子上学吧!咣!……清亮的啰声敲进了乡亲们的心里,敲得母亲和五个孩子热泪盈眶。后来,当地政府派人到两个学校联系,给我和哥哥免除了学杂费,每月颁发了伙食助学金。父亲的病也得到医治,痊愈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现在的大顾店更有名了,“名”在了路上。站在街头,可以看见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在这里形成了“米”字形的交会点,这里成了六安市交通枢纽的标志。
站在街头,我不仅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也听到了车轮滚滚的声音。此时,我耳边还仿佛响起了当年的锣声。这锣声,清脆又悠扬,是我永远铭记的乡音、乡愁……
大顾店,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当年,是公社和乡所在地;后来,沦落成了一个行政村。别看这个地方小,但是却很出名。名气在哪?山,水,路,人。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里的下骆山,据说是当年皋陶协助大禹治水,在山下拴过骆驼而得名。山上有个卧佛寺,寺中的弥勒佛大腹便便地卧在正厅。这位泥菩萨的身后,站了五位娘娘,分别是送生娘娘、催生娘娘、顺生娘娘、逗生娘娘和健生娘娘。因为和生育有关,引来许多妇女烧香求愿,祈求早生贵子。凡生了孩子的人家,便于第二年正月十五这天前来还愿。他们各自扯上一丈长的红布,往庙门前古树上挂。然后随着三声锣响,大家开始抢,这叫“抢红子”。这一天,来“抢红子”的人山人海,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抢到红子的人流血了,预示今年将有“彩头”,还是喜事呢。特殊年代,寺庙拆除了,香火不复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省里在下骆山建起微波站,建设了电视传输系统。后来,“有线”让位给“无线”,微波站也过时了。不过,现在这里,山上古木参天,山中洞穴幽深,山下田园渔歌,常有游客流连忘返。
下骆山下有条漫流河。河水清悠,白鹭翻飞,野花烂漫,村庄如螺。淠史杭灌区建成后,这里又出现了一道“新漫流河”。两条河交相辉映,水碧天蓝,吸一口气是爽的,捧一口水是甜的。
漫流河流过的地方,有姚李、大顾店、白塔畈、叶集。这很让人想起这个流域是出文人的地方。如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蒋光慈,“未名四杰”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以及谢德新、黄开发、彭元正、喻廷江、黄圣凤、张冰、穆志强等一大批作家。至于书法家、美术家、歌唱家、戏剧家、教育家等等,也不乏其人,可谓群星灿烂。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也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说起文人,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张小秃。他是唱小戏的。大名我已记不清,只知道绰号了。他虽光头,但上台时将头巾一扎,抹上胭脂口红,却能唱起花旦来。他的声音,又妖、又野、又甜。娇滴滴的声音,常能使大姑娘小媳妇入迷,张小秃唱到哪,她们跟到哪。
当时唱小戏,要敲三遍“操台锣”,头一遍沿大顾店街上先敲,边敲边喊,广而告之,今晚唱戏;第二遍锣,告诉大家赶快到场,马上开演;第三遍锣,正式演出。记得小时候,每当听到街上敲“操台锣”的时候,家家开门,户户探头,都跑出来听,有的还端着饭碗。小学五年级时的一天,我离开晚自习教室,溜出来跑去听张小秃小戏。我父亲是值日教师,见我不在,回家时责问我去哪儿了。我说听小戏去了。他说,你能记得唱些什么,我就不打你。我说,张小秃唱的男的,他见一个女老板长得排场,就唱:司林布褂子白滚条,一条红绫系着腰,大腿就把二腿跷,坐在门前绣荷包。打个呵欠,伸个懒腰,里面露出花裤腰。这好比,青竹竿晒干鱼,想坏老猫……刚讲到这,父亲“啪”的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训话道:小小年纪,去听这些下流小调!在当时,父亲这一巴掌是该打的,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儿子在几十年后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家,也许可以释怀了吧!
张小秃的小戏,影响的不止我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霍邱剧团在全县招聘演员,一个大顾店就先后选中了张泽厚、汪华炳等十几位演员,他们扛起了整个剧团大半边天。这些张小秃的“传人”们,居然让传统的戏台锣声敲响全县,还敲到了地区、省里。
1957年7月,我考取了叶集初中,哥哥考取了霍邱高中。当时父亲每月工资27元,维持一家七口生活费尚且艰难,哪有能力供应两个孩子外出上学呢。父亲情急之下,精神错乱,赤足奔跑,胡言乱语。大顾店的乡贤们见状,决定为我家敲锣募捐,以济危难。当时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两位抬着一面大锣,边敲边喊。咣,咣,咣!三声响声之后,喊道:各位乡亲请注意啦,俺们大顾店出了大事了啊。老史先生一家考取了两个学生,因为没钱上学,老史先生急疯掉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给老史先生瞧病,让两个孩子上学吧!咣!……清亮的啰声敲进了乡亲们的心里,敲得母亲和五个孩子热泪盈眶。后来,当地政府派人到两个学校联系,给我和哥哥免除了学杂费,每月颁发了伙食助学金。父亲的病也得到医治,痊愈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现在的大顾店更有名了,“名”在了路上。站在街头,可以看见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在这里形成了“米”字形的交会点,这里成了六安市交通枢纽的标志。
站在街头,我不仅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也听到了车轮滚滚的声音。此时,我耳边还仿佛响起了当年的锣声。这锣声,清脆又悠扬,是我永远铭记的乡音、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