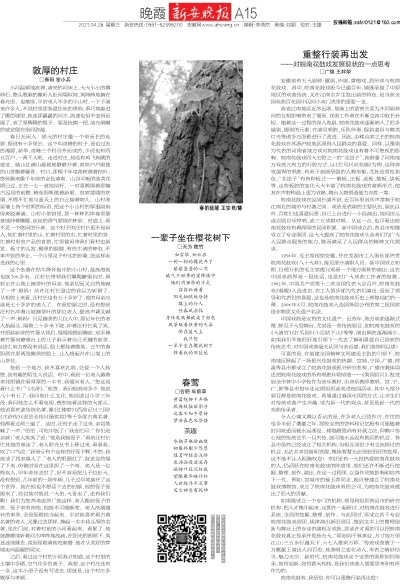发布日期:
敦厚的村庄
□青阳章小兵
小河温顺地流着,清亮的河床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憨头憨脑的像听人扯闲篇似地,笑眯眯地躺在春光里。也难怪,平时来人不多的小山村,一下子涌来许多人,不说村里那条爱狂吠的黑狗,乖巧地躲进了篱笆墙里,就连那潺潺的河水,流速也似乎变得迟缓了,成了厚稠稠的缎子。要是抚摸一把,油光滑嫩的感觉便在指间弥漫。
春日无闲人。偌大的村庄像一个窄而长的走廊,据说有十多里长。这个叫奇峰的村子,是由过去的湘源、新华、奇峰三个村合并而成的,少说也有四五百户,一两千人吧。走进村庄,却没有鸡飞狗跳的感觉。映山红满山漫坡地静静开着,家家户户刚做的山茶飘着馨香。村口,那棵千年皂角树落着枯叶,悠扬飘来像千年前的金色请柬。山谷平畈的油菜花期已过,正在一心一意地结籽。一对喜鹊围着那幢古民居的前檐,精垒细啄做着新巢。农家缕缕的炊烟,不慌不忙地与蓝天上的白云接着吻儿。山村老屋墙上各个时期的标语,把这个小山村的厚重渲染得斑驳淋漓。山村小茶馆里,那一杯杯四库春雪惬意地伸着懒腰,丝丝的香气萦绕在杯前。村道上,看不见一个悠闲的行者。这个村子的汪村长更不是闲人,他忙着村里的山,忙着村里的水,忙着村里的茶,忙着村里农产品的直销,忙里偷闲带我们看村史展览。板寸的头发,黝黑的脸膛,有些木讷的神态,不事声张的举止,一个山里汉子朴实的形象,就这样走进我的心里。
这个坐落在牯牛降怀抱中的小山村,最高海拔也就700多米。汪村长带领我们攀爬瞭望台时,看到正在山坡上摘茶叶的母亲,他亲切而又自然地喊了一声:姆妈!站在汪村长身边的我以为听错了。从相貌上来看,汪村长也有五十多岁了,他的母亲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惊疑之时,没有想到汪村长冲着山坡摘茶叶的那位老人,提高声调又喊了一声:姆妈!只见摘茶的几位人中,那位年长的老人抬起头,隔着二十多米下坡,冲着汪村长笑了笑,并把装新茶的竹篓从背后,慢慢地挪到胸前,双手捧着竹篓向瞭望台上的儿子展示着自己采摘的新茶。此时,双方都没有说话,脸上都挂着微笑。正午的春阳洒在那两张黝黑的脸上,让人想起开在山崖上的山茶花。
每到一个地方,我不喜欢扎堆,总爱一个人转悠,找有趣的陌生人说话。村中,看到一位老人戴着老花眼镜在看厚厚的一本书,我便问老人:“您这是看什么书?”“《水浒》。”他答。我问他高寿多少,他说八十有五了;我问他什么文化,他说读过小学三年级;我问他怎么不看电视,费劲地看这样的大部头。他说喜欢读传统名著,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十多部古典名著,他都看过两三遍了。这时,汪村长走了过来,亲切地喊了一声:“伯伯,可吃中饭了?”我连忙问:“你们是亲戚?”老人笑笑了说:“他是我胞侄子。”看到汪村长忙其他的事走了,老人眼光从书上移过来,看看我,叹了口气说:“我得亏有个这样的好侄子啊,不然,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老人的眼圈红了,叙述显然慢了下来,仿佛时间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老人是一位残疾人,早年老伴去世了,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没有想到,几年前的一场车祸,儿子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他也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他的侄子侄媳来了,恳切地对他说:“大伯,大哥走了,还有我们啊!我们为您养老送终!”就这样,老人搬到侄子的家。侄子家有肉吃,他就不可能断荤。老人洗涮缝补的事务,全是侄媳担当起来。平时就喜欢看古典名著的老人,又像过去那样,捧起一本本砖头厚的名著,坐在门前,对着村前的小河看起来。看累了,他就静静地听着河水哗哗地流淌,在阳光的朗照下,笑迷迷地睡去,直到侄媳请他吃晚餐,他才从美好的梦境走向温暖的现实。
之后,看过这个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个村里的土壤中多硒,空气中多负离子。我想,这个村庄还有一多,这本小册子没有写进去,那就是,这个村庄多敦厚与孝顺。
小河温顺地流着,清亮的河床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憨头憨脑的像听人扯闲篇似地,笑眯眯地躺在春光里。也难怪,平时来人不多的小山村,一下子涌来许多人,不说村里那条爱狂吠的黑狗,乖巧地躲进了篱笆墙里,就连那潺潺的河水,流速也似乎变得迟缓了,成了厚稠稠的缎子。要是抚摸一把,油光滑嫩的感觉便在指间弥漫。
春日无闲人。偌大的村庄像一个窄而长的走廊,据说有十多里长。这个叫奇峰的村子,是由过去的湘源、新华、奇峰三个村合并而成的,少说也有四五百户,一两千人吧。走进村庄,却没有鸡飞狗跳的感觉。映山红满山漫坡地静静开着,家家户户刚做的山茶飘着馨香。村口,那棵千年皂角树落着枯叶,悠扬飘来像千年前的金色请柬。山谷平畈的油菜花期已过,正在一心一意地结籽。一对喜鹊围着那幢古民居的前檐,精垒细啄做着新巢。农家缕缕的炊烟,不慌不忙地与蓝天上的白云接着吻儿。山村老屋墙上各个时期的标语,把这个小山村的厚重渲染得斑驳淋漓。山村小茶馆里,那一杯杯四库春雪惬意地伸着懒腰,丝丝的香气萦绕在杯前。村道上,看不见一个悠闲的行者。这个村子的汪村长更不是闲人,他忙着村里的山,忙着村里的水,忙着村里的茶,忙着村里农产品的直销,忙里偷闲带我们看村史展览。板寸的头发,黝黑的脸膛,有些木讷的神态,不事声张的举止,一个山里汉子朴实的形象,就这样走进我的心里。
这个坐落在牯牛降怀抱中的小山村,最高海拔也就700多米。汪村长带领我们攀爬瞭望台时,看到正在山坡上摘茶叶的母亲,他亲切而又自然地喊了一声:姆妈!站在汪村长身边的我以为听错了。从相貌上来看,汪村长也有五十多岁了,他的母亲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惊疑之时,没有想到汪村长冲着山坡摘茶叶的那位老人,提高声调又喊了一声:姆妈!只见摘茶的几位人中,那位年长的老人抬起头,隔着二十多米下坡,冲着汪村长笑了笑,并把装新茶的竹篓从背后,慢慢地挪到胸前,双手捧着竹篓向瞭望台上的儿子展示着自己采摘的新茶。此时,双方都没有说话,脸上都挂着微笑。正午的春阳洒在那两张黝黑的脸上,让人想起开在山崖上的山茶花。
每到一个地方,我不喜欢扎堆,总爱一个人转悠,找有趣的陌生人说话。村中,看到一位老人戴着老花眼镜在看厚厚的一本书,我便问老人:“您这是看什么书?”“《水浒》。”他答。我问他高寿多少,他说八十有五了;我问他什么文化,他说读过小学三年级;我问他怎么不看电视,费劲地看这样的大部头。他说喜欢读传统名著,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十多部古典名著,他都看过两三遍了。这时,汪村长走了过来,亲切地喊了一声:“伯伯,可吃中饭了?”我连忙问:“你们是亲戚?”老人笑笑了说:“他是我胞侄子。”看到汪村长忙其他的事走了,老人眼光从书上移过来,看看我,叹了口气说:“我得亏有个这样的好侄子啊,不然,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老人的眼圈红了,叙述显然慢了下来,仿佛时间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老人是一位残疾人,早年老伴去世了,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没有想到,几年前的一场车祸,儿子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他也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他的侄子侄媳来了,恳切地对他说:“大伯,大哥走了,还有我们啊!我们为您养老送终!”就这样,老人搬到侄子的家。侄子家有肉吃,他就不可能断荤。老人洗涮缝补的事务,全是侄媳担当起来。平时就喜欢看古典名著的老人,又像过去那样,捧起一本本砖头厚的名著,坐在门前,对着村前的小河看起来。看累了,他就静静地听着河水哗哗地流淌,在阳光的朗照下,笑迷迷地睡去,直到侄媳请他吃晚餐,他才从美好的梦境走向温暖的现实。
之后,看过这个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个村里的土壤中多硒,空气中多负离子。我想,这个村庄还有一多,这本小册子没有写进去,那就是,这个村庄多敦厚与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