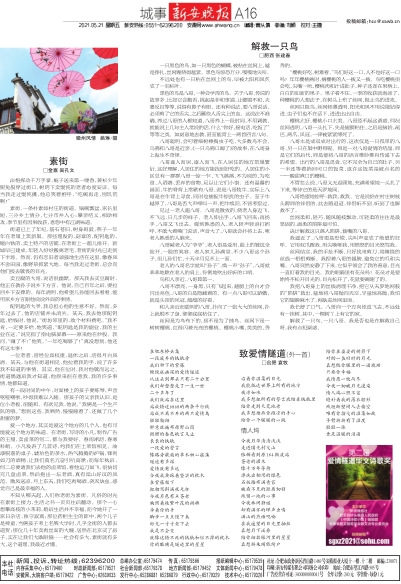发布日期:
素街
□金寨吴孔文
法梧挥动千万手掌,栀子送来第一缕香,黄衫少年脱兔般穿过街口,树阴下卖馄饨的老者态度安详。每当我走过馄饨摊,他总笑着招呼,“吃碗再走,别饥荒啊!”
素街,一条朴素如村庄的街道。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三分乡土情分,七分市井人心;攀亲结义,相助相攻,季节里有因果收获,恩怨中有江湖味道。
街道已上了年纪,基石苍旧,树身斑驳,燕子一年年在老巢上筑新巢。那些理发的、刻章的、配钥匙的、砸白铁的、卖土特产的店铺,在老街上一溜儿排开。新城早已建成,年轻人纷纷搬离老宅,老街的时光已走到下半场。然而,仍有恋旧者顽强地生活在这里,像春风不舍田园,像野草抓紧大地。每当我走过老街,总会向他们投去敬畏的目光。
卖豆腐的大哥,说话很幽默。那天我去买豆腐时,他正在教孙子说乡下方言。他说,自己百年之后,要拉回乡下安葬的。每年清明,他希望儿孙能回去看看,能用家乡方言跟他说说外面的事情。
配钥匙的大爷,我总担心他的生意不好。然而,多年过去了,他的店铺并未消失。某天,我去他那配钥匙,给钱时,他说,“街坊邻里的,收个材料费吧。”我不肯,一定要多给,他笑道,“配钥匙是我的副业,我的主业在这。”说完指了指电脑屏幕——原来他在炒股。我问,“赚了不?”他笑,“一年吃喝够了!”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本事!
一位老者,曾经位高权重,退休之后,活得月白风清。某天,与他在街道相见,他拉着我的手,说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他在位时,我对他敬而远之。街道偶遇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很在意我,我的许多事情,他都知道。
有一段时间的中午,对面楼上的孩子要练琴,声音呕哑嘲哳,吵得我难以入睡。那孩子的父亲我认识,是位小老板,很随和。有次见我,他说,“我俩是一个生产队的哦。”想到这些,我哂然,慢慢睡着了,还做了几个甜蜜的梦。
爱一个地方,其实是爱这个地方的几个人,也有可能爱这个地方的味道。在老街,写诗的小凡,制作广告的王翔,卖卤菜的何二,都与我要好。春雨淅沥,春寒料峭。小凡发表了几首诗,约我们在土菜馆相见。油漆脱落的桌子,琥珀色的茶水,热气腾腾的炉锅,锋利如刀的酒精,让我们莫名亢奋引吭高歌;而每年秋后,何二总要请我们去他的卤菜馆,看他运刀如飞,很快切完几盘卤菜,然后抱出一坛老酒,真有梁山好汉的风范。微风送凉,月上东天,我们吃肉喝酒,浇灭块垒,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不知从哪天起,人们称老街为素街。凡俗的时光在素街上接力,生活之书一页页往后翻动。那个一心想攀高枝的小茉莉,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而今她开了一家日杂店,独守寂寞;那位药柜生尘的郎中,两个儿子是神童,当俩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时,几乎全街的人都去道贺;那位几十年卖肉丝面的大嫂,居然在北京买了房子,实在让我们大跌眼镜……社会有多大,素街就有多大,这个道理,我最近才懂。
法梧挥动千万手掌,栀子送来第一缕香,黄衫少年脱兔般穿过街口,树阴下卖馄饨的老者态度安详。每当我走过馄饨摊,他总笑着招呼,“吃碗再走,别饥荒啊!”
素街,一条朴素如村庄的街道。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三分乡土情分,七分市井人心;攀亲结义,相助相攻,季节里有因果收获,恩怨中有江湖味道。
街道已上了年纪,基石苍旧,树身斑驳,燕子一年年在老巢上筑新巢。那些理发的、刻章的、配钥匙的、砸白铁的、卖土特产的店铺,在老街上一溜儿排开。新城早已建成,年轻人纷纷搬离老宅,老街的时光已走到下半场。然而,仍有恋旧者顽强地生活在这里,像春风不舍田园,像野草抓紧大地。每当我走过老街,总会向他们投去敬畏的目光。
卖豆腐的大哥,说话很幽默。那天我去买豆腐时,他正在教孙子说乡下方言。他说,自己百年之后,要拉回乡下安葬的。每年清明,他希望儿孙能回去看看,能用家乡方言跟他说说外面的事情。
配钥匙的大爷,我总担心他的生意不好。然而,多年过去了,他的店铺并未消失。某天,我去他那配钥匙,给钱时,他说,“街坊邻里的,收个材料费吧。”我不肯,一定要多给,他笑道,“配钥匙是我的副业,我的主业在这。”说完指了指电脑屏幕——原来他在炒股。我问,“赚了不?”他笑,“一年吃喝够了!”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本事!
一位老者,曾经位高权重,退休之后,活得月白风清。某天,与他在街道相见,他拉着我的手,说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他在位时,我对他敬而远之。街道偶遇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很在意我,我的许多事情,他都知道。
有一段时间的中午,对面楼上的孩子要练琴,声音呕哑嘲哳,吵得我难以入睡。那孩子的父亲我认识,是位小老板,很随和。有次见我,他说,“我俩是一个生产队的哦。”想到这些,我哂然,慢慢睡着了,还做了几个甜蜜的梦。
爱一个地方,其实是爱这个地方的几个人,也有可能爱这个地方的味道。在老街,写诗的小凡,制作广告的王翔,卖卤菜的何二,都与我要好。春雨淅沥,春寒料峭。小凡发表了几首诗,约我们在土菜馆相见。油漆脱落的桌子,琥珀色的茶水,热气腾腾的炉锅,锋利如刀的酒精,让我们莫名亢奋引吭高歌;而每年秋后,何二总要请我们去他的卤菜馆,看他运刀如飞,很快切完几盘卤菜,然后抱出一坛老酒,真有梁山好汉的风范。微风送凉,月上东天,我们吃肉喝酒,浇灭块垒,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不知从哪天起,人们称老街为素街。凡俗的时光在素街上接力,生活之书一页页往后翻动。那个一心想攀高枝的小茉莉,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而今她开了一家日杂店,独守寂寞;那位药柜生尘的郎中,两个儿子是神童,当俩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时,几乎全街的人都去道贺;那位几十年卖肉丝面的大嫂,居然在北京买了房子,实在让我们大跌眼镜……社会有多大,素街就有多大,这个道理,我最近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