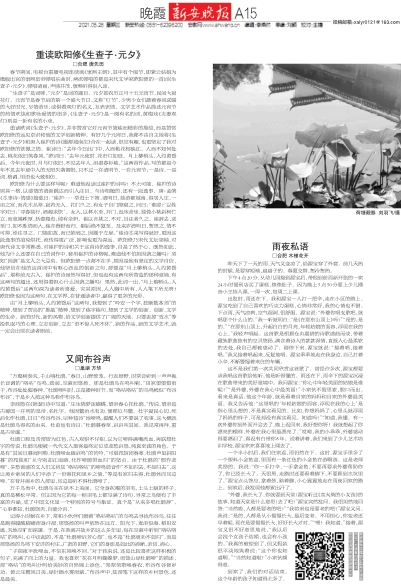发布日期:
重读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合肥唐先田
春节期间,电视台重播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其中有个细节,即紫云姑娘为微服出宫的康熙皇帝弹唱乐曲时,两次弹唱的都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词《生查子·元夕》,弹唱清丽,声情并茂,康熙听得很入迷。
“生查子”是词牌,“元夕”是词的题目。元夕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大闹花灯。元宵节是春节后的第一个盛大节日,又称“灯节”,少男少女们趁着春风送暖的大好时光,尽情游乐;或借着观灯的名义,互表衷情。文学艺术作品描述元宵节的热情欢快和歌咏爱情的很多,《生查子·元夕》是一阕有名的词,黄梅戏《夫妻观灯》则是一折有名的小戏。
重读欧词《生查子·元夕》,并非赞赏它对元宵节简炼而精彩的描绘,而是赞赏欧阳修的远见卓识和他的文学创新精神。有好几个元宵日,我都不由自主地将《生查子·元夕》和唐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合在一起读,很觉有趣,也更坚定了我对欧阳修的钦佩之情。崔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欧词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两首作品,写的都是今年不见去年意中人的无限失落惆怅,只不过一在清明节,一在元宵节;一是诗,一是词,格调、用语也大致相仿。
欧阳修为什么要这样写呢?难道他没读过崔护的诗吗?不太可能。崔护的诗别具一格,以感情的清新跳达而引人注目。与诗相随的,还有一段逸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篇载曰:“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于左扉。”崔诗本来写得就好,更因这段逸事的渲染烘托,流传得更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欧阳修乃宋代文坛领袖,对唐代诗文非常熟悉,对崔护的诗和关于这首诗的逸事,自是了然于心。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词作中,套用崔护的诗格呢,难道他不怕担因袭之嫌吗?须知“因袭”是文人之大忌矣。但欧阳修一点都不在乎,原因是他有坚定的文学自信,他坚信在他的这首词中有呕心沥血的创新之句,那便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堪称前无古人。崔护的诗虽然写得好,但也没有这两句所营造的那种意境,有这两句的超出,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因袭之嫌吗!果然,此词一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深为读者所喜爱。究其原因,人人胸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呀!欧阳修也因为这两句,在文学界、在普通读者中,赢得了更多的光彩。
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我想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精神,想到了贾岛的“推敲”精神,想到了炼字炼句,想到了文学的创新。创新,文学的生命。新的时代、新的风物,给文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丢掉“放水”等投机取巧的心理,立志创新,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新的作品,新的文学艺术,就一定会出现在读者眼前。
春节期间,电视台重播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其中有个细节,即紫云姑娘为微服出宫的康熙皇帝弹唱乐曲时,两次弹唱的都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词《生查子·元夕》,弹唱清丽,声情并茂,康熙听得很入迷。
“生查子”是词牌,“元夕”是词的题目。元夕即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大闹花灯。元宵节是春节后的第一个盛大节日,又称“灯节”,少男少女们趁着春风送暖的大好时光,尽情游乐;或借着观灯的名义,互表衷情。文学艺术作品描述元宵节的热情欢快和歌咏爱情的很多,《生查子·元夕》是一阕有名的词,黄梅戏《夫妻观灯》则是一折有名的小戏。
重读欧词《生查子·元夕》,并非赞赏它对元宵节简炼而精彩的描绘,而是赞赏欧阳修的远见卓识和他的文学创新精神。有好几个元宵日,我都不由自主地将《生查子·元夕》和唐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合在一起读,很觉有趣,也更坚定了我对欧阳修的钦佩之情。崔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欧词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两首作品,写的都是今年不见去年意中人的无限失落惆怅,只不过一在清明节,一在元宵节;一是诗,一是词,格调、用语也大致相仿。
欧阳修为什么要这样写呢?难道他没读过崔护的诗吗?不太可能。崔护的诗别具一格,以感情的清新跳达而引人注目。与诗相随的,还有一段逸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篇载曰:“崔护……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于左扉。”崔诗本来写得就好,更因这段逸事的渲染烘托,流传得更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欧阳修乃宋代文坛领袖,对唐代诗文非常熟悉,对崔护的诗和关于这首诗的逸事,自是了然于心。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词作中,套用崔护的诗格呢,难道他不怕担因袭之嫌吗?须知“因袭”是文人之大忌矣。但欧阳修一点都不在乎,原因是他有坚定的文学自信,他坚信在他的这首词中有呕心沥血的创新之句,那便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堪称前无古人。崔护的诗虽然写得好,但也没有这两句所营造的那种意境,有这两句的超出,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因袭之嫌吗!果然,此词一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深为读者所喜爱。究其原因,人人胸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呀!欧阳修也因为这两句,在文学界、在普通读者中,赢得了更多的光彩。
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我想到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精神,想到了贾岛的“推敲”精神,想到了炼字炼句,想到了文学的创新。创新,文学的生命。新的时代、新的风物,给文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丢掉“放水”等投机取巧的心理,立志创新,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新的作品,新的文学艺术,就一定会出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