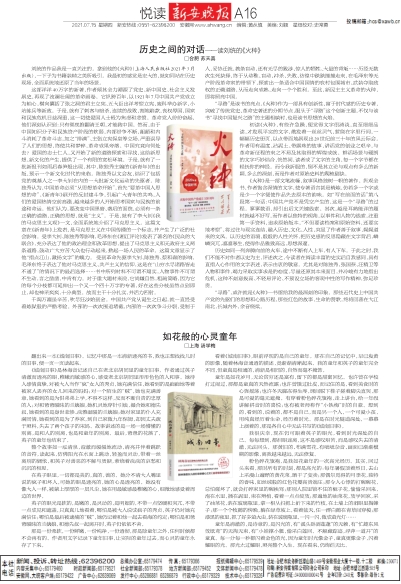发布日期:
如花般的心灵童年
□上海汤学梅
翻出来一本《城南旧事》。记忆中那是一本清新透亮的书,我也正想找找儿时的旧事,便一页一页读起来。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记述自己在老北京胡同里的童年旧事。作者通过英子清澈而透亮的眼,稚嫩而敏感的心,感受老北京胡同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她待人感情真挚,对被大人当作“疯”女人的秀贞,她充满信任,她看到的是痴痴地等着被家人丢弃的女儿回来的妈妈;对一个陌生的“贼”,她也充满善意,她看到的是为供弟弟上学,不得不这样,反而不断自责的忠厚的人;对和爸爸暧昧的兰姨娘,她机灵地穿针引线,撮合她和德先叔,她看到的是身世悲惨、淡雅温暖的兰姨娘;她对家里的仆人充满同情,她看到的是为了养家,到自己家做九年保姆,却因丈夫疏于照料,失去了两个孩子的宋妈。故事讲述的是一场一场懵懂的别离,是和人的别离,也是和童年的别离。最后,爸爸的花落了,英子的童年也结束了。
整个故事如一泓清泉,澄澈而缓缓地流动,清亮并伴着跳跃的音符,读起来,仿佛阳光在水面上跳动,轻盈而灵动,带着一丝离别的惆怅,和英子对善恶的不解与质疑,萦绕着淡淡的哀愁和沉沉的相思。
在英子眼里,一切都是美的,真的,善的。她分不清大人嘴里说的疯子和坏人,可她的眼是透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她没有像大人一样,被蒙上厚厚的一层凡尘,她在用最敏感最稚嫩的心,细微地感受着周边的世界。
英子的眼光是软的,是嫩的,是灵动的,是明媚的,不带一点坚硬和突兀,不带一点成见和遮盖,只真真儿地看着,哪怕是被大人说成疯子的秀贞,英子仍对她充满信任;哪怕是最后被逮捕的“贼”,她仍记着和他一起去看海的约定;哪怕是和爸爸暧昧的兰姨娘,和德先叔一起离开时,英子仍依依不舍。
那是一份柔软,一份鲜嫩,一份纯净,一份透彻,那是除童年之外,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有的。作者用文字记录下童年旧事,让实际的童年过去,而心灵的童年永存了下来。
看着《城南旧事》,眼前浮现的是自己的童年。那在自己的记忆中,早已发黄的影像,随着林海音通透的描述,竟渐渐清晰起来。我的童年和英子的童年完全不同,但童真是相通的,清新是相同的,自然而毫不掩饰。
童年是如花岁月,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留下的都是甜蜜回忆。也许曾在学校打过闹过,那都是童真的天然流露;也许曾饿过肚皮,而记住的是,看到美食时的心旌摇荡;也许冬天脚冻得生疼,课间脱下鞋子搓着脚尖直哭,那是可爱的毫无遮掩。有穿着粉色碎花旗袍,走上讲台,给一年级讲解拼音时的喜悦;也有被老师称作“小铁梅”时的自豪。想到的,看到的,说着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可爱小孩,用纯真经历着生命,经历着时光。那是在时光隧道深处,一幕幕上演着的,那是各自心中无法书写的《城南旧事》。
我很庆幸,现在仍可跟着英子的眼光,看到时光深处的自己。每每想到,都泪眼迷离,这不是感叹艰苦,而是感叹失去的清澈,无法回头。那黄旧的、布满雪花、有呲呲杂音、画面已渐渐模糊的影像,离我越来越远,无法修复。
粉色碎花旗袍,是我如花童年的一次高光经历。其实,回过头来看,那时所有的时刻,都是高光的:每年暑假顶着烈日,去山上采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晒干了变卖;那偶尔觅得的月季花,独特的香味,如丝绒般的红色花瓣高贵端庄;那令人心悸的打碗碗花,总怕碰坏了,就会打碎家里的碗挨骂;那别人院里锁不住的栀子花,偷偷采回来,泡在水里,插在泥里,束在辫梢,看着一点点绽放;那遍地的油菜花,放学回家,采了油菜花,装在玻璃瓶里,拿一根从扫把上折下来的竹枝,在土墙上的洞眼里掏蜂子;那一个个牧鹅的傍晚,躺在绿草坡上,看着蓝天,任一群白鹅在青草间穿梭;那漆黑的夜里,抓了好多萤火虫,装在玻璃瓶里,一闪一闪,做成萤光灯……
童年是清澈的,是诗意的,是闪光的,有“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无拘无束,有“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的童真。每一分每一秒都闪着金色的光,因为童年时光像金子,童真更像金子,闪着耀眼的光。那光太过耀眼,照亮整个人生。现在看来,仍绚烂无比。
翻出来一本《城南旧事》。记忆中那是一本清新透亮的书,我也正想找找儿时的旧事,便一页一页读起来。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记述自己在老北京胡同里的童年旧事。作者通过英子清澈而透亮的眼,稚嫩而敏感的心,感受老北京胡同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她待人感情真挚,对被大人当作“疯”女人的秀贞,她充满信任,她看到的是痴痴地等着被家人丢弃的女儿回来的妈妈;对一个陌生的“贼”,她也充满善意,她看到的是为供弟弟上学,不得不这样,反而不断自责的忠厚的人;对和爸爸暧昧的兰姨娘,她机灵地穿针引线,撮合她和德先叔,她看到的是身世悲惨、淡雅温暖的兰姨娘;她对家里的仆人充满同情,她看到的是为了养家,到自己家做九年保姆,却因丈夫疏于照料,失去了两个孩子的宋妈。故事讲述的是一场一场懵懂的别离,是和人的别离,也是和童年的别离。最后,爸爸的花落了,英子的童年也结束了。
整个故事如一泓清泉,澄澈而缓缓地流动,清亮并伴着跳跃的音符,读起来,仿佛阳光在水面上跳动,轻盈而灵动,带着一丝离别的惆怅,和英子对善恶的不解与质疑,萦绕着淡淡的哀愁和沉沉的相思。
在英子眼里,一切都是美的,真的,善的。她分不清大人嘴里说的疯子和坏人,可她的眼是透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她没有像大人一样,被蒙上厚厚的一层凡尘,她在用最敏感最稚嫩的心,细微地感受着周边的世界。
英子的眼光是软的,是嫩的,是灵动的,是明媚的,不带一点坚硬和突兀,不带一点成见和遮盖,只真真儿地看着,哪怕是被大人说成疯子的秀贞,英子仍对她充满信任;哪怕是最后被逮捕的“贼”,她仍记着和他一起去看海的约定;哪怕是和爸爸暧昧的兰姨娘,和德先叔一起离开时,英子仍依依不舍。
那是一份柔软,一份鲜嫩,一份纯净,一份透彻,那是除童年之外,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有的。作者用文字记录下童年旧事,让实际的童年过去,而心灵的童年永存了下来。
看着《城南旧事》,眼前浮现的是自己的童年。那在自己的记忆中,早已发黄的影像,随着林海音通透的描述,竟渐渐清晰起来。我的童年和英子的童年完全不同,但童真是相通的,清新是相同的,自然而毫不掩饰。
童年是如花岁月,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留下的都是甜蜜回忆。也许曾在学校打过闹过,那都是童真的天然流露;也许曾饿过肚皮,而记住的是,看到美食时的心旌摇荡;也许冬天脚冻得生疼,课间脱下鞋子搓着脚尖直哭,那是可爱的毫无遮掩。有穿着粉色碎花旗袍,走上讲台,给一年级讲解拼音时的喜悦;也有被老师称作“小铁梅”时的自豪。想到的,看到的,说着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可爱小孩,用纯真经历着生命,经历着时光。那是在时光隧道深处,一幕幕上演着的,那是各自心中无法书写的《城南旧事》。
我很庆幸,现在仍可跟着英子的眼光,看到时光深处的自己。每每想到,都泪眼迷离,这不是感叹艰苦,而是感叹失去的清澈,无法回头。那黄旧的、布满雪花、有呲呲杂音、画面已渐渐模糊的影像,离我越来越远,无法修复。
粉色碎花旗袍,是我如花童年的一次高光经历。其实,回过头来看,那时所有的时刻,都是高光的:每年暑假顶着烈日,去山上采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晒干了变卖;那偶尔觅得的月季花,独特的香味,如丝绒般的红色花瓣高贵端庄;那令人心悸的打碗碗花,总怕碰坏了,就会打碎家里的碗挨骂;那别人院里锁不住的栀子花,偷偷采回来,泡在水里,插在泥里,束在辫梢,看着一点点绽放;那遍地的油菜花,放学回家,采了油菜花,装在玻璃瓶里,拿一根从扫把上折下来的竹枝,在土墙上的洞眼里掏蜂子;那一个个牧鹅的傍晚,躺在绿草坡上,看着蓝天,任一群白鹅在青草间穿梭;那漆黑的夜里,抓了好多萤火虫,装在玻璃瓶里,一闪一闪,做成萤光灯……
童年是清澈的,是诗意的,是闪光的,有“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无拘无束,有“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的童真。每一分每一秒都闪着金色的光,因为童年时光像金子,童真更像金子,闪着耀眼的光。那光太过耀眼,照亮整个人生。现在看来,仍绚烂无比。